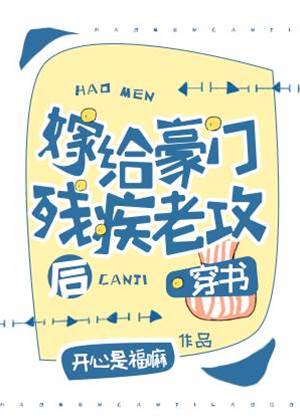《一屋暗燈》 第9章
這個暑假對于宋謹來說很充實,他和同班的幾個同學一起接了些小的項目,除了在太底下進行RTK作業,就是對著電腦做GPS數據解算。在分工上,宋謹偏向于做靜態數據,所以出去曬太的次數還算,至一個暑假下來,他幾乎沒曬黑,只是近視度數稍微加深了一點,有時候看遠的東西都要戴眼鏡才能分辨清。
除了做測繪,宋謹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甜品店,他偶爾會被唐閔他們鬧著他吃甜品,但宋謹除了面包,其他跟油相關的,他都不。
“會吐的。”宋謹說,“我真的吃不了油。”
“那看來是我做蛋糕的技還不行。”唐閔若有所思道,“所以我們宋謹哥哥不愿意吃。”
“哥哥”這兩個字無疑是宋謹最難以面對的詞匯之一,他勉強一笑:“我真不吃。”
“那就算了,走吧,一起吃飯。”唐閔 摘下圍和襯衫上的領結,說,“不是說去嘗嘗那家新開的韓式烤麼,店長說了要請客的。”
“我什麼時候說了!”正在對賬的何浩蹦起來,“唐閔!除非你有錄音,否則不要誣陷我!”
唐閔拿出手機,不慌不忙地真的給放了一句錄音。
其實是一條微信語音,唐閔正在跟朋友說話,結果背景里是何浩一句十分擲地有聲的“等那家烤開了我請你們吃!”
何浩沒話說了,一邊撕著一天下來堆積的小票一邊有氣無力道:“行吧,大家去了多吃蔬菜,點,現在豬那麼貴,烤店里肯定以次充好,我不希你們吃壞肚子。”
唐閔笑著攬過宋謹的肩,朝何浩揮揮手:“好的店長大人,那我們只能多點牛了,你關了門就跟上來啊。”
Advertisement
唐閔的習慣就是這樣,他長得高,宋謹剛好比他矮了一點,很適合當他的支架,他有事沒事就把手搭在宋謹肩上,把整個人的重量給宋謹勻過去一些,還名其曰是給宋謹做力量訓練。
宋謹:“你只會讓我變高低肩。”
夏日傍晚的風溫而不熱,街道上是來往的車流,對面的商場大樓燈璀璨,一切都熱鬧得充滿生活氣息。
兩人走到商場門口,何浩還沒跟上來,估計還在店里孜孜不倦地一遍又一遍地對賬,宋謹給他發了微信過去,催他快一點。
“哎,那男生好眼。”唐閔朝遠看了看,“好像是前不久在店里朝你發脾氣的那個。”
宋謹的手一,手機差點掉在地上,他抬頭看去,但是遠了視線就有些模糊,他又沒戴眼鏡,完全看不清那些移的人影里哪一個會與宋星闌有關。
“你看錯了吧。”宋謹的聲音都有點發虛,“沒那麼巧的。”
“不知道,看著像,長那麼高,一張臉又那麼好看,說實話我印象深的。”唐閔說,“就是格不太好的樣子,不過這樣的男生在 中學里都特吃香,小孩就喜歡這種類型。”
“不一定。”宋謹收回視線,“格那麼差,不是一張臉就能解決的。”
唐閔側頭看著宋謹笑起來:“哇,第一次聽你說這種話,平常看起來溫溫的,沒想到還記仇?”
宋謹心想我這哪里是記仇,只不過是一個正常人在遭過那些對待后該有的反應而已。
“別看了,應該不是他。”宋謹說,“進去吧,估計人多的,先排隊號。”
“嗯。”唐閔看了一眼手機,“何浩說已經鎖門了,馬上就過馬路。”
Advertisement
宋謹忘了自己有沒有回答,他的思緒早就因為唐閔那個關于遠可能出現宋星闌的猜測而變得模糊雜起來,今天是開學后的第二個星期,沒過幾天,就是宋星闌的生日。
宋謹并不想記得這個日子,但他偏偏就是忘不掉,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計算過,自己的生日和弟弟只差兩個月,他們一個出生在秋天,一個出生在夏末。
后來分開的那十年里,每次一到九月,宋謹就會想到,夏天快過去了,在夏天結束之前,是弟弟的生日。
然而他也深知自己和宋星闌的距離以及差別有多大,隨著年歲的增長,剛開始那些試圖去見一見宋星闌的想法被漸漸埋沒,到最后只剩下“他一定不想見我”的篤定猜測,而這確實是真的,宋星闌很討厭他,討厭到極點。
宋謹承認,他有病,在過去的十年里,他接母親的所有怨氣,然而他并未覺到過度的沉重,反而將那當作是一種被依托與需要的覺。
他的心理是畸形的,只要對方需要他,他似乎就能為此承一切,哪怕宋星闌有一秒鐘的時間將他當作哥哥,宋謹說不定也會甘愿接所有,包容所有。
但是宋星闌沒有。
宋謹隔了一天再去甜品店,已經是下午,唐閔正在切水果。
“來了。”他轉頭看宋謹一眼,“外面很熱吧?”
“是啊,還是很熱。”宋謹正準備圍上圍墻,轉眼卻看見了唐閔手肘上的紗布。
“你的手怎麼了?”宋謹低頭去看,“摔了?”
“別說了,嚇人的。”唐閔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昨天晚上過馬路的時候,有輛車直接朝我上撞,幸好我躲得快,摔在人行道上了。”
宋謹不可置信地睜大了眼:“故意的嗎?”
Advertisement
“不知道,說不定是醉駕。”唐閔搖了搖頭,“那路口沒什麼人,我又摔在地上,連車牌號都沒看清,車子就開走了。”
“可以調一下周圍的監控,說不定能找到車。”宋謹說。
“算了吧,就算找到了又怎麼樣呢,有些時候多一事不如一事,人沒事就行了,萬一惹著什麼不對勁的人,瘋起來找我麻煩怎麼辦?你說是吧。”
他的一席話就像扔在水里的石頭,砸得宋謹心跳飛速,他確實比誰都明白這種覺,就像他永遠不敢招惹宋星闌一樣,明明做錯的是對方,自己卻是最小心翼翼的那個。
因為瘋子不講道理,他要你睡不好,你就永遠別想做上任何一個夢。
第二天下午也是在甜品店里忙,晚上宋謹回了家,這間舊屋子幾年都沒怎麼變,母親的東西仍然歸置在生前的那間屋子里,宋謹還是睡閣樓,但現在卻不覺得狹小了,因為整個家里只有他一個人了。
他躺在床上,看著閣樓天窗外凄清的月,今天是宋星闌的生日,他的弟弟十八歲了。
他們兩人之后只會越來越遠,從親兄弟變仇人,再變陌生人,為彼此生命里不會再被提及的部分。
從前宋謹不愿意面對這種下場,但現在看來,這樣的結果或許是最好的,有些鴻不過去,那就別了,不必互相為難。
況且在領教宋星闌的種種之后,宋謹已經不再用緣來欺騙自己了,它并不能代表什麼,有時候反而是一種諷刺的累贅,得一個咬牙忍讓,一個愈演愈瘋。
今天晚上并不熱,宋謹便沒開那個老舊的空調,只是打開了電風扇,寬松的T恤被吹得微微抖,累了一天,宋謹幾乎是閉眼就睡著了。
當他被一陣關門聲吵醒的時候,那大概是凌晨了。
電風扇還在呼呼地吹,宋謹在黑暗里茫然地睜開眼,可能是被云層遮住了,窗外已經看不到多月,視線里只有一層蒙蒙的深灰,因為有點近視,宋謹這會兒看什麼都好像鋪紗帶暈。
宋謹支起子,沒再聽到什麼靜,大概是隔壁的鄰居晚歸,這棟老樓的隔音并不好,哪怕是睡在閣樓,宋謹從前就常常在睡夢中被一些靜吵醒,由于睡眠時的意識不清醒,很多聲音都會被玄妙地放大,仿佛響在耳邊,他不是沒有經歷過。
宋謹于是又趴下去了,他將側臉埋在枕頭里,電風扇吹著后腦勺,宋謹秒睡過去。
當他朦朧中聽見腳踩在地板上的吱呀聲時,他還在模模糊糊地想,自己有時候半夜回家,隔壁鄰居是不是也被這麼打擾過。
他懷著散的思緒將要夢,房門突然傳來異響,那是陳舊的門把手被往下時出的刺耳聲音。
宋謹就是再沒睡醒,也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還覺得這不是從自己家發出的響聲。
只是還沒等他撐著手起,一只手就按住了他的后頸,將他死死地釘在了床上。
風扇的風像是突然間被放大數倍,照著宋謹的臉不斷地呼嘯而來,宋謹拼命睜著眼睛,心跳幾乎要穿過腔,將整張床都震得發抖。
他聽到清脆的鐵鏈撞以及金屬鋸齒的咯咯聲。
宋謹很快就知道,那是一副手銬。
因為對方在宋謹被按著后頸無法彈時,快速又直接地將它銬在了他的右手手腕上,就像人贓俱獲時不留面的警察。
宋謹寧愿自己真的是獲罪被捕,也不想面對此刻的一切。
他聞到了酒氣,他聽到后的人在沉重地息。
息也是有音的,有時候也能聽出那屬于誰。
是宋星闌。
猜你喜歡
-
完結145 章

病美人
前世,葉雲瀾容貌毀於一場大火,此後經年,他受盡世人誤解,聲名狼藉。 一朝重生,他回到三百年前。他從大火中逃出。這一回,他容顏無恙,卻因救人損了根骨,折了修行,落下一身病骨沉痾。 葉雲瀾並不在意。 前生風雨漂泊日久,今生他隻想要平靜生活。 然而,很快他卻發現,前生廢去他金丹的師兄,關押他百年的宗主,將他送給魔尊的道侶,還有那些厭惡嫌棄他的人……突然都開始對他大獻殷勤,不但送靈藥送法寶送信物,甚至還要送自己。 葉雲瀾︰?這就大可不必。 ——沈殊此生都無法忘記那一幕。 漫天烈火之中,那人如白鷗飛掠而來,將年少的他抱起護在懷中。 烈焰撞入那人背脊,有血滴在他臉頰,又落入他心尖。 比烈火更加灼然。 後來,他低頭恭喊那人師尊,卻又在對方蹙眉輕咳時,忍不住握緊那人蒼白的手,強硬抹去他唇上的血。 人人罵他墮入魔道,背叛師門,他不聞不聽,一心隻注視著那人,如望明月。 ——沉湎於美色,困囿於渴念。 修真界新晉第一美人,是所有人的心尖明月,求而不得。 【高亮預警】 1、病美人受,受病弱但實力不弱,美顏盛世萬人迷,經常會吸引人渣、sjb、病嬌的覬覦。 2、CP徒弟,偏執狠戾狼狗攻,前生唯一沒有負過受的人,其他
48萬字8 6796 -
完結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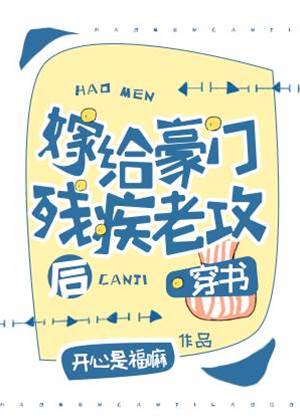
嫁給豪門殘疾老攻后
景淮睡前看了一本脆皮鴨文學。 主角受出生在一個又窮又古板的中醫世家,為了振興家業,被迫和青梅竹馬的男友分手,被家族送去和季家聯姻了。 然后攻受開始各種虐心虐身、誤會吃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會變成船戲之路。 而聯姻的那位季家掌門,就是他們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季靖延作為季家掌門人,有錢,有顏,有地位,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可惜雙腿殘疾。 完美戳中景淮所有萌點。 最慘的是自稱是潔黨的作者給他的設定還是個直男,和受其實啥都沒發生。 他的存在完全是為了引發攻受之間的各種誤會、吃醋、為原著攻和原著受的各種船戲服務,最后還被華麗歸來的攻和受聯手搞得身敗名裂、橫死街頭。 是個下場凄涼的炮灰。 - 原著攻:雖然我結婚,我出軌,我折磨你虐你,但我對你是真愛啊! 原著受:雖然你結婚,你出軌,你折磨我虐我,但我還是原諒你啊! 景淮:??? 可去你倆mua的吧!!! 等看到原著攻拋棄了同妻,原著受拋棄了炮灰直男丈夫,兩人為真愛私奔的時候,景淮氣到吐血三升。 棄文。 然后在評論區真情實感地留了千字diss長評。 第二天他醒來后,他變成主角受了。 景淮:“……” 結婚當天,景淮見到季靖延第一眼。 高冷總裁腿上蓋著薄毯子,西裝革履坐在豪車里,面若冷月,眸如清輝,氣質孤冷,漫不經心地看了他一眼。 景淮:……我要讓他感受世界的愛。
16.2萬字5 61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