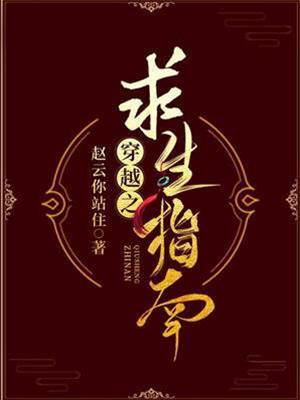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白日提燈》 第7章 心愿
涼州府城的城墻修得高聳堅實,如同沉默的巨人,可即便這樣的巨人也沒有能抵擋住胡契人的第一次來襲,更沒能保護住這一城的百姓。
從城墻上能看見不遠寬闊的關河,天氣晴朗之時,甚至能遠遠看見河對岸的丹支朔州。
城墻上守衛的士兵看見段胥來了,紛紛行禮道將軍。統管城墻布防的韓令秋韓校尉也趕來,那是個壯高挑的年輕男人,他臉上有一道駭人的傷疤,從下頜一直到額角,以至于看起來有些可怖。他神嚴肅,雙手抱拳道:“段將軍。”
段胥點點頭,讓孟晚隨韓令秋去查看城墻布防,然后便回頭看向那個拿著糖人的姑娘。
十分自然地走到了垛口邊,一邊向遙遠的關河,一邊還不忘的糖人。
城墻上不比城里,冬日的寒風迅疾而猛烈,的長發被風拉扯著,斗篷里也灌滿了風,仿佛被吹開一朵藕的桃花。
的一只手放在城墻的磚塊上,冬日里的磚塊上去應該如同刀割一般,的指尖蒼白,指節同的臉頰鼻尖一樣凍得通紅。可是沒有重新拉好自己的斗篷,更沒有毫瑟。
但凡是能覺到冷的人,應該都不會如此罷。
賀思慕突然轉過頭來,說道:“城墻上所有的風果然都一覽無余。像白蛛,疏疏布滿天地間,看不見來也不知去。”
像蛛一樣的風,奇妙的比喻。
段胥隨的手指看過去,在凜冽寒風中道:“白的風,便如我這袖口一般的嗎?”
“是。”賀思慕笑起來,笑著笑著,突然問道:“將軍大人,你有沒有心愿?”
“心愿?”
“對,心愿。”
段胥微微一笑,坦然道:“平生所愿,關河以北十七州回歸大梁所有。”
Advertisement
“……”
賀思慕面上神不變,心想這是什麼冠冕堂皇的樣文章,比關淮奉承的話還不能當真。
段胥見不說話,道:“怎麼了?”
賀思慕一臉哀容,推說怕,一想到收復十七州,天下流河就害怕。頓了頓,突然湊近段胥,段胥面帶笑意不聲地后退半步,等著的下文。
“我行走江湖,對頭骨頗有研究。”賀思慕指指著段胥的頭,不著邊際地說:“將軍大人生了一副好頭骨,后腦圓潤,顱頂高,額頭飽滿,眉骨高而眼窩深,還是雙眼皮。”
段胥挑挑眉,這聽起來實在不像是夸人的話,倒像是屠場里挑牲口的經驗。
“地道的漢人頭骨并不長這樣。我聽我爹說,幾百年之前在比丹支還要北的北方,有一支做狄氏的民族,他們那里的人頭骨才是如此。當年狄氏和漢人之間廝殺多年,你死我活是海深仇,可是如今世上已經沒有了狄氏。狄氏融進了漢人的脈里,融進了您先祖的脈里。”
如今胡契和漢人亦是死敵,但最終他們的脈將相融,百年之后為父子兄弟,骨至親。
這世上的事大多如此。恨極了的轉頭濃于水,深了的眨眼陌路兩端,親疏反復且無事長久。
你死我活的爭斗或收復山河的壯志,都會化為云煙。世事多無趣,何必這麼認真呢?
段胥凝視了賀思慕一會兒,突然大笑起來,他扶著城墻,笑得彎下腰去肩膀。
賀思慕納悶地看著他,只覺得這個話題沒什麼好笑的,這個年怎麼笑得像個傻子。
其實的評價有失偏頗,段胥笑起來是很好看的。他眼睛明亮微彎,盛著滿滿的要溢出來的快樂,出潔白的牙齒。
Advertisement
“抱歉,抱歉賀姑娘,我便是天生特別笑,并不是對你的話有什麼意見。”段胥平復著笑意,直起來對賀思慕說道:“我就是想起來,年時我喜歡去海邊堆沙子,無論堆多好的沙堡,海水一漲皆被沖散。當時我若能有姑娘這番見解,也不至于傷心了。畢竟沙堡沒有真正消失,只是歸于沙礫。”
“姑娘或如我,而我如沙堡。”
他偏過頭,笑意盈盈地看著賀思慕:“我生前是沙,后是沙,唯有一刻為堡壘,也只需為這一刻而活。”
百年以前如何,百年以后又如何,即便世間有回他重活于世,那也不是他了。
賀思慕瞧了段胥片刻,他站在燦爛,蛛一樣集的風纏繞在他上,就像是繭子里的蝴蝶。
心嘆著,凡人嘛,不過百年的壽命,終究還是堪不破恨仇。面上卻出敬佩的神,拍手稱贊。
段胥的目落在手里的糖人上,他說:“方才我就想問了,姑娘手中的糖人,畫的可是……”
“神荼,沉英還有個郁壘的,兩位門神大人。”賀思慕晃晃手里那個被得沒了半個肩膀的糖人,道:“前段時間半夜撞了鬼,沉英一直怕得不行。今日從孟校尉那里多拿了些飴糖,我就畫了倆門神,據說惡鬼都怕這個,拿來驅驅邪。”
說著,一口便咬下了神荼糖人的半個腦袋。
段胥忍俊不,他抱著胳膊搖搖頭,卻見賀思慕舉著那糖人遞給他:“要不要嘗嘗。”
那琥珀的糖人在下晶瑩剔,仿佛寶石一般閃爍芒。穿過糖人的隙可以看見的笑臉,坦而熱烈。
段胥于是出手,掰下未曾荼毒的糖人左腳放中。他微微皺眉,繼而笑開:“賀姑娘,太甜了。”
Advertisement
賀思慕靠近段胥,逗他道:“將軍,是說什麼甜?”
眼前的姑娘面凍得泛紅,笑容卻甜。
年的眸閃了閃,但仍然波瀾不驚道:“糖人。”
“甜嗎?”
“甜得過頭了。”
“各人口味不同,誰讓我嗜甜呢。”賀思慕又咬了一口糖人,看向遠方冰凍的關河,突然說道:“四日后十一月初八,亥時東風夾雪。”
段胥明了,俯行禮道謝,便聽見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你一定要去嗎?”
段胥抬眼,便見那姑娘直直地著他的眼睛,眼里又流出一輕微的悲憫。
“我聽孟校尉說將軍大人本不是踏白的將軍,臨危命而已。以您的顯赫世,多做斡旋,應當可以回京。”
段胥嘆息一聲,道:“你們怎麼都這樣,讓我覺得仿佛是在螳臂當車,好生悲涼。姑娘放心,小時候我算過命,先生說我這一生將會逢兇化吉。”
賀思慕想,這人從給事中,宰執候選人到翊衛郎到邊關郎將到生死一線的將軍,可是盡逢兇了怎麼沒見化吉呢。
“你這不是螳臂當車,又是什麼?”
段胥微微一頓,輕松地笑道:“是雖千萬人吾往矣。”
賀思慕只好點點頭,順便吃掉了最后一口糖人。
這倒是沒錯,沒有強悍的命格如何駕馭破妄劍呢?
小將軍可別死啊,破妄劍的主人,應當不止于此吧?
段胥一路將賀思慕送回了的小院,遠遠地就看見沉英抱著膝蓋,乖巧地坐在門口四張,見了便兩眼放地跑過來。
這孩子自從上次遇見惡鬼后,越發粘人了。
賀思慕告別段胥,牽著沉英走近院中,漫不經心地說:“糖人吃完了?下次還想吃什麼?”
“還想吃糖人!小小姐姐這次糖人畫得真好,就是太淡了,都沒有什麼甜味。”沉英最近養得圓潤了些,拉著賀思慕的手撒。
賀思慕的腳步頓了頓,低頭看向沉英:“沒什麼甜味?”
沉英是窮苦人家的孩子,從小就沒怎麼吃過糖,又實誠得很,他說不甜應就是真的不甜。
方才段胥說這糖人甜得過頭,難道只是玩笑?
心中一,蹲下來對沉英道:“今天送我回來的小將軍,他的袖口是什麼的?”
沉英想了想,舉起手指天道:“藍的!天空的。”
——白的風,便如我這袖口一般的嗎?
賀思慕沉默片刻,似笑非笑地把玩起腰間的玉墜。
好啊,小將軍在試探,是掉以輕心了。
他的直覺顯然比孟晚好太多,居然被他給探準了,這只小狐貍。
打發了沉英去玩,看著沉英漸漸消失在的視線里,便從懷里拿出那顆明珠,喚道:“風夷。”
過了一會兒,那明珠里發出聲音:“老祖宗,又怎麼了?”
“我還記得,你說過段胥在南都長到七歲,就被送回岱州老家祖母邊服侍,十四歲方才重歸南都。”
“沒錯。”
“南都沒有海,岱州離海更是隔了十萬八千里。他應該從沒見過海,他時是去哪里的海堆的沙堡呢?”賀思慕顛著明珠,悠悠道:“這個家伙,不太對勁啊,幫我好好查查他。”
段胥離開賀小小的小院門口,面帶笑意悠然地往回走。快走到太守府門時,有幾個孩子在街上蹴鞠,一腳下去失了力道,藤球便疾速朝段胥飛來。孩子們的驚呼聲剛剛響起,他就更快地側抬手,五指穩穩地抓住那藤球。
有個小男孩便跑過來,段胥把藤球遞給他,這小孩仰著頭看向段胥,滿臉好奇道:“大哥哥,你怎麼笑得這麼開心呀?”
段胥蹲下來,笑意盈盈地他的頭:“今天遇見一個很有趣的朋友。”
“一個能看見風,卻很可能不辨五,不知冷暖,不識五味的人。”
小男孩出迷的神,不解道:“好奇怪的人呀,這不是很可怕嘛!”
“可怕?哪里可怕?”段胥偏過頭,笑容更加燦爛了:“這多有趣啊。”
小男孩哆嗦了一下,他現在覺得這個大哥哥也怪可怕的。
“將軍!”
段胥抬眼看去,看見夏慶生帶著一班士兵朝他走來。他站起,夏慶生便抱拳行禮,面憂慮道:“將軍,這里不比南都,您不能總是一個人行……”
段胥拍拍夏慶生的肩膀,不反駁也不答應,只是道:“吳郎將來了嗎?”
“在里面候著了。”
“好,我們進去。”
猜你喜歡
-
完結2785 章
邪君的醜妻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还他一针!人再犯我,斩草除根!!她,来自现代的首席军医,医毒双绝,一朝穿越,变成了帝都第一丑女柳若水。未婚被休,继母暗害,妹妹狠毒。一朝风云变,软弱丑女惊艳归来。一身冠绝天下的医术,一颗云淡风轻的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棋子反为下棋人,且看她素手指点万里江山。“江山为聘,万里红妆。你嫁我!”柳若水美眸一闪,“邪王,宠妻……要有度!”
512.9萬字8 45021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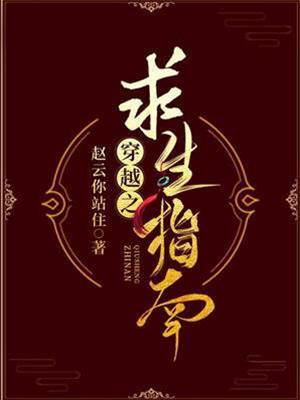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完結597 章

傻妃帶崽要和離
傻子公主被迫和親,被扔到西蠻邊陲之地。所有人都認為她活不久,可沒想到,五年后……她不僅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個奶兇的小團子,再嫁將軍府。“一個被蠻人糟蹋過的女人,還帶著一個小野種,真是將軍府的恥辱!”誰知將軍惶恐,跪搓衣板求饒:“娘子,我兒子……都長這麼大了。”
106.1萬字8.18 48686 -
連載2165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1.6萬字8.33 477841 -
完結51 章

讓你展示法術,你直接禁術起手?
天道網游降臨與現實融合,怪物橫行。藍星進入全民轉職的時代,通過獵殺怪物,不斷升級,獲得裝備,強化自己。 地球穿越者:薛江,在轉職當天不僅成功覺醒職業,還驚喜的發現自己開啟了禁術系統。 “叮,恭喜您提升了等級,請選擇您的禁術獎勵!” 生生不息,直到將對手燃燒殆盡的火屬性禁術:地獄炎照? 足以毀滅一座城市的大范圍雷屬性禁術:雷葬? 能夠將對手冰凍,瞬間完成控場的冰屬性禁術:絕對零度? “不玩了,我攤牌了,其實我這個入是桂!” 于是,薛江直接開啟不當人模式。 野外小怪?秒了! 遇到boss了?秒了! 地獄級領主?秒秒秒! 沒有什麼是薛江一發禁術秒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來一發。 這個時候,就有網友質疑了: “薛江薛江,你那麼牛逼,有本事你把小日子過得還不錯的島國秒了。” 那一天,島國人民仰望著天上逐漸構成的法陣,終于想起了被支配的恐懼。
8.7萬字8 1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