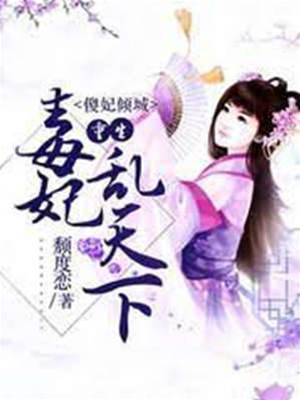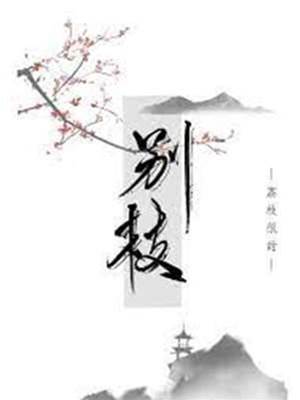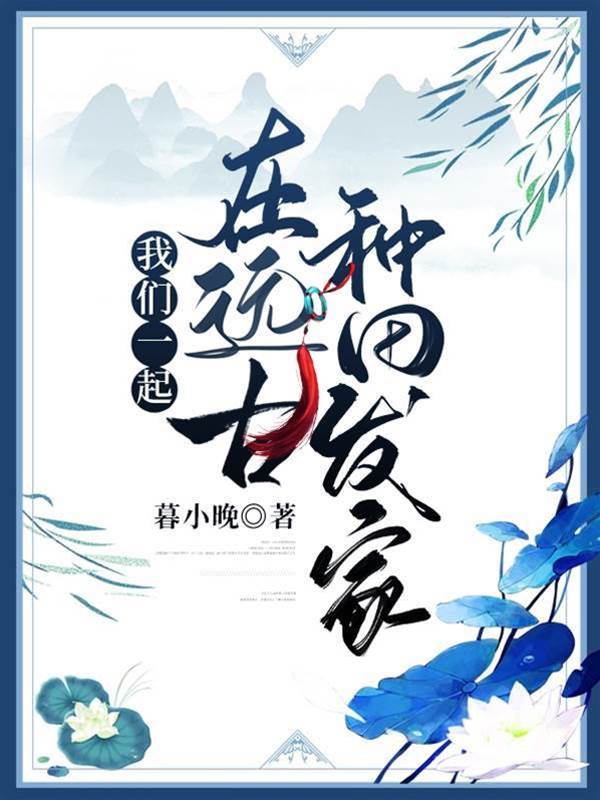《枷鎖》 第27章 第27章
九月初,鎮南王離京。
離京那日聲勢浩大,圣上親自相送十里,執手殷殷囑托,并當場贈送凱旋詩一首。鎮南王激涕零,叩首謝恩。
君臣相宜的和睦場景,一時間傳為佳話。
九月中旬的時候,朝臣們敏的發現,朝中風向有變。
先是有朝臣多有夸贊三皇子的德,后有圣上幾次三番將三皇子單獨進書房考究學問,再到之后三皇子換了之前授業恩師,改作認當世大儒為師,又一改常態與之前不對付的晉世子走親近,種種跡象讓人不得不猜測,圣上怕是有立儲之意了。
五皇子府。
當聽說圣上又將三皇子單獨進書房后,五皇子筆下的宣紙上落下了好大一滴濃墨。
五皇子生的面相儒雅,饒是年紀小些,可待人素來溫和有禮,舉止有度,既讓人如沐春風,也不失他皇子龍孫的矜貴。
此刻,他那面上那素有的溫和淡定,到底出現了一裂痕。
之前父皇遲遲未立太子,待諸位皇子也一視同仁,這讓他也存了些念頭,以為自己會有一力之爭。
萬萬沒想,最終還是這般結果。
昔年,皇考了為了前朝穩定,改立資質相對平庸的父皇為皇太子。如今,他父皇也要效仿皇考,棄他,而立那資質心明顯不如他的三皇兄為太子?
五皇子意難平。
若說皇考那時,夷族侵害的江山不穩,要多依仗驍勇善戰的鎮南王來穩固江山,因而才改立皇太子,這也在理之中。可如今,夷族已不氣候,老將也已遲暮,他父皇為何還有顧忌重重,要那鎮南王影響他們皇家兩朝基業……
突然想到一個緣由,五皇子猛地變了臉。
后又覺得不能,他父皇年登基,如今還不及不之年,沒道理活不過那年過花甲的鎮南王。
Advertisement
想起他父皇這一年來頻頻抱恙,五皇子終是覺得不安,遂招來心腹,讓他多留意下宮中向。
秋去冬來,冬去春至。
又是一年春三月。
可今年的史府,不見去年的喜慶和樂,眼去,滿是悲意蕭條。
饒是有各種珍貴藥續著,符老史的生命還是即將要走到盡頭。
此時林苑已是懷孕七個月,肚子已經十分顯懷,再有三個月就要臨產。
可符老史卻是等不到見到孫子的那日。
他本早已油盡燈枯,能苦苦熬到今日,就是為了能撐口氣見到長孫誕生那日。可那日,他終究是等不到了。
圣上不顧龍抱恙,駕親臨史府,特意過來送他最后一程。
病榻上的符老史面容枯槁,奄奄一息,猶如風前殘燭。好一會才看清榻前之人,當即激的了灰白的,老目含淚。
圣上在病榻前執著老卿的手,嘆息不舍。
“圣上……不必為臣憂心……臣,無憾。”
掙扎的說完這一句,他來長子次子到床前,讓他們跪下。
“符家,赤膽忠心,滿門忠君……要,為君,為國,為民……如有違背,祖宗蒙,天地,不容!”
“父親,兒子記下了!”
永昌十六年三月初五,符老史去了。
圣上大悲,輟朝一日。
符家黃紙漫天,哭聲哀哀。
府前高掛的白燈籠上的黑奠字,愈發加重了悲涼凄婉之。
靈堂設在了正屋堂上,家屬披麻戴孝跪于棺前燒紙守靈,哭尸于室。
“吏部侍郎王瑜大人前來吊唁——”
“府監張銘言大人前來吊唁——”
“國子監祭酒吳翰大人前來吊唁——”
三位大人在門外略作禮讓之后,將挽聯或禮金遞了堂外小廝,之后斂容肅穆進了靈堂,接過香點燃后拜過三拜,之后問家屬,勸他們節哀。
Advertisement
家屬答謝過后,符居敬兄弟二人便起相送。
春杏給林苑換了條帕子,林苑接過,垂眸拭淚。
孫氏雖難掩悲痛在靈前慟哭不止,卻也會分神一二顧著長媳這邊。見其面發白,不免就建議下去歇著會。
“兒媳再守會。若真有不適,兒媳再下去歇著。”
雖說子重了,可為長媳,怎麼說第一日定是要守的。不過也不會過于逞強,若真有不適,便也會去歇著些,待好了些再來守靈。
“莫要逞強。你公爹他……”說到這,孫氏又淚流不止:“他心心念念盼著長孫,你們母子平安,他方能走的安心。”
想到公爹臨終前殷殷切切的囑咐,林苑也忍不住落了淚。
這時候,門外小廝又高聲報到——
“三皇子殿下、鎮南王府晉世子,前來吊唁——”
符居敬兄弟一驚后,忙上前迎接。
林苑也稍微驚了下,不過轉瞬又恢復如常。
畢竟都是陳年舊事,都過去一年多的景了,覺得即便對方昔年有什麼不甘或其他的緒,如今應也已經淡了。
兩人一前一后步靈堂。
三皇子率先上了香,敬過之后,對符居敬道:“老史一生清廉,兩袖清風,錚錚傲骨,人敬仰。如今仙去,委實讓人痛惜,朝中又痛失一棟梁。”
符居敬作揖哽道:“先父泉下有知,定殿下如此厚。”
三皇子嘆道:“符史,你也要節哀順變啊。”
這時晉滁已經上完香,等三皇子與符居敬敘完話,就低聲道了句節哀。
符居敬面一緩,便作揖答謝。
這位晉世子如今倒不似從前那般氣勢凌人了,此刻瞧來,長玉立,緩帶輕裘,倒有些貴公子的矜貴模樣了。
Advertisement
這半年來,他也聽說了些,大概是因著圣上著重教導,這晉世子愈發收斂穩重起來,子也不復之前的乖張肆眥。
雖說昔年兩人之間有些齟齬,可如今人家既然誠心登門吊唁,符居敬自也不會捻著陳年舊恨不放,自也十分誠心的謝過。
晉滁隨著三皇子到家眷這邊。
三皇子道:“老夫人節哀,兩位夫人節哀。”
孫氏哽咽謝過。
林苑與鄭氏頷首謝過。
晉滁近前,聲線略低道:“請節哀。”
悉的音再次落耳中時,林苑真覺得是恍若隔世了。
隨婆母再次答謝。
火盆里的黃紙燃燒,帶些微弱的來,映著前人那張素白的面龐。
為長媳,挨婆母旁,披麻戴孝,雙膝跪地。素手著紙錢,不斷的扔進火盆中,又帶起一陣微弱的。
映照著看似的。
一年前,著紅嫁,一年后,披白孝服。
可無論穿戴何種模樣,終究與他沒有半分干連。
是別家婦,是符家婦。
轉離去時,晉滁的余從那疏離的面容上掠過,又不著痕跡的在那顯懷的腹部定了兩瞬。
那等他們離開后,林苑垂落的眉目稍抬了幾分,暗自松了口氣。
瞧他態度平和,想來前塵往事,他應是放下了。
孫氏見扶了扶后腰,似有腰酸,遂忙建議道:“你還是回去先歇著罷。”
林苑這會的確也覺得疲憊,便也不逞強,應了聲后就由春杏攙起,就扶著腰慢慢的朝室方向走去。
晉滁在與三皇子道別之后就回了府上。
回府之后就徑直去了練武場,牽了匹馬,就飛上去,戾喝著縱馬疾馳。
馬快風疾,他心里卻無半分暢快。
腦中反復出現的,是靈堂里,那個對他疏離答謝的人。
還有那,刺眼的,已然顯懷攏起的小腹。
老史去世,按照常例,符居敬是要丁憂去職的。只是圣上對他格外重用,遂下詔奪,將三年丁憂日期減為三個月。
三個月過后,就要讓他重新回朝。
而那時,也恰好到了林苑臨產的日子。
林苑的胎相極好。從懷孕起,就很注重養胎,聽從嬤嬤囑咐,該吃什麼,喝什麼,該如何走,都一一照辦。加之在符家沒多需要心之事,閑時或賞花看草,或看書寫字,心放松了,胃口也極佳。
這般整個孕期養起來,子骨反倒比之前好上幾分,連娘都說,瞧氣好多了。
六月初的一天,在剛吃過早膳后,林苑就發了。
符家人雖張卻不慌,有條不紊的指揮著那些穩婆、娘、還有下人們,都做好準備。燒水的燒水,接生的接生,符居敬跟孫氏他們則在外間等著,不時地朝產房的方向頻頻去。
孫氏見長子面有冷汗,遂勸道:“定會母子平安的。”
符居敬眉頭皺著依舊難掩張,卻還是緩了神點點頭。
鄭氏坐在另一側,雙手絞著,口中念念有詞。
符以安起先沒聽清念叨什麼,還當是是在祈福保佑平安呢。后來,待他冷不丁聽清在念叨“生兒生兒”時,當即氣的臉都綠了。
狠狠拉了一下,怒視無聲警告一番。
鄭氏見夫君生氣,就趕閉了,不敢再念了。
只是心里頭念不念,旁人便不得知了。
戌時正刻,產房傳來一聲嘹亮的哭聲。
產房外所有人神一震。
孫氏幾乎是奔到產房門口,隔著門大聲問:“生了?!”
“生了!”產房的穩婆揚聲恭喜:“恭喜老夫人,母子皆安!”
猜你喜歡
-
完結4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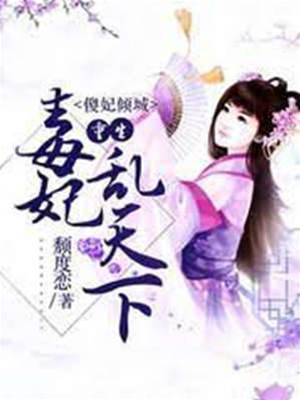
傻妃傾城:重生毒妃亂天下
她,素手翻云,一生一世只求一雙人,苦熬一生成他皇位。卻不料夫君心有她人,斷她骨肉,廢她筋骨,削為人彘,死而不僵。她,相府嫡女,天生癡傻,遭人惡手,一朝拖到亂葬崗活埋。當她重生為她,絕色傾城,睥睨天下。
116.7萬字8.18 82183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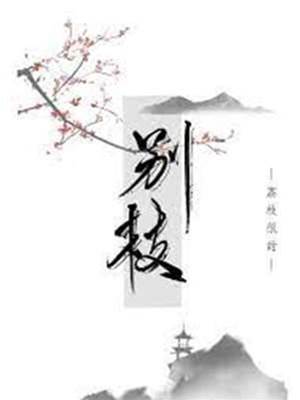
別枝
都知道當今皇上喜怒無常,朝中無人敢與之相駁,宮中更是無人敢伴君側,但也有件讓人津津樂道的罕見事兒—— 和光大師贈了皇帝一幅美人畫,甚得皇帝喜愛,被收于景陽宮。 自那以后,但凡五官有一處與畫中女子相似之人,都被納于后宮。 但也聽聞,無人曾被臨幸過,甚至還死了好幾個。 付家的五姑娘出身不好,自幼膽小如鼠,被傳召進了宮,又因坊間對這位帝王的傳言,她更是提心吊膽,瑟瑟發抖。 緊張之下打碎了景陽宮的一只白玉杯,嚇的魂都沒了,一張臉血色褪的干干凈凈。 宮人見狀,個個閉眼為她默哀,誰知一向淡漠的君王蹲下身子,將付茗頌的手從那堆白玉碎片中握住。 付茗頌嚇的眼淚不止:“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賠給你…” 聞恕抬手擦掉她的眼淚:“你拿什麼賠?” 他身音低啞,像在壓抑著什麼似的:“拿你賠給我,可好?” 一眾宮人面上波瀾不動,心中卻波濤暗涌,唯有一直伺候聞恕的元公公知曉,這付家五姑娘長了一張跟畫中女子一模一樣的臉,連眼角那顆痣的位置都分毫不差。 后來果然不出元公公所料,付茗頌盛寵加身,冠寵后宮。 她害怕,聞恕哄著,她哭了,聞恕哄著,就連晚上做個噩夢,聞恕都抱在懷里哄。 聞恕吃飽饜足后,半彎著唇想,美人都是有毒的,栽了一次,卻還想栽第二次。 閱讀指南: *前世今生,非重生。男主有前世的記憶,女主一開始沒有 *前世be,今生he,別被嚇到,我jio得挺甜的 *女主前期膽子很小,很小很小很小 *雙c 【一切設定為劇情服務,人設不完美,完美主義者慎入。眾口難調,不合口味的話換一本就好啦~】 一句話簡介:別枝未驚鵲,只驚了他而已
29.1萬字8 33400 -
完結2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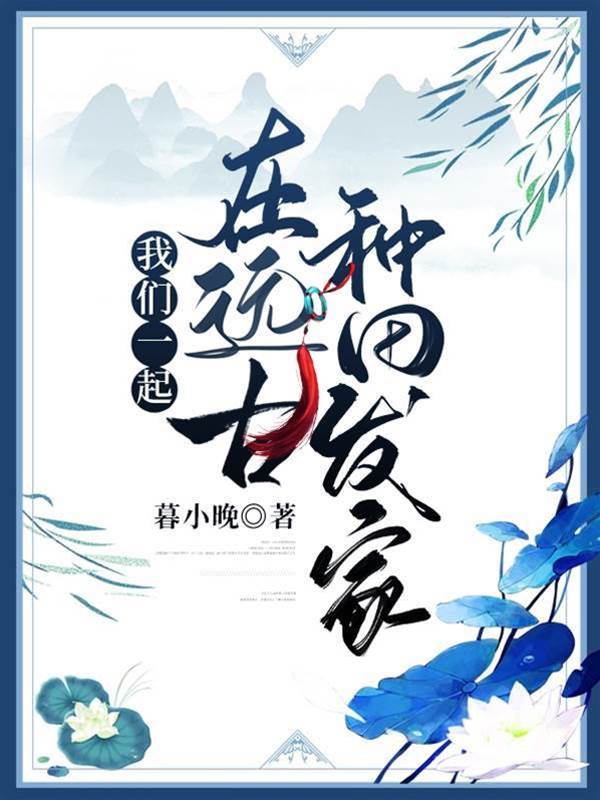
我們一起在遠古種田發家
沈汐硯怎麼都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還能去到自己論文里提到的時代去探究,更沒有想到會遇到一個純古人。二人的相遇是意外,在這個遠古時代也是意外,但生活是繼續的,那就向前進吧。在這個未知的遠古時代發揮那麼點光熱也不是不可以,在改善生存空間的同時還能帶推動文明的進程,也挺好的,做自己想做的,和宋時一起努力找尋回去的辦法,帶宋時去看看自己的時代。 在宋時的這前二十三年里,想著讀書,為官,但這一切在遇到沈汐硯后,他想去看看天外是什麼,他想去看看沈汐硯口中的時代,想看一看銀河。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他會努力讓沈汐硯和自己生活得更加的順利,他也在不斷的找尋方法,以便去看一看沈汐硯口中的天際宇宙銀河。他們依靠部落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來,幫助部落發展,讓部落走向繁榮。
28萬字8 10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