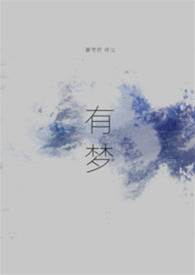《言教授,要撞壞了》 第26章
穿制服在他面前
「不、不用,我自己來吧,」阮誼和面頰緋紅,從任明生手裡接過碘酒和棉簽。
「那好吧,」任明生笑著問:「你怎麼這麼容易臉紅啊?跟我以前印象裡那個「校園小魔」很不一樣啊。」
那還不是因爲你才臉紅啊……
阮誼和正要開口,卻見那位禽般的言教授邁著大長向這邊走來。
他怎麼來了?!
任明生也看到了言征,禮貌地說:「言教授好。」
言征隨意點了點頭,徑直走到阮誼和面前,自然而然地把手裡的碘酒棉簽拿過去。
這高大的男人蹲在邊,朝流的膝蓋輕輕呵氣,說道:「明天開始不去軍訓了。」
溫熱的呼吸拂在傷口,的,阮誼和的雙都在微。
任明生在一旁默默看著言教授給他的「侄」碘酒,總覺得這兩個人不是普通叔侄關係那麼簡單。
「輕點……好疼…」
碘酒到傷口後立即引起火燒火燎般的痛,何況本來敏度就高,現在整個人都在下意識往後。
Advertisement
「那小阮學妹,既然你叔叔來了,我就先走了。」任明生說著,「言教授,回見。」
「嗯。」
………
等任明生走後,阮誼和背後一寒,總覺言征又要欺負了……
「小阮學妹,」言征回味著這個稱謂,嘲諷地笑了笑:「怎麼,故意傷了去勾引學長,討他的同心?」
他的大手著的小腕,加重了力度。
阮誼和被冤枉後也很不爽,氣呼呼地說:「我就是故意摔傷了勾引他,怎樣?你管的著嗎?」
「你最好挨的時候也有這種脾氣,」言征冷冷說:「軍訓給你取消了,這幾天不準住在學校。」
「你這是非法囚。」
「是又怎樣,」言征在耳畔低聲威脅:「你那些視頻和照片要是傳到網上……」
「變態!禽!」
然而禽教授言征不怒反笑,了阮誼和的頭算是安,說:「乖侄,跟叔叔回家。」
的一切反抗,歸於無效。
—————————————
浴室裡滿溢著沐浴的芳香,曖昧不明。
Advertisement
小赤著白晰的子站在花灑下,任由男人將花灑的水衝刷在上。
溫熱的水流對準了嘟嘟的小頭,微微的衝擊力就讓脆弱的小頭充起來,翹著待男人吮吸。
因爲膝蓋疼,阮誼和幾乎站不穩,無力地雙手撐著墻,好幾次快要癱到地上。
「洗乾淨了,」言徵親了親潤的櫻,「可以讓叔叔了麼?」
「我…我真的好累……」阮誼和乞求:「我今天跑了十幾圈……而且膝蓋也疼。」
「誰讓你不聽話,一到大學就勾引學長呢?」言徵用白浴巾給乾了子,把抱到的大床上,蠱說:「叔叔今天要懲罰阮阮這個壞孩子。」
言征拿出一套趣制服,是清純可的水手服,但卻是明布料,而且短的可憐,穿在阮誼和上,上堪堪及部,而短連的小翹都沒有完全遮住。
阮誼和本來就是可型的長相,現在穿這種又清純又的制服,簡直就是人間尤。
太恥了……竟然穿這種服……
Advertisement
阮誼和得不敢正視言征,垂著眸子,盯著床單看。
「既然阮阮這麼累,」言征頓了頓,「今天就輕鬆一點,只要把自己玩到高就可以睡覺了。」
阮誼和困地看著言征拿給的自棒,有幾分慌。
「放在這兒,」言征把自棒直接到剛剛洗完澡還很潤的小裡,打開了最大檔的震。
這自棒是棒的形狀,上面還有礪的顆粒,小時立刻引起了快。
阮誼和渾空虛至極,雙糾纏著夾了那自棒,小屁在床上不安分地扭著,淌在香的上,又又……
猜你喜歡
-
連載100 章

風流推銷員
看一介推銷員如何獵艷,馳騁在萬花叢中,盡享美人香。。。。。
15.8萬字7.75 69839 -
完結248 章
少爺們的小女僕
李依依進入樊家做大少爺的貼身女僕,真正目的卻是打算偷走樊家大少的精子。 然而,很快她嬌媚的身體就被樊家的男人看上,淪爲樊家四位少爺的公用女僕。 至於精子? 她要多少有多少。
24.6萬字7.79 856080 -
完結38 章

別給她鏡頭
主業畫室老師,副業模特,副副業相親節目女嘉賓。結果節目導演是前男友…… 那又怎樣,有錢不賺王八蛋!愛是我驕傲,我自卑,是你來我往,是我自相矛盾之間,依舊對你忠心不二。江戍×孟槐煙話不多會寵人床上必然是主場× 風情萬種是真的本質愛撒嬌也是真的日常小甜餅全文免費,順利完結的話再設打賞章。隨心所至,緣更。喜愛的話留言就好,歡迎光臨。[email protected]在言外
8.7萬字8 35401 -
完結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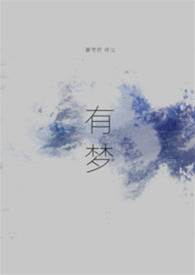
有夢
作品簡介: 她總說他偏執。 是了,他真的很偏執,所以他不會放開她的。 無論是夢裡,還是夢外。 * 1v1 餘皎x鐘霈 超級超級普通的女生x偏執狂社會精英 練筆,短篇:) 【HE】 其他作品:無
5.9萬字8 55327 -
完結105 章
獸人之雌性的反攻
對於一個真正的攻來說,就算穿越成雌性,那也必須是攻! 並且,一個雌性成攻不算成功,我們的目標是——雌性們,攻起來! 本文講述一隻美攻穿到他最口水的獸人世界,遇到他最口水的忠犬強受,在這個雌性重口雄性更加重口的世界裡歡快地奔向抖S攻一去不復返的故事! 本文同時講述一隻獸人雄性被撿來的小雌性一次次吃乾抹盡這樣那樣之後依然覺得是自己不對的無底線寵溺的故事! 小白爽文,美攻強受,1v1,HE。
18.8萬字8.33 151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