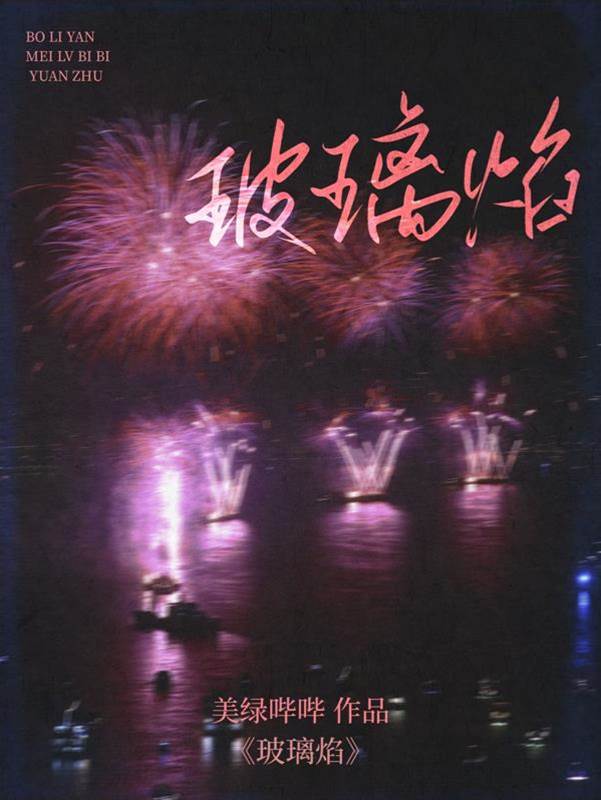《獨寵舊愛·陸少的秘密戀人》 她瘋了,五年去哪兒了
2012年6月,阿笙。
子初,前些天我闖禍了。
有一天,母親走進我房間,說外面太很好,問我想不想出去走走。我連忙點頭,我已經很久沒有外出了,上好像都有黴味了。
太很毒,母親留我一人在門口,回去拿遮傘去了。
有人從我面前經過,在打電話。我跟在後,等打完電話,我向藉手機。
我想問問你怎麼還不來接我。可不借,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了,我搶了的手機。
抓著我的頭髮,我不疼,可是子初,接電話的人不是你,他說我找錯人了。
我怎麼會找錯人呢?這本來就是你的手機號啊!
那個人把我臉抓傷了,罵我是神經病。
我不是神經病。子初,你知道的,我不是有心的,我只是太想念你了。
Advertisement
……
2012年8月,阿笙。
我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出去了。
母親說我傷人傷己,最好呆在房間裡。
我不怕一個人,我怕的是沉甸甸的回憶,忽而清晰,忽而模糊,如同我的神智。有很多事,我都不記得了,但我卻記得一個男人的名字,他陸子初。
我混淆了時間,嫂子那天給我送飯,對我說,現在已經是2012年了,這裡不是舊金山,而是西雅圖。
房間很安靜,靜的我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我想哭,但卻哭不出來,不是害怕,而是畏懼。已經五年了,我的五年哪去了?
嫂子一定在騙我。
……
2012年8月,阿笙。
原來,我真的病了,瘋了。
我父親一年前死了。
我沒印象,我那時候生活在一片迷霧裡,失了孝道。
Advertisement
我給母親下跪,“放我出去,就五分鐘,我只想給爸爸磕個頭。”
母親同意了,我把頭磕出了鮮,但我不痛。全家人都在哭,他們哭什麼呢?
那天,我看到了簡。是我哥哥的兒,很小的孩子,喜歡笑,不怕我,不怕人人口中的瘋人。
說:“姑姑,別擔心,你寫了那麼多日記,我每隔半個月撕幾張給他寄過去,他如果看到這些信,就一定會來接你。”
子初,我著的頭髮,手指竟然在發,的頭髮很,我的心卻碎了。
5年過去,你在舊金山找不到我,大概早就把我忘了吧?你會不會埋怨我,恨我?
你別恨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太多的不明白,好像一直在犯錯,躲在無人角落裡,一病經年,負了你的。
我對不起你。現如今我這樣,我已不敢再等你。
……
客廳。
吳奈不敢吭聲,看完其中一封信,眼眶已溼。
悶異常,一顆心沉沉的往下落。
瘋了?那個平時寡言聰明,笑容淺淡的阿笙,竟然瘋了!
“子初,你跟我說說話。”吳奈忽然很擔心陸子初。
難怪吳奈會擔心了,陸子初全都在發抖,攥著信紙,結,好像隨時都能哭出來一般。
他的臉上呈現出一種近乎死絕般的崩潰。
那個冷靜如斯,善於忍剋制的男人,再也承不了心涌起的痛,把那些信紙在他的臉上,失聲痛哭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479 章

純禽老公:請節製!
為了報複渣男和渣姐,她費儘心思嫁給傳聞娶一個死一個的男人,目的隻是為了報複完成拍拍屁股走人。但陰謀一樁接一樁,背後操控人竟是……他她?爺爺讓我們生個孩子,老婆現在開始吧?”某女瞪著某男,毫不猶豫的拆穿他,“什麼時候你這麼聽爺爺的話?”“一直都很聽,我們快造個小寶貝出來給老爺子玩玩。”“玩?不不不,其實我們可以找個代孕……唔~”生個小包子神馬的,她還怎麼離開啊?摔!!!
58.4萬字8 14682 -
完結314 章

二婚之癢
在最悲慘的時候,沈瑜遇到了薛度雲,他給了她最極致的溫柔,也帶給她最刻骨的疼痛。她在一次次的經曆中變得堅強,卻揭開了令她承受不起的真相。後來,她終於明白,他對她所有的慈悲不是蓄謀已久,而是久彆重逢。
80.3萬字8 16137 -
完結264 章

罪妻
【虐身虐心+替身男主+追妻火葬場】沈南洲恨唐音入骨,為了報複她,他逼她捐肝、試藥、患上絕癥。他逼死她的女兒,毀掉保護她的那個男人,毀掉了她在意的一切。他說:“唐音,我做夢都盼著你死的那一天。”後來,一切真相揭開,流淌了滿地的鮮血,刺紅了他的眼。他再沒能焐熱她的身體。他跪在她的墳墓前,淚如雨下,刀尖狠狠刺入自己的心髒:“阿音,地下太冷,我來陪你。”————沈南洲一直堅信,唐音愛他入骨。直到多年後再相見,他親眼看著她,挽著那個眉眼跟他神似的男人,沈南洲瘋了。(虐文,慎入!)
49.8萬字8 15336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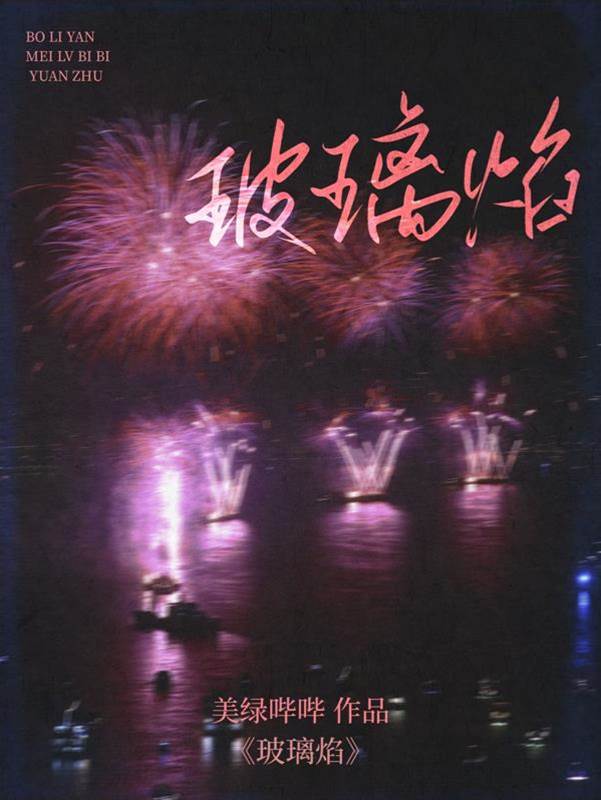
玻璃焰
[已簽約實體待上市]【天生壞種x清冷校花】【大學校園、男追女、協議情侶、強製愛、破鏡重圓】黎幸在整個西京大學都很有名。高考狀元,夠美,夠窮。這樣的人,外貌不是恩賜,是原罪。樓崇,出生即登上金字塔最頂層的存在優越家世,頂級皮囊但卻是個十足十的人渣。——這樣兩個毫無交集的人,某天卻被人撞見樓崇的阿斯頓馬丁車內黎幸被單手抱起跨坐在腿上,後背抵著方向盤車窗光影交錯,男人冷白精致的側臉清晰可見,扣著她的手腕,親自教她怎麼扯開自己的領結。——“協議女友,知道什麼意思嗎?”“意思是牽手,接吻,擁抱,上床。”“以及,愛上我。”“一步不能少。”——“玻璃焰,玻璃高溫產生的火焰,銀藍色,很美。”
25.7萬字8 14204 -
完結255 章

顧總別追了,夫人已經和您離婚了
譚鈺和顧江淮結婚三年,所有人都知道顧江淮不喜歡她,在別人眼裏她就是個笑話。直到顧江淮的白月光回國,支配她多年的戀愛腦突然長好了。一紙離婚協議。顧江淮卻瘋了。譚鈺:“顧總麻煩往旁邊讓讓,別擋著我看小鮮肉”顧江淮眼眶微紅,眉目含淚:“你看他不看我?我有腹肌他沒有!我還比他好看!”譚鈺白眼翻出地球,哪來的綠茶精,快叉出去。
47.6萬字8.18 477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