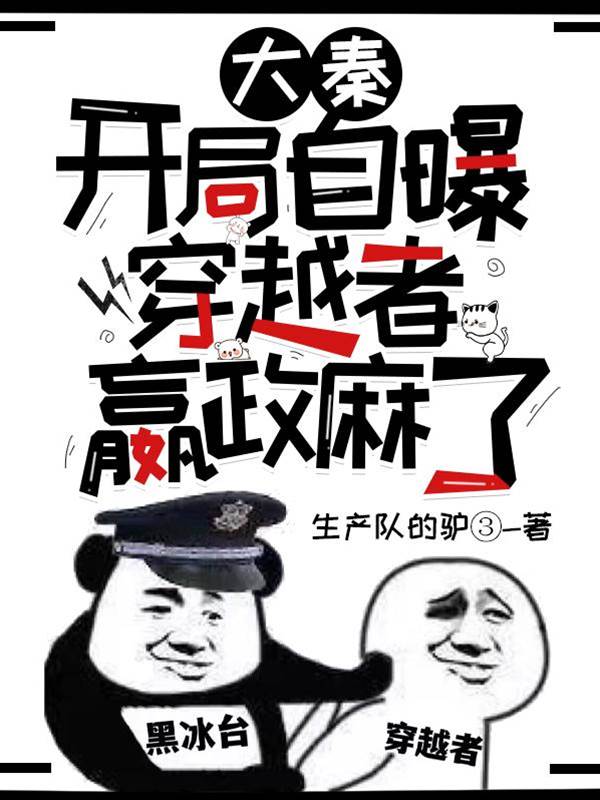《梟虎》 暴怒起 斥訓屬下
暴怒起斥訓屬下
信歸是不送了,但未免出什麽意外,十五這日還是特意趁趙虓召集群臣在前廳議事時過去了一趟。
趙虓見來,有些不解地蹙了蹙眉,但還是起迎:“怎麽這時候過來了?”
張德謙、陳棠、朱雍、李懋、李弘、羅鉞都在,不幾日前剛同意投誠的石徑祥亦是第一次與諸臣同座,共商大計。
七個人齊刷刷起來向行禮,“見過王妃。”
寧悠歉疚地欠,“打擾殿下和諸位大人了,只是殿下午膳後就召集各位至此議事,已議了兩個時辰了,今兒又是十五,妾見您實在辛苦,便讓後廚燉了些梨湯送來,您和大人們飲些,也潤去燥。”
丫鬟們端上碗盞,臣帥們畢恭畢敬地接過去,向道謝。趙虓則眉頭舒展開來,眸中含笑地著:“你有心了。”
劉赟事發應當也就在這會兒了,可外面一點兒靜也沒傳來。
寧悠拖著功夫,見他坐下與其他人一道用湯,又湊過去小聲問:“殿下今兒可要留大人們在府上用膳?妾早些吩咐廚房,包些餃子?”
前世不在建孜,只記著一般逢這樣的節日,趙虓都會要軍中改善夥食,不過有沒有設宴招待將領就不得而知了。但以他格,大抵不會拒絕。
這些大臣將領們又未帶著家眷,形單影只不說,年節期間還在辛苦備防,重整兵馬,理當在朔這日團聚歡慶,稍作歇息放松。畢竟,劉赟那邊兒可是晌午就開始飲酒作樂了。
趙虓虛攬著腰肢,聽在耳邊說完,略忖了忖,拍拍道:“也好,那就勞你費心。”
寧悠點頭:“妾知道了,是照例酒,還是允大夥小酌一二?”
“照例吧。”
磨磨蹭蹭,心焦地等著有人來報,可暼了外邊兒幾眼,院中安靜,就是不見有毫風吹草。難道是,又與以前不一樣了?
Advertisement
已經沒了留下來繼續叨擾的理由,趙虓仰頭一口飲盡碗裏的梨湯,放下碗,看一眼,似乎也在疑為何還磨磨唧唧地黏著不肯走。
目留連地著他,見他眉角粘了浮,便手替他拂去。正要開口向他道告退,只聽外邊一陣小跑聲傳來,護衛急匆匆地進了廳裏來跪下,稟道:
“殿下,左衛指揮僉事曹遠求見!”
來了,前世便是這曹遠向趙虓檢舉得劉赟。
這兩人也算是齟齬已久、矛盾不淺,向來很不對付。因為他倆這矛盾,好幾次還險些鬧出事端來。不過那都是多年以後的後話了,現在還顧不上管那些個。
趙虓心道這曹遠一向沉穩,突然跑來肯定是有什麽要事,就道:“讓他進來。”
曹遠進來後,寧悠見他一臉怒氣沖沖的不忿,跪下去稟道:“殿下,屬下今兒巡營回城上右衛鎮田樟,見他白日裏就喝酒喝得五迷三道,拉著幾個軍士在道旁吹牛。屬下不知這酒令是什麽時候撤了的,可即便是撤了令,也不能這麽放任手下作樂,壞您軍紀、辱您軍威,何統!請殿下察之!”
他倒是沒提劉赟的大名,可田樟那是直歸著劉赟管的,這番言辭犀利的檢舉也就差沒指著劉赟的鼻子罵了。
趙虓知道曹遠和劉赟素來有怨,兩個人不論為人還是帶兵都全然是兩個風格。曹遠耿直剛正,治軍從嚴,眼裏不得一粒沙子。劉赟對手下則向來比較寬恤,難免就放任,以至放縱。曹遠看不慣他言行,起些口角爭執也不鮮。
對這對兒老冤家,趙虓一般不願過多幹涉。平時吵便吵,鬧歸鬧,打仗的時候親無間、配合默契就是了。只要拎得清輕重,那兩人時不時來個狗咬狗一,他也懶得去管。
Advertisement
不過,公然不把他的話放在眼裏,白日裏就縱容手下飲酒,這事還是讓趙虓大為火。
“你先下去,把劉赟給我喊來!”
寧悠站在趙虓旁邊看著,并無離去的意思,想必這會兒他也沒顧及的心思。掃了他腰間那把賜的戰刀一眼,一同等著劉赟過來。
不多時,兩個軍士將已經喝得暈暈乎乎、站都站不穩的劉赟給連拖帶拽地架到了趙虓跟前。
他醉得連趙虓是誰都認不出了,嘻嘻哈哈地對著左右招呼著:“喲,哥幾個聚在這兒,也樂呵著呢?”
趙虓臉更是鐵青,朱雍看見他這樣,也是幫著訓斥,厲呵道:“荒唐!還不快跪下!”
畢竟是自己衛所的人,李懋氣得幹脆是起來給了他一腳,將他踹得跌坐在地上。
劉赟一怒,罵道:“誰他娘的膽敢踹我?”
李懋恨鐵不鋼,咬牙切齒地正要再教訓他,趙虓卻沖他一揮手,令他退開,起來走到劉赟跟前。
“劉赟,你好好看看我是誰?”
他雖掛著臉,語氣卻并非盛怒之狀,反倒聽起來風平浪靜,無甚波瀾。但寧悠再了解他不過,他若面上暴風驟雨,大幹戈,那證明事還并不嚴重。若他忽然冷下來,靜下來,那便是虎伏撲,雷霆震怒的前兆了。
可劉赟醉著,哪知道自己命危矣?
他不知天高地厚地擡眉掃了趙虓一眼,“你他娘的是誰我怎知道?誰把我搞這兒來了?快,快給我扶回去,大夥兒還等著我行酒令呢!”
說著便手去拉趙虓,要讓他扶自己起來。
趙虓左手的刀已經攥了,在場人見此,都為地上的劉赟了把汗,就沖他這大不敬,下一秒他人頭落地都是活該!
一圈人戰戰兢兢,噤若寒蟬地瞥著趙虓,不知這向來不循常理的主上,究竟會怎麽置這個逆臣。
Advertisement
幾近窒息的瞬間,劉赟這個不爭氣的竟然又自己往火上澆了桶油。
他見趙虓沒有,竟催促道:“快些扶我,愣著幹什麽?”
趙虓面上登時然變,一腳踹在他肩膀上,將他蹬了個後仰,锃地一聲拔出刀來。
李懋許是早料到如此,就算心裏邊覺得劉赟死不足惜,還是呼啦帶頭跪了下去。
“殿下冷靜啊!劉赟他罪不至死!”
李弘和羅鉞見狀也跟著拜倒在地,張德謙、陳棠原本只是站了起來,看趙虓這架勢,也只好趕跪下了。
“請殿下息怒!”
一屋子人一時間跪倒了一片,連石徑祥也迫不得已跟著跪了,只是跪得遠了些,仿佛要遠離這出鬧劇的中心,免得波及自己。
總算有人攔著,寧悠略略松了口氣,才發現這須臾自己竟也張得攥了手心。
趙虓盛怒之下已是面鐵黑,握著刀的手青筋凸起,半晌未發一言。
他不說話時,真別人也大氣不敢出一下,仿佛誰靜大了,這刀便要朝誰脖子上招呼過去。
這片刻幾乎凝滯的空氣,他周遭那仄的氣場,即使離著好幾步開外,寧悠都一陣心驚膽寒。心口突突直跳,真怕他手起刀落,一顆淋淋的人頭滾落下來。
劉赟再是不知死活,似乎也酒醒了幾分,撐著胳膊,愣愣地看著一地的人。
看場面僵持,寧悠正想著自己是不是該冒這大不韙上去緩和著些,劉赟大夢方醒地清明了。
他嚎啕著撲至趙虓靴前,杵臼似地咚咚叩起頭來:“殿下,卑職罪該萬死!罪該萬死!”
趙虓終于開口,怒道:“我看你死一萬次都還不夠!”
劉赟這廝,酒醒了倒也是個腦子靈的。他也知不能再給自己找借口開,卑微懇切地一面繼續磕頭如搗蒜,一面哀哀嗚嗚地陳述自己的罪過。
先是對自己無視令“居安忘危,痛心靦面,罪實在臣”,後又對放任手下“不悟不阻,愧憤難當”,最後痛罵自己“上辱于祖宗皇命,下負于七軍黎庶,永言愧悼,若墜深谷,理應自戕,而勿使殿下負戮之名……”
寧悠見他居然還能在這種境況下做出文章來,實在慨,這還真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趙虓聽得煩躁,收刀鞘,喝他:“閉!”
劉赟趕聲,但磕頭卻是一直沒停。
“擡頭!”
他連忙擡起頭來,腦門上已經磕得一片模糊。
寧悠目不敢視地轉開眼,卻又擔憂著趙虓的況,只得將注意力盡量放在他上。可劉赟額頭上那刺眼的紅著實令人難以不留意,胃中忽地犯,勉強才忍住一陣惡心。
猜你喜歡
-
完結720 章
退婚後我成了權臣心尖寵
農科專家時卿落死後再睜眼,穿成了一名古代農家女。開局就是被全家賣了,正要被強行帶走,給縣城即將病死的富家公子成親陪葬。時卿落擼袖子就是幹。以惡制惡、以暴制暴,讓極品們哭爹喊孃的主動將親退了,還不得不供著她。轉頭她主動將自己嫁給了隔壁村,被分家斷親昏迷的蕭秀才當媳婦。時卿落看著蕭秀才家軟弱的娘、柔弱的妹妹和乖巧的弟弟,滿意的摸摸下巴,以後你們都歸我罩著了。從此擔負起了養家活口的重任,種植養殖一把抓,帶著全家去致富,一不小心成了全國首富。蕭寒崢一醒來。原本溺水而亡的弟弟活蹦亂跳,被抓去沖喜而死的妹妹依舊在家,爲了賺錢買藥進深山被野獸咬死的孃親還活著。關鍵是一覺醒來,他還多了個能幹的小媳婦。上到親孃下到弟弟妹妹,全對這個小媳婦依賴喜愛無比。他看著小媳婦:“你養家活口,那我幹什麼?”小媳婦:“你負責貌美如花,考科舉當官給我當靠山。”蕭寒崢早就冰冷的心一下活了,“好!”從此以後擼起袖子就是幹,從個小秀才,一路走到了最風光霽月有勢的權臣。京城裡的所有人都在等著蕭寒崢休了那個村媳,無數大家閨秀想等著嫁給他當繼室,誰知道他卻將媳婦寵上了天。只有他知道,從醒來的那一刻開始,小媳婦就是他此生的救贖。
133.1萬字8.09 195538 -
完結1550 章

穿成惡婆婆后,我讓全村心慌慌
二十歲的林九娘一覺醒來,成為了安樂村三十五歲的農婦五個兒女跪著求她去‘寄死窯’等死,兩兒媳婦懷著娃。母胎單身二十年的她,一夜之間躍身成為婆婆奶奶級的人物調教孩子、斗極品、虐渣已經夠困難了,可偏偏天災人禍不斷。慶幸的是,她空間有良田三千畝,還愁小日子過不好嗎?不過她都老大不小了,他們個個都盯著自己做啥?
302.2萬字8.33 176397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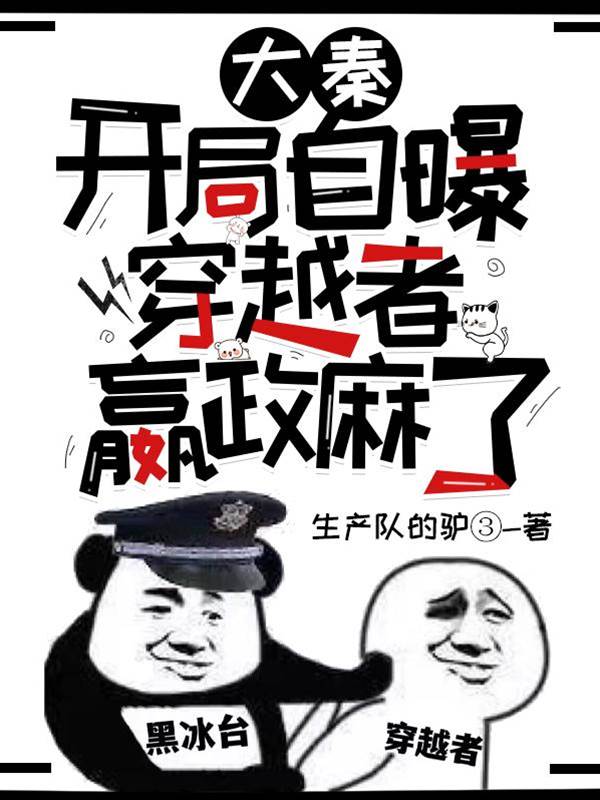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
完結273 章
假太監:從啟蒙皇后開始鳳舞九天
簡介:葉凡穿越到了大興帝國,即將成為太監的他,被皇后侍女劫走了,成為皇后寢宮一個名副其實的假太監。一心游戲的葉凡,當然不會放過最美的皇后,通過不懈的努力,他終于如愿以償,當得知皇后的秘密后,他松開了手……
48.5萬字8 21067 -
完結426 章

穿越獸世,各路大佬追著寵!
【獸世】非女強+1VN+甜寵+系統+種田 家人們誰懂啊! 演唱會上何嬌嬌一腳踏空,醒來已經穿越獸世,想不到獸世的雄性們似乎都是戀愛腦,對她那是一個言聽計從! “嬌嬌,我是的你第一獸夫!”冷峻霸道的蛇獸人吐著蛇信子癡癡望著她。 “嬌嬌,可以多寵寵我麼?”溫柔粘人的大白虎用腦袋蹭了蹭,一臉討好。 “嬌嬌......” 看著獸夫們爭來爭去,何嬌嬌感覺腦袋都大了!
77.2萬字8 1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