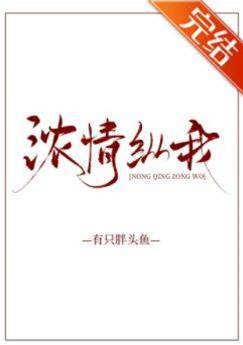《浪漫過敏》 第三章 闕濯給予的安全感
在闕濯面前那群等著與他攀談的人其中也包含了琴琴心目中上流圈的象征——的中年男友。
這在眼中是多麼不可思議的景象啊,那群剛才和對話時還充滿了疏離與矜貴的賓客們此刻在闕濯的面前都像是見到了君王的臣子,姿態卑微地匍匐下來。
剛做好的甲陷掌心,疼痛在不斷提醒,闕濯才是這輩子真正想要的男人。
任開在一邊兒看闕濯連著喝了好幾杯酒,看小書那不時投向闕濯的關切神對今晚之后發生的事已經可以預見,便放心地放下酒杯開始今晚的獵艷。
等到安念念同闕濯離開的時候時間已經十一點多了。
任開早就撤退了,整場的人還在不斷地挽留闕濯讓他多聊會兒,琴琴那中年男友卻直到現在才察覺到年輕妻子已經不在場中,開始到找琴琴的蹤影。
說起來安念念也確實只在開場的時候見到過琴琴——這不太像做事的風格,本來安念念還以為今晚和琴琴會有一場惡戰的。
不過這些都無所謂了,安念念穿著高跟鞋已經站得肚子都在筋,尋思自己今晚也應該算是完了使命,便小心地扶著闕濯往外走。
其實闕濯似乎并不需要攙扶,他走得很穩,雖然喝了很多但看不出什麼醉意。
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安念念覺得就是他的手不知道什麼時候環住了的腰,而且收得很,掌心的溫度穿過輕薄的擺燙著的皮。
闕濯在沒喝酒的時候不可能這麼做,所以安念念判斷他醉了。
回到酒店,闕濯總算松了手。安念念向前臺要回了總裁房間的房卡,畢恭畢敬雙手奉上的時候心中還懷抱著對闕濯酒量的最后一期待:“闕總,這是您的房卡。”
Advertisement
闕濯淡淡地看了一眼安念念手上的東西,完全沒有要接的意思,只是嗯了一聲便直接轉往電梯口走。
安念念只得屁顛屁顛地跟在后進了電梯:“闕總您醉了嗎,要是還好的話——”
電梯門合攏的瞬間闕濯直接側住旁的人。
半醉的闕濯力氣比今天凌晨時分更大,安念念睜圓眼睛的瞬間帶著微醺氣息的吻已經落了下來。
的后腦被闕濯在了電梯壁上,只剩一雙手撐在他的口,毫無作用地維持著兩人之間的距離。
他是真的喝了很多,從口腔到呼吸全部都是酒的氣味。安念念生生地被親了,原本撐在男人口的手臂也為了保持平衡不得不扶上他的肩:“闕總……你、你真的喝多了。”
“我很清醒。”
闕濯聲音有點啞,又是一如既往的低沉。
他很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清醒地知道自己從多久之前就想像現在這樣死死地抱著安念念。
深夜的電梯沒有人在中間上來,一路躥升到酒店的頂樓。
電梯門緩緩打開,但兩個人誰也沒有注意到,只讓它再一次寂寞地閉合。
安念念覺得闕濯這男人是讓人真上頭。
發生了一次還想再來第二次,可一次是烏龍,兩次是失誤,這都第四次了。
安念念啊安念念,闕總就這麼讓你留嗎!?怎麼可以老占人家闕總的便宜呢!
“闕總……”安念念每次都這樣,開始前狗膽包天,進行中興致,但一完事兒就回到小書的位置里去了。
可偏偏子后面的暗扣剛才好像被拉壞了怎麼也摁不回去,只能讓一只手捂著口,畏畏地站在浴缸邊上。
闕濯簡單地沖洗了一下之后關了花灑,看著安念念垂著腦袋跟個小媳婦似的站在浴缸邊一副等候發落的樣子冷聲道:“去洗澡。”
Advertisement
安念念倒是想,可不敢。又瑟了一下:“您、您先洗,我不著急。”
闕濯懶得理:“那你出去。”
安念念就垂頭喪氣地找了另外一間浴室洗了澡,出來的時候闕濯已經換好睡袍坐在最大的那間臥室里了。
那畫面倒是不錯,闕濯這人的氣質天生就和這種矜貴致的地方很合得來。安念念在浴室門口觀了一下,正在糾結自己是回十三樓還是進去征得闕總同意后去側臥睡,就聽臥室里的闕大資本家開口:“你過來。”
安念念一刻也不敢耽擱,顛顛兒地湊上去:“闕總。”
闕濯眉頭一直擰著,見過來閉起眼了鼻梁:“有點頭疼,有止疼藥嗎?”
想也知道是今晚酒喝多了——雖然闕濯不是沒有應酬,但安念念確實很在酒桌上看見有誰敢灌他酒,絕大多數的時候闕濯去飯局酒局都是滴酒不沾,跟個冷面鬼似的往上座一坐,連帶著安念念一塊兒鎮著,別說勸酒了,只唯恐自己哪里招待得不周到。
所以要不然怎麼說安念念不想辭職呢,待遇自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跟著闕濯混確實太有安全了。
只要是跟著闕濯出去的,安念念基本只需要低頭吃飯,偶爾說幾句漂亮話就安穩度過。每次聽祁小沫說自己前一天又陪著去應酬喝到半夜,吐得死去活來,安念念心疼朋友的同時也意識到闕濯作為一個上司,一個領導有多麼的難能可貴。
這麼一想,安念念覺得今天讓闕濯給擋酒確實不好意思的,抿了抿:“我現在外賣點一盒止疼藥應該很快就到,然后在藥來之前……我給您?”
闕濯掀開眼皮睨了安念念一眼,嗯了一聲表示許可之后又重新閉上了眼。
Advertisement
安念念出去找到自己的手包掏出手機,提了外賣訂單之后才輕手輕腳地回到房間,闕濯還是坐在床上背靠著床頭,雙眼閉仿佛已經睡著。
悄無聲息地在床邊坐下,出手用掌心覆住了男人兩側的太。
“闕總,這樣的力度可以嗎?”
沒有回應,應該大概可能是真的睡著了,安念念悄咪咪地松了口氣。
臥房的頂燈在第二次進門的時候就關掉了,只留下床頭的臺燈。暖黃的燈被磨砂燈罩濾了一遍,出來的和芒籠罩在男人堅毅的五上,在闕濯臉上顯出一種不多見的和。
有一說一,還沒有過能夠這麼近距離、長時間觀察闕濯的長相的機會。
安念念看著闕濯眼下一片睫投出來的影,心頭真是忍不住生出一種對這不公的蒼天的哀怨。
一個男的,長這麼好看,睫比還長,合適嗎?
雖然從第一天職起安念念就知道自己的頂頭上司長得很絕,但很敢直接與闕濯對視,主要就是膽子小,不敢。
因為來之前打聽了一下,發現這個闕總的難搞是已經出了名的,對工作要求很高,眼里不得沙子脾氣極差不說,沒事還喜歡板著一張臉散發迫嚇唬人。
安念念一開始還安自己說三人虎,后來職一個月終于確認傳聞都是真的。
但當時的安念念拿到了第一個月的工資,已經嘗到了高薪水高福利帶來的甜頭,兒舍不得辭職跑路,只能鉚足勁好好工作。
這小兩年以來的目標很簡單:不挨闕總的罵,不被闕總炒掉,好好混吃等死。
了一會兒房門口傳來門鈴聲,是客房服務把外賣拿上來了,安念念過去開了門道了謝,就直接在玄關也沒就水直接把藥拆開來干吞了進去。
吃完藥一回頭就看見應該大概可能已經睡著了的闕濯正站在臥室門口看著,趕把止痛藥狗地遞過去:“闕總,您的止疼藥。”
闕濯定定地盯著手上的另一盒藥看了一會兒才出手,接的卻不是藥,而是安念念的手腕。
男人的掌心干燥溫熱,將安念念纖細的手腕握住往自己的方向帶了一步。
剛才他看著安念念自己悄悄吃藥,腦海中忽然又想起一件以前的事。
在安念念職之前,他前任助理無一例外全都是男的,那些人也都默認跟著這種公司總裁工作,就得會喝酒,所以每次出去應酬,觥籌錯都是必修課,從來沒人提出過異議。
所以闕濯一直覺得這種事理所當然,頂多喝醉之后他的司機多送一個人回家就是了。
直到后來有一次,他帶著安念念去了一個酒局。
那是一個特別喜歡收藏紅酒的老板,他很熱地邀請他們去了他的酒莊,當時大家的興致都很高,紛紛舉起了酒杯。
其實很多時候,比起勸酒,更讓人難以拒絕的是氣氛到了。
氣氛一到,誰不喝就變了格格不的那個人。
安念念當然不敢在這個時候敗了其他人的興致,那天晚上就那麼陪著,一杯接一杯地喝。
沒說自己不能喝,又不是喝一點就上頭的類型,闕濯看不出的任何異樣,直到后來安念念去了廁所很久沒有回來,才發現抱著洗手臺已經吐得起都起不來。
“安書?”
他當時就站在后,看見在聽見自己聲音的那一刻,就像是條件反一般從包里掏出解酒藥。
那個藥闕濯也吃過,最多一次也就吃個四片兒,但安念念一口氣掰了七八片下來,就準備囫圇地往里塞,一邊塞還一邊口齒不清地回應他:“哎,闕總我、我馬上好……”
后來闕濯也忘了自己是怎麼從手里搶下那幾片解酒藥的。
他只記得當時嗓子眼憋著一口氣,直接跟客戶道了別,帶著安念念離開了客戶的酒莊。
回去的路上,安念念已經快要不省人事,卻好像還能覺到他不善的臉,小聲地跟他道歉:“對不起啊闕總,其實我酒量……有點差。”
闕濯當下,更好奇的其實是安念念以前到底遇到的是什麼樣的老板。
讓養了這種打落牙齒和吞,有困難一言不發只往自己肩上扛的事方式。
后來,闕濯在飯桌上就盡量再不讓安念念陪酒。
久而久之,安念念也把這件事兒給忘了,只記得跟著闕濯時不用陪酒陪笑臉的那種安全。
“闕總?”
時間回到現在,安念念被牽著愣愣地跟在他后走了幾步才反應過來:“您不是頭疼嗎?”
“睡一覺就好了。”
這話不說還好,一說,闕濯頓時覺安念念往后退了一步,原本微微彎曲的細白手臂被拉直,場面立刻陷僵局。
他擰眉:“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
昨晚的事還歷歷在目,安念念鼓起勇氣聲音卻還是小得不行:“您的睡相有點兒……”
安念念的訴求很單純,只是想今晚睡個好覺,但闕濯只覺自己遲早有一天要被這塊木頭氣死。
安念念就看著男人的面一下沉到了底,松了的手腕便直接從這偌大的臥室走了出去,與肩而過進了另一頭的側臥,徒留一人站在原地發懵。
闕總他變了,他變得不能坦然接自己的缺點了。
這趟公差出得也算是飛狗跳,安念念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約祁小沫出來逛街,拉著足足吐槽了三個小時才把這次出公差遇到的事給說完。
“我突然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祁小沫聽完沉默了半天,安念念一聽這開頭就知道在想什麼,趕先把這萬惡的想法掐死在搖籃里:“不,你沒有。”
“行行行,你說沒有就沒有吧。”祁小沫笑得花枝的:“那至今年的圣誕節我能不能提前先預約一下啊,我這個孤家寡人實在是不想自己過圣誕節啊。”
安念念明明進商場之前還看見了商場門口的巨大圣誕樹,卻直到現在聽祁小沫這麼說了才覺圣誕確實是快要來了。
對于單狗來說圣誕節確實不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日子,安念念當然也不想一個人過圣誕,趕應下,然后倆人就圣誕節要去吃什麼干什麼又熱烈地討論了一個多小時。
兩個人吃完晚飯準備回去,路上祁小沫開著車還不忘調侃安念念:“不過我也確實佩服你啊,那麼一個大帥比當你上司你還能把持一年多,要我啊……說不定職一個月就把他給拿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627 章

大佬的小嬌嬌又崩人設了
遲家大小姐在山村裡養了十六年,忽然回c市了,不過很快就被人發現,這位大小姐的畫風有些不對勁。第一天,狗仔就拍到了她和影帝同框吃飯的畫麵,照片被迅速頂上了熱搜。影帝別亂猜,她是我老大,我是她小弟。吃瓜群眾信了你的鬼!第二天,狗仔又拍到了金融巨頭當街為她係鞋帶,再次上了熱搜。某金融巨頭別亂猜,她是我老大,我是她的小弟。吃瓜群眾⊙…⊙第三天,狗仔又又拍到了醫學界大佬送她去學校,又一次承包了熱搜。醫學界大佬不好意思,她是我老大。吃瓜群眾!!!說好的花瓶小嬌嬌呢,畫風越來越崩壞。正當吃瓜群眾逐漸習慣遲嬌的操作時,有一天,狗仔又拍到了她和權家掌門人權玨一起進了民政局。人人都說權家掌門人權玨
138.6萬字8 61840 -
完結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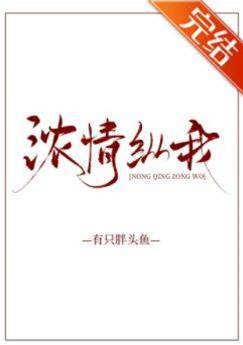
濃情縱我
宋傅兩家聯姻告吹,所有人都以為,深情如傅北瑧,分手后必定傷心欲絕,只能天天在家以淚洗面療愈情傷。 就連宋彥承本人,起初也是這麼認為的。 直到有天,圈內好友幸災樂禍發給他一個視頻,宋彥承皺著眉點開,視頻里的女人烏發紅唇,眉眼燦若朝瑰,她神采飛揚地坐在吧臺邊,根本沒半點受過情傷的樣子,對著身邊的好友侃侃而談: “男人有什麼好稀罕的,有那傷春悲秋的功夫,別說換上一個兩個,就是換他八十個也行啊!” “不過那棵姓宋的歪脖子樹就算了,他身上有股味道,受不了受不了。” “什麼味道?渣男特有,垃圾桶的味道唄!” 宋·歪脖子樹·彥承:“……?” 所以愛會消失,對嗎?? - 后來某個雨夜,宋彥承借著酒意一路飆車來到傅家,赤紅著雙眼敲響了傅北瑧的房門。 吱呀一聲后,房門被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男人矜貴從容,抬起眼皮淡淡睨他一眼:“小宋總,半夜跑來找我太太,有事?” 這個人,赫然是商場上處處壓他一頭的段家家主,段時衍。 打電話送前未婚夫因酒駕被交警帶走后,傅北瑧倚在門邊,語氣微妙:“……你太太?” 段時衍眉梢一挑,側頭勾著唇問她:“明天先跟我去民政局領個證?” 傅北瑧:“……” * 和塑料未婚夫聯姻失敗后,傅北瑧發現了一個秘密: ——她前任的死對頭,好像悄悄暗戀了她許多年。 又名#古早霸總男二全自動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就被死對頭扛著鋤頭挖跑了# 食用指南: 1.女主又美又颯人間富貴花,前任追妻火葬場,追不到 2.男主暗戳戳喜歡女主很多年,抓緊時機揮舞小鋤頭挖墻角成功,套路非常多 3.是篇沙雕甜文 一句話簡介: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跟死對頭跑了 立意:轉身發現新大陸
23.5萬字8 27578 -
完結805 章

聶少的落跑前妻
“離婚吧,她懷孕了!”夫妻歡好后,聶擎宇扔給她一紙離婚協議書。安然想不明白:他只是出國一趟,把腿治好了,怎麼又把腦子給治壞了呢!直到有一天,她發現了一個驚天秘密。“你不是他!”她瘋狂地撕打他,“騙子,你把他還給我!”“還給你?”他嗜血冷笑。“不可能!不如你把我當成他,反正我們倆很像。”她轉身離去,男人卻日日夜夜糾纏不休。“乖,讓老公疼你!”聶擎宇強勢將她擁入懷中,柔聲低語:“老公只疼你!”
196.8萬字8.18 144900 -
完結1020 章
骗个大佬当老公
被催婚催到連家都不敢回的慕晴,為了能過上清靜的日子,租了大哥的同學夜君博假扮自己的丈夫,滿以為對方是個普通一族,誰知道人家是第一豪門的當家人。……慕晴協議作廢夜君博老婆,彆鬨,乖,跟老公回家。
97.2萬字8.18 164027 -
完結304 章

分手后我嫁給了前任小叔
本就是天之嬌女的孟音,一朝家破人亡,明珠成泥碾作塵,眾叛親離終於覺醒。 原來相伴多年的愛人不過是貪圖她的權勢,自己竟一直在為仇人賣命。 為復讎,她強闖進渣男小叔沈霆川的房間。 “沈二叔,求你娶我!” 眾人都嘲她不自量力,畢竟眾人皆知沈霆川清冷禁欲,不沾女色。 孟音也以為這是一場交易,卻不料假戲真做,發現為時已晚...... 他封鎖醫院,眾目睽睽下將她粗暴帶走。 “利用完就走,還敢帶著我的孩子跑?” 人人以為孟音慘了,等到再次現身,孟音盛裝出席,手上的結婚戒指閃瞎了眾人的眼。
52.5萬字8 302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