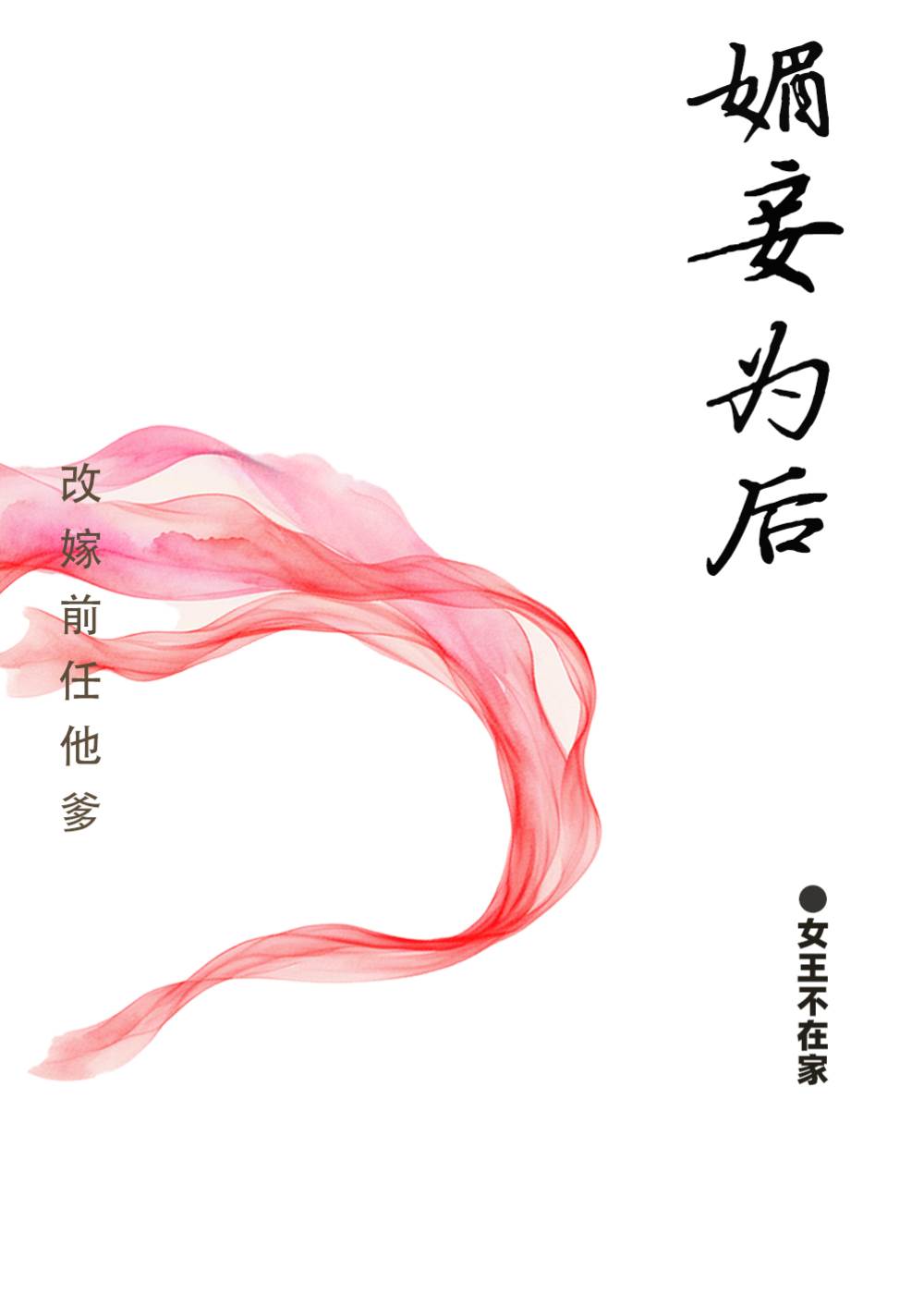《媚君榻》 第2章 這麼快就完事了?
皂吏頭子才一進門,就急不可耐地去扯江念的衫。
江念忙側一避,后退兩步,從上出一,雙手奉上,低聲道:“大人!奴家奉上一些小,請大人笑納,求大人看顧一二。”
皂吏頭子見人躲閃,心里正待火起,然而在見到人掌心的東西時,睜大了眼,那是十幾顆米粒大小的翠珠,剔無瑕,一看就不是普通行貨。
這些翠珠是江念從自己的小扯下的,喜歡發發閃的東西。
從前在家中,縱然不出門,也要將自己打扮得珠翠滿頭。
富麗炫彩的珠寶和繁瑣層疊的裳,非但沒住,反把襯得更艷絕俏麗,玉骨玲瓏,換作任何人都撐不起這份厚重的奢靡。
別家的貴,的以舒適為主,哪怕面料再稀貴,也不會在上面綴金玉,江念偏不,特特代下去,無論外還是里,都要綴上名貴的細珠,恨不得連那繡線,都要用金銀的才好。
舒不舒服另說,只有這樣,方襯得起的貴重。
一朝從天上跌到地上,摔得筋骨盡斷,唯有小上還殘有一點點富貴的影兒。
這皂吏頭子也不傻,看了那翠珠幾眼,明白了人的意圖,為何剛才在外面不拿出來,等進側屋才獻出,若是在外面現眼,那便是見者有份,而現在嘛……自然是他一人的。
Advertisement
如此一來,他想盡吞這些珠寶,便要護著,否則嚷一聲,讓其他幾人知道,都是一共事的,他不吐點出來?
男人攤開手,江念將翠珠奉上,皂吏頭子在手心拉幾下,轉而放懷里,有了這些珠子,后半輩子吃穿不愁。
不過,他心里有些不痛快,反口道:“我若說不呢?”
江念先是一怔,繼而笑了笑:“大人大量,您高高地抬一抬手,咱們這些人便能好活一分,再者……”
“再者什麼?”
江念往前進了兩步,揭開袖,出胳膊:“大人,您看看。”
男人睜眼看去,只見那細瘦如柴的胳膊上,干裂發紫不說,還起有蠶豆一般的疙瘩,好些已經連一片,看著甚是可怖。
皂吏頭子唬得往后一仰,把手連擺:“去,去,離遠些。”
“大人送完這一趟,差事就付了,歸家可盡富貴,何必讓咱們這些人污了您。”
皂吏頭子不耐煩地驅趕:“還不出去!”
江念暗暗松下一口氣,應聲退出。
前一腳走,皂吏頭子后一腳出來,屋外的幾個皂吏調侃:“這麼快就完事了?”
“那人染了臟,又開始發病,你們離遠些。”皂吏頭子盤坐下,一路上病死了不知多人,偏這人賴活到現在。
其他幾人心中有數,只想快些將人付,好返程。
江念走回囚犯堆里,坐下。云娘眼含擔憂地看著。
Advertisement
“無事。”
江念說完,扯了扯袖,將自己的胳膊蓋住。臟下的皮火辣一片,忍不住去撓,越抓越,越越想抓,不一會兒,袖上浸出點點斑。
皂吏頭子往對面斜了一眼:“去,拿些吃的給他們。”
矮個兒皂吏應下,撿了幾個冷的干饃,也不靠近,距囚犯們一之地,將饃丟了過去。
十來人的囚徒見了食,一擁而上,就為了搶幾塊干饃,搶到便能吃上一頓,搶不到的只有著。
江念和云娘兩個子哪里搶得過那些男人。
好在其中一個干饃朝另一邊滾去,其他人沒注意,江念迅速爬去,那不規整的圓形干饃往門邊滾,手去夠,就要上之時,木門“吱呀——”開了,驟然間,刺骨的風雪呼呼灌。
門欄外的風雪中立了許多人,當先一人拔步而。干饃滾到那人的長靴前停下,江念的眼睛從饃移到那雙錦靴上,靴底沾了雪沫,靴面掐著祥云金邊,再抬眼往上一點點看去。
男人量十分高大,在刺目的中,看清了他的臉,這張臉同記憶中另一張模糊的容漸漸重疊,一點點清晰……
那一年,祖父還在世,江家圣恩正隆,權尊勢重。
京都城外,景芳菲,香車寶馬往來,游人不斷。兩輛亮漆鏤花的高闊馬車一前一后緩行,其中一輛馬車尤為顯眼,左右車窗的絹紗在風中飄飐,可窺見車盛服麗妝之影。
Advertisement
后面還有幾輛小一些的馬車,坐著丫鬟和婆子,另有護衛前后簇擁隨護。
車馬輕快,趁著今兒天氣暖融,江夫人帶著自家小去寺廟進香。
浩浩的人馬引得不路人關注,這是江府的車馬,不用猜,那鮮亮的馬車端坐的定是江府千金,江念。
這一年的江念才十二三歲,正值豆蔻年華,已然出落得姿容殊麗,有絕。
眾人無不嘆,有些人生來就得上天眷顧。路人為了多看一眼車中麗人,或是得多看一眼,跟著馬車小跑起來。
趕車的馬夫早已見怪不怪,他家小娘子出行,每每都要引起,一聲駕呵,馬車轆轆快行,將跟隨的路人甩在后。
“娘子,你看那些人,居然追著跑,也不怕灰嗆了鼻。”丫鬟秋水揭開窗紗看了一眼外面,掩嗤笑道,順帶打量了一眼主子的面。
在看來,家娘子的那雙眼是最好看的,眼褶不深不淺,看人時,著明的,點點的含蓄,很容易讓人在無知無覺中陷進去。
然而,明的眸子下是一管直隆隆的鼻,分外秀,再配上小巧傲然的下,生生把那眼中本就不多的含蓄和嫻靜碎了。
“莫要取笑人家。”江念將帕子塞到腕間的玉鐲里,肘在窗案上。
秋水將枕往主子腰后塞了塞:“前日侍郎家公子在茶樓題詩相贈,昨兒畫舫上還有人擲來并蓮,奴婢倒要看看,今次禮佛路上還能見著什麼新花樣。”
話音未落,忽有年郎拋來一枝杏花,驚得拉車的棗紅馬打了個響鼻。
江念眼中淡淡的,卻也安然地著這份毫無意義的虛榮。
行到半路,窗外傳來喧嚷之聲,隨之馬車停下,江念側目,隔著輕紗看去,只見前路圍聚了不人,相互談論著什麼。
“嘖——真是可憐——”
“造孽喲!”
“不像咱們大梁人……”
人群隨著護衛清道,散開了,原來人群圍攏,躺著一個小人兒。
那人蜷著,不蔽,臉偎在胳膊下,渾抖著,若不細看,多半以為是一條半死不活的野狗……
猜你喜歡
-
完結1192 章

六宮鳳華
狠辣無情的謝貴妃,熬死所有仇人,在八十歲時壽終正寢含笑九泉。不料一睜眼,竟回到了純真善良的十歲稚齡。仇人再一次出現在眼前……算了,還是讓他們再死一回吧!
206.8萬字8 131377 -
連載915 章

王爺鄰家大小姐看上你了
【甜寵日常】【先婚後愛】+【救贖】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
168.2萬字8 5532 -
完結159 章

做妾?笑話!她撕毀婚書另謀高嫁
【女強男強 雙潔 重生爽文 家國天下】她是名震天下的女戰神,本領強悍,戰術無雙,一朝重生到大雍鎮國公府被汙了清白的嫡女身上,號稱溫潤如玉的未婚夫上門退婚,要把她貶為妾室,親人們個個視她為恥辱,認為她做妾室也該感恩戴德,她毫不留情廢了賤男一隻爪子,與道貌岸然的親人正式決裂。 誰料一道旨意從天而降,竟把她賜婚給了那位傳說中殘暴嗜殺權勢滔天的攝政王,引起滿城嘩然。 當殺伐果斷攝政王遇上雷霆風行女煞神,天下誰敢爭鋒?滅了渣夫嘎全家,揮軍報仇掌天下。
26.6萬字8.33 79478 -
完結53 章

這通房還行
裴府上下皆傳: 主君的身體狀況很不樂觀,太夫人正在四處找尋合適的女子,送到主君屋裏給裴家留個後。 路過的小廚娘阿玖搖了搖頭,“聽起來好像給豬配種哦。” 剛入秋就身披厚氅、揣着暖手爐的主君:“……” 當晚,阿玖就被送到了主君的寢居。 阿玖是個鄉下來的小丫頭,一頓能吃三碗飯,嗓門還賊大。 考問她灶間香料估計能講得頭頭是道,可伺候養尊處優的主君,甚至當未來小主君的孃親,那就差些檔次了 ——裴府上下,從太夫人到伙夫都這樣想。 可阿玖非但沒被主君趕出來,反而一晚一晚地留下。 後來,小主君誕生了,主君的身子也漸漸好了起來。 太夫人:……也,也行吧。 【小劇場】 這一年冬天,裴延終於不用困在屋內喝那些苦湯藥。 他沉着臉跨上馬背,於簌簌飄雪中疾馳,攔在阿玖的牛車前。 眼神冷如霜刀,問出的話卻是可憐巴巴:“你不要孩子就算了,連我也不要?” 懷裏被顛吐了的小裴:? 阿玖咦了聲,從牛車探出頭來,“不是說留個後嗎,我完成任務可以回鄉下啦,表哥還等着……唔。” 小裴捂着眼睛跑開了。
22.7萬字8 9528 -
完結2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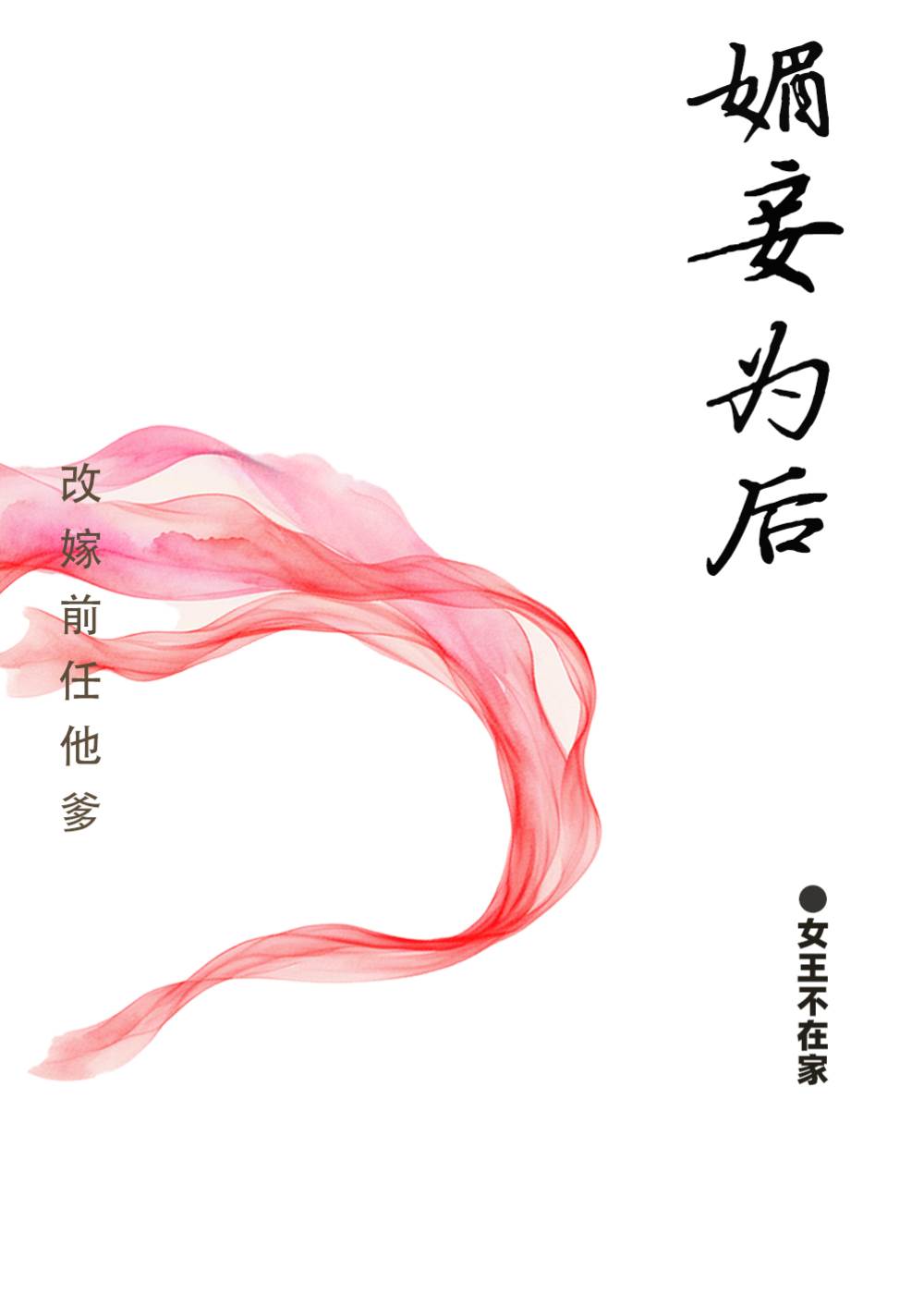
媚妾為后
景熙帝性情肅厲冷漠,不喜女色,膝下只有一太子 太子清風朗月一般的人物,對於這個兒子景熙帝勉強還算滿意。 誰也不曾想到,年少的太子竟因寵溺一美貌侍妾,和太子妃不睦,鬧得雞飛狗跳。 據說此侍妾頗通媚術,且愛財如命。 景熙帝看了眼那侍妾畫像,頗爲鄙薄,一看便是不安於室之輩,如此輕佻女子,留在太子身邊終爲禍患。 他一個御令,命那侍妾削髮爲尼。 太子:“父皇自是不懂阿嫵是何樣女子!” 景熙帝:“朕需要懂嗎?” 太子跪求半日,奈何景熙帝鐵石心腸,太子不得不退讓。 消息出來後,阿嫵並無不快,她哭唧唧向太子告別,順手訛了太子一大筆銀子。 之後她收拾包袱,準備去當一個有錢有閒的快活小尼姑。 誰知道那一日,她無意間闖入一處溫泉,跌入其中,並撞入一精壯男子懷中。 這就是景熙帝。 —— 年輕的太子闖入御書房,他憤憤地道:“父皇不讓兒臣留下阿嫵,結果父皇竟霸佔了阿嫵。” 景熙帝望着自己一手栽培的太子:“天下女子,除了阿嫵,你可以隨意選,朕不再幹涉。” 太子顫巍巍地拔出了腰間佩劍,咬牙切齒:“可兒臣就要阿嫵。” 景熙帝的手按在御案上,面無表情地道:“她已經是朕的后妃,你應該知道該怎麼稱呼她。” 太子泫然欲泣:“父皇,兒臣,兒臣,父皇怎麼可以!怎能,父皇——” 景熙帝淡淡地道:“那日你說朕不懂,現在朕只是懂了而已。”
56.6萬字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