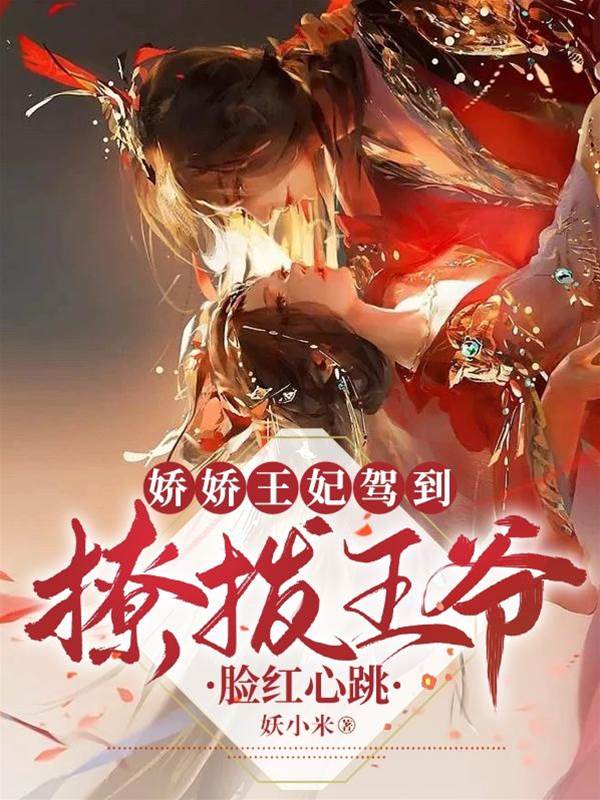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媚君榻》 第16章 狼窩里長大的鷹
蘭卓來之前去了一趟正殿。
正殿外,沿階立著兩排宮婢,宮婢們上的衫以杏黃的妝花緞制,散闊領,坦出大片的脯。
殿傳來羹匙磕聲和微不可聞的行止響。
男人坐于桌邊,一手端著碗,輕輕攪著調羹,就那麼有一下無一下地攪著,眼睛直直看著某一個地方,不知在想什麼。
男人的后立著幾個錦華服的艷宮婢,款段玲瓏。
大宮婢木雅覷了男人一眼,他的面前是心布好的菜饌,也未。
蘭卓躬進來,走到廳前,朝上行禮。
“王,奴婢有事稟報。”
呼延吉放下手里的碗,點點頭,木雅會意,招了招手,領著一眾宮婢、侍奴退下。
“何事?”呼延吉問道。
“梁延誤了飯點,在值房后用飯,同一道當值的另幾個宮婢,有意難為,還……”
“還什麼?”
“還砸了的飯碗。”
剛才下面的人向傳報,值房有人鬧事,而鬧事的人中有那個梁。蘭卓先前得了王的囑咐,有關梁的向,不論大小,事無巨細向他回稟。
就是東殿的朵夫人,大王也只是代宮侍們,夫人有恙時,報知他。
“不若……老奴前去,借此機會敲打敲打另幾個宮婢,殺儆猴,以后也無人敢欺負于。”
Advertisement
“不必。”呼延吉把子往后一靠,兩條臂膀搭于椅扶上,雙手叉握在前,“照著規矩辦,該當如何便如何,豈能由著來,得讓吃吃教訓。”
既是王令,蘭卓應下,就要退出,卻又被上頭那位住。
呼延吉看了一眼桌上沒過的菜饌:“本王今日沒甚胃口,吃不下這些東西,裝起來,賞給下面人吃罷。”
蘭卓先是一怔,轉瞬明白過來,連連應下……
……
江念回到后湖,蹲在青石階前,指尖拂過磚里新冒的綠芽,掌心火辣辣地疼。方才那三十板子得手心疼腫,稍一蜷指如同著團炭火。
將裾掖在腰間,出半截碧襯,腳沾著泥點子。
剛才蘭卓問清掃哪一片,回說后湖,蘭卓沒說其他的,只點了點頭,今日,若不將后湖清出個樣子來,又是一條罪名兜頭扣下。
后湖的殘荷在溫風里打著旋兒,柳條掃帚歪在太湖石旁,活像被了筋骨的青水袖。
淺草叢中,一雙翹頭平底繡鞋,齊整整并著,旁邊散著一件棗紅衫,而在它們的不遠,子赤著腳,寬大的管挽至膝上,腳踏在草叢與湖泥的界邊,手拿一長耙,夠著湖泥里的枯枝敗葉。
江念抬起手,用腕子蹭了蹭額汗,不盡興,又用腦袋去夠肩膀,把鬢間細小的碎發蹭到一邊,攢在一。
Advertisement
待將湖邊清理得差不多時,蒼青的暮已爬上灰白巖的宮墻。
“當心摔個泥菩薩。”一個聲音響起。
江念回過頭,發現是阿星和阿月兩人朝這邊急急行來。
“你們怎麼來了?”
阿星笑道:“我們過來幫你。”
“這園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原是一片荒廢的園子,不必清掃,上面也沒人過問,讓你一人來,三日也清理不完。”阿月轉過頭,四圍看了看。
江念擔憂道:“你們不當值麼?莫要為了我誤了事。”
阿星一面走到太湖石邊擒住掃帚,一面說道:“我和阿月下值了,紅珠姐晚些時候才下值,咱們快些整理罷,完事了好回。”
有了兩人的幫忙,作快了許多,積年的塵灰化作霧,裹著西曬的日頭洇出晚霞,待日頭沉到飛檐浮后頭時,廢園竟顯出幾分清貴相。
江念的腳上、手上沾著泥,園子里湖水干涸,只有一塘的稀泥,沒法清洗手腳上的臟污。
只好拿出帕子胡將腳底拭凈,也不著,著腳套鞋中,隨即打下擺,將腳掩于底。
低等的宮婢服為了做事方便,衫長度只及小肚,實是遮蓋不住什麼。
天漸暗,三人往下人房中快速行去。
“阿念,我聽說了,蘭阿姆那樣問你,你都未將我供出,當真是條好漢。”阿星踮腳去夠轉角的柳枝。
Advertisement
江念撐不住吃吃笑起來:“你還說,蘭阿姆眼風掃過來,我膝頭得跟新蒸的米糕似的,再多問一句,指不定我就說了。”
阿星和阿月聽罷,也跟著笑了。
“在這西殿里,倒也還好,大王并不是那等嚴苛之人,我曾聽人說,前些時,有個侍奴打翻硯臺,污了軍報,大王只他重謄一遍便罷了,連句重話也不曾說,這次也是背運,讓人報知了蘭阿姆。”阿星說道。
阿月在后頭掩兒笑:“這話說得,倒似咱們大王是菩薩座下的善心子。”
江念角抿出輕微的彎弧,輕聲呢喃,以為沒人聽得見:“狼窩里長大的鷹,偏要裝家雀兒,他那顆心也就比家雀兒大點兒……”
話尾突然斷在風里。
游廊拐角轉出一個暗影,金線繡的圖掠過暮,利爪正對著驟然蒼白的臉。
呼延吉停在十步開外,腰間玉帶映著殘。八個錦侍從綴在左右,后還跟著一眾侍奴、宮婢。
阿星手里的柳條“啪嗒”墜地,阿月低著頭往影里。
江念屏息斂氣,不敢抬頭,耳墜上沾的霞凝琥珀,在漸濃的暮里晃啊晃。
“接著說。”呼延吉挲著拇指上的扳指,寬大的袖被風吹得鼓獵作響,“狼窩里的鷹該如何置規矩的婢子?”他往前幾步,一步一步近。
以只有二人聽到的聲氣說道:“用‘江念’的口吻告訴我。”
人渾一震,明白他的意思,他讓用“江念”的語調說,那個言辭蠻厲,高傲不可一世,話頭不饒人的惰貴。
江念盯著他晃的襟,頭忽然哽住,說出的卻是:“該剜了眼珠子給大王賞玩。”
呼延吉低笑起來,笑聲泠泠如碎冰相擊:“對嘛!這才是你,何必可憐兮兮的,沒得讓人以為你是良善人。”
呼延吉突然手抬起人的下,冷的扳指硌得人生疼:“這般伶牙俐齒……”拇指重重過流暢的下頜,“三十板子倒是打輕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5 章
愛妻帶種逃
那婚前就放話不會把她當妻子看待的夫君,八成犯傻了,不然纔剛摔了交杯酒要她滾出去,怎麼一見她的手腕就變了,還是他真如傳言「生意做到哪,小手摸到哪」那般有戀手癖?要不爲何一眨眼就對她又是愛憐呵護又是纏綿求歡的……寵她之餘,還連所有她在乎的人也都一併照顧了,他說唯有這樣,她纔不會分心去擔心別人,能好好被他獨佔,他說不許她哭,除非是他的愛能寵她到令她流出幸福的眼淚,他說了好多好多,讓她甜上了心頭,也被他填滿心頭,然而也因爲他說了好多,讓她忘了問他爲何對她這麼好,纔會由上門「認親」的公主那兒得知,其實他寵的人不是她,他愛的是前世妻子,而自己手腕上的胎記讓他誤認了……而同時擁有胎記和記憶的公主,似乎纔是他尋尋覓覓的人,她想,他曾給了她那麼多幸福,這次,爲了讓他也得到幸福,即使已懷了孕,即使再痛苦,她都要將他還給他真正愛的人……
8萬字7.82 12634 -
完結154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275.8萬字8.17 60069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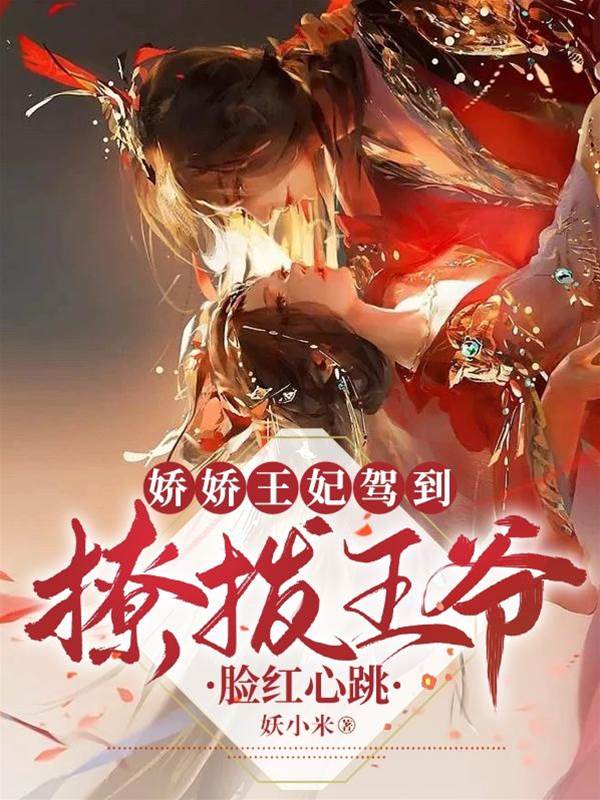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109 章

承秋波
東宮謀逆,北寧伯府做了件不大不小的錯事,但若要嚴辦,整個伯府都得出事,全家老少戰戰兢兢,生怕殺頭的禍事臨身。 伯府老夫人把孫媳林昭昭叫來,沉重地說:“昭昭,你得救救伯府。” “處置此事的,是靖國公,聽說你們林家以前和靖國公府頗有私交,試試看,能不能讓國公爺通融通融。” 林昭昭:“……” 老夫人不清楚,當年她可差點嫁給靖國公,是她夫君“橫刀奪愛”。 試試倒是可以,只是,依靖國公那脾氣,只怕試試就逝世。 * 靖國公府的老人都知道,公爺裴劭年少時有一段求而不得,大家都以爲,那女子已然仙逝,成了公爺的白月光,讓這麼多年來,公爺絲毫不近女色。 卻不曾想,原來公爺心裏裝的白月光,竟已嫁給他人。
16.6萬字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