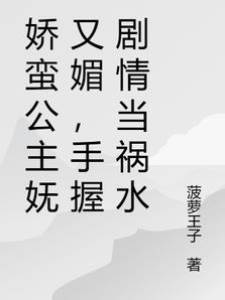《嬌養》 第22章 玩骨牌
第22章 玩骨牌
秦知宜的傷是短暫的。
謝晏手裏的茶水還沒喝完,就已經重振旗鼓,眉開眼笑地帶著兩個婢在茶案對坐,玩骨牌消磨時間了。
這是一副用瑪瑙制的彩玉骨牌,一套三十二張,選的俱是一樣純淨無暇櫻桃紅的老坑瑪瑙。
若枝頭剛曬紅的櫻桃,質地清水潤,淡雅縹緲。
被子以纖纖素手撚著,優雅華,不知有多貴氣。
若不是早上整理東西,從添妝裏找到這個,秦知宜都忘了,閨中好友姜姒說給的添妝禮,是一件籌備了兩年的好東西。
秦知宜視之貴重,出嫁前沒拆開看,又放在嫁妝箱底。
昨日整理時翻出來拆開,就立即讓人送到正房裏,放在手邊隨時欣賞把玩。
上午忙了正事,下午該歇息了。
姜姒的禮這樣用心,且投其所好,必然要好好珍惜,把玩夠本。
秦知宜沒骨頭似的歪斜著子,最是舒服愜意,手臂撐在案上,不釋手地著骨牌。
只是把玩,把三十二張牌擺來擺去,細看瑪瑙的,幾個人都玩了許久。
玩著牌,又說著從前閨中趣事,還有姜姒那幾個與秦知宜好的姑娘,一下午時間都不夠用。
謝晏被秦知宜徹底拋在了腦後。
自在,他也自在。
夫妻兩個各忙各的事,這才是婚後第一次井水不犯河水。
但“井水”安心,“河水”也歡暢。
只是,前幾日天天早睡,每每天暗不久就沐浴躺床的秦知宜,今天玩樂開懷,以至于忽略了時間。
直至戌時末,還沉浸其中無法自拔。
前幾日謝晏不用早睡,依著的起居習都早睡了。
明日他要上朝去府,必須早睡的時候,秦知宜還在不亦樂乎地玩骨牌。
這兩人,總是合不到一起去。
Advertisement
不過,和秦知宜一樣,謝晏也沒催促,只是讓玉堯知會一聲。
他先行睡下了。
玉堯來報時,秦知宜擡頭看,大眼睛茫然懵懂。
“夫君今天睡這麽早嗎?”
玉堯含笑提醒:“夫人,已經進巳時了。”
“已經巳時了?”秦知宜喃喃,還有些不敢信。
但只是個人覺,并不是懷疑。玉堯這樣幹的人,總不會說錯話的。
小柳氏那邊早就已經把水備好了,一直等秦知宜發話,是玩牌太專注,忽視了時間。
秦知宜記得謝晏明日要早起上朝,恐怕再過兩三個時辰就要起了,耽誤不得。
放下骨牌起。
“把東西速速收好吧,快些洗漱睡覺了。”
謝晏邊的人默默等了許久,總算是等到夫人結束玩牌,都暗暗松了口氣。
世子上朝是大事,要是耽誤了,就算秦知宜人再平易近人,也是會遭人詬病的。
人的名聲如何,并不是一昧脾氣好、沒壞心就行的。
多得是人心地純良,但誤人子弟,或好心辦壞事。
頭腦愚蠢的人,甚至比刻意為之的壞人還要容易壞事。
這些天,原世子院的下人看著,雖喜歡秦知宜的為人,卻擔心不堪大用。
方才謝晏已睡了,還在玩樂,人人上不說,卻免不了心裏有怨言。
急著睡,秦知宜便沒沐浴,簡簡單單刷牙淨面泡腳,了外就往床上爬。
謝晏睡在床外圍,平躺著閉目。
一不的,不知道睡沒睡著。
秦知宜像是翻山越嶺一樣,從他上方爬到側,鑽進被窩中。
有謝晏提前睡,褥子裏一片暖意,從上到下無一。
秦知宜小幅度挪,朝謝晏邊靠攏。
分辨不出,以為他已經睡著了。
然而謝晏其實還一派清醒,盡管沒有睜眼,秦知宜的一舉一都被知到了。
Advertisement
也不知道是以什麽姿勢爬上床的,竟然連一點腳也沒到謝晏上來。
他只覺到兩邊的床鋪,被人按後的明顯下陷。
隨後,鑽了進來,輕輕在他邊。
沒看到什麽況,但只憑這些,也會讓人想象到場面的有趣。
但因為要盡早睡,謝晏只是輕如微風地舒展了下眉眼,并未睜開眼和秦知宜說什麽。
秦知宜也就無從得知他心中所想了。
隨後,誰也沒靜,維持一個姿勢靜靜躺著,直至沉夢鄉。
當朝皇帝是間日朝會,每隔一天一小朝,七天一大朝。
員卯時正需在宣政殿外等候。
因此上朝日時,員五更天之前就要起,趕路宮。
時間之早,說是披星戴月也不為過。
在秦知宜睡得還七葷八素偶爾夢囈時,謝晏醒來起床。
或許是婚嫁的幾日以來,日日被秦知宜帶著賴在床上,給人養出了惰,謝晏很久沒有覺起床是這麽艱難的事了。
醒是醒了,卻仍想舒坦地留在溫暖被窩中。
似乎有種魔力,讓世間一切被被褥隔絕在外。
外面寒風肆,只有床帳中這一小方天地是怡神仙境。
得虧謝晏是嚴于律己的人,他只是側目看了秦知宜兩眼,就默默地掀開被角,站起來。
的惰完全被清醒的理智制。
起過後,謝晏又將他睡的外側的被褥給好。
很難忘掉,前幾日秦知宜控訴他起床後不管褥子,了冷風,讓滿是委屈的事。
雖說那日事發突然,是見的意外,并不是謝晏心大意故意為之。
可在與秦知宜親之前,謝晏獨自睡覺,從沒有過起床後需要管顧被褥的事。
邊多了一個,不止是多個夫人的事。
謝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被牽一發而全地改變著。
Advertisement
不是很習慣,但他又必須要慢慢地習慣。
之前已發生的種種事跡,以及之後還會多出來的許多意外況。
放下床帳之前,謝晏又扭頭看了一眼。
見秦知宜一無所查,仍睡得香甜,便放下床帳去了外間。
是簡單一眼看到底的。
易知足又睡得,不論是清醒的時候,還是睡著後,都不會輕易地被他人的行為“改變”。
謝晏去了另一個小室穿洗漱,著中,又穿戴好深綠朝服、革帶、玉佩錦綬,頭戴進賢冠,簪白筆。
肅穆端正的服上,比起平日穿戴簡潔時,更添幾分不可的肅正之姿。
若秦知宜醒著,恐怕都忍不住要多看幾眼。
謝晏在朝堂之上,是數一數二相貌出衆的俊仕,連從前的第一男子,禮部主事蕭卿之都要甘拜下風。
因為謝晏生得明朗英氣,比蕭卿之還更高挑。
從氣勢上就了別人一頭。
今日宣政殿外,早到的員不多。
往常謝晏只與相的員問好,簡單談幾句。
但今日是他婚假過後首次臉,不人見到他,都是帶著笑意稱呼一聲“新郎君”,略帶調侃地說他意氣風發。
謝晏點頭應了。
他只覺得同僚都是有意調笑,說的并非事實。
因為從鏡中看,謝晏覺得自己并無變化。
何來“意氣風發”一說?
當日侯府大喜,不員也是邀到場的,分明見過他穿喜服時的模樣,但在今天仍是湊趣。
謝晏不解。
直到與他關系最近的霍林安來了,一見面就笑道。
“瑾兄,多日不見,英氣更甚。”
謝晏問:“為何這麽說?”
霍林安被問得怔了怔:“覺上是這樣的。”
婚後的威靖侯世子,就是比從前要更有風度了。
差別其實并不大,因此讓人細說是說不出的。
謝晏沉默不語。
不久後,禮部那一群風度翩翩的員也來了。
人群中有一位風華正茂的郎君,俊絕倫,著謝晏這邊靜默許久。
在大殿外等候時,後來到場的人都比較矚目。
謝晏注意到了蕭卿之別樣的目。
更加莫名其妙。
他平素與人來往,與這位第一男子更是并無集。
從前就覺到對方對他若有若無的敵意。
這次休沐歸來,察覺到的敵意更重了。
謝晏面無表,繼續與霍林安說話。
他行得端坐得正,不論外界有什麽不對,沒到需要解決的時候,一概無視。
外界暗流湧,可棲遲居的室中,仍是一派睡的靜謐,一直持續到天大亮。
謝晏走後,早晴怕秦知宜冷醒,輕手輕腳往褥子裏塞了暖爐。
因此秦知宜在綿綿不斷的熱意中,一路酣睡。
待睡足了,睜眼看到旁空,迷迷糊糊地問。
“世子已去上朝了嗎?”
早晴坐在腳踏上陪著。
“是呢,世子爺四更末就起了,一點聲音沒發出。還將褥子掖得的!”
秦知宜抱著褥子笑。
“夫君是人,今天也記得給我掖被子了。”
早晴忙點頭。
睡好了,因此腦袋清醒得很快。
秦知宜坐起,將睡的頭發都撥到腦後,志氣昂揚。
“要不然,我這就去給母親請早安如何?反正世子也不在,一個人在這屋子裏也無趣。”
早晴忙點頭:“很好呢。”
自從敬茶那日,侯夫人說不必請早安後,秦知宜早上就沒去過正院。
侯夫人一直沒派人來請過,今天雖然有些晚了,可秦知宜主要去,自然是很好的。
猜你喜歡
-
完結86 章

我不是小啞巴
沈緒在山野撿了個小啞巴帶回宮,從此多了幾個特殊嗜好:喂小啞巴吃飯,哄(陪)小啞巴睡覺,順便還劈了一塊田地給小啞巴種菜玩兒……當旁人都以為小啞巴不會說話好欺負時,她當著眾人的面,捉住沈緒的袖子,仰頭道:“疼。”沈緒彎下腰,嗓音柔和,眉目沉靜:“哪里疼?”“手疼。”他眼中閃過一片陰鷙:“誰干的?”小啞巴抬手一指,從此再沒人敢欺負她。
23.2萬字8 11882 -
完結538 章

庶女醫妃颯翻天
蘇淩瑤作爲22世紀最強雇傭兵組織的頭部毒醫殺手。在被同事陷害身死以後穿成了丞相府被抛棄的庶女。 抛棄九年,才被接回府竟然是爲了讓他替嫡女姐姐嫁人。 新郎性格暴虐?有世界最大的恐怖組織頭目暴虐嗎? 新郎身患殘疾?還有我毒醫治不好的病? 不就是替嫁嗎?只要錢到位,壹切都好說。 結婚當日。 等等,這新郎好像有點眼熟。 這不是欠我505兩的那個小子嗎?還錢。
101.1萬字8.33 120125 -
完結365 章

皇后她每天都想進冷宮
元黛穿成了活不過三集的炮灰女配?按照原劇情她下場凄涼落了個五馬分尸結局。跟女主搶男人是沒有好下場的。于是她開始一路作死想把自己作進冷宮!誰知道這狗皇帝竟然會讀心術?蕭凌剛想把她打入冷宮,卻聽到她道:【快讓我進去!進冷宮我就可以包養小白臉游山玩水嘞!】嘴上夸著他英俊帥氣,心里卻道:【長著一張死人臉,帥個屁,還是小奶狗好】蕭凌:?后來蕭凌忍無可忍不想再忍將她撲倒在龍床上,“小白臉?這輩子都別想了。”
64.4萬字8.18 64850 -
完結395 章
暖春入帳
被抄家之后,她差點淪為死太監的玩具。為謀生路,她不得已做了替身,成了封宴的通房。正主回來后,她默默離開。可封宴記住了那個榻間嬌婉喚他名字的女人,從聲音到香氣都讓他惦念,翻遍了天下把她給翻回了懷里。她不愿做后宅中的一只籠中雀,主動提出封宴可廣納后宅,只要別夜夜去她那里打擾。最后,封宴抱著她,繾綣地吻在她耳后顏顏說得都對。
70.2萬字8.18 19400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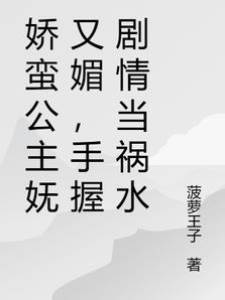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5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