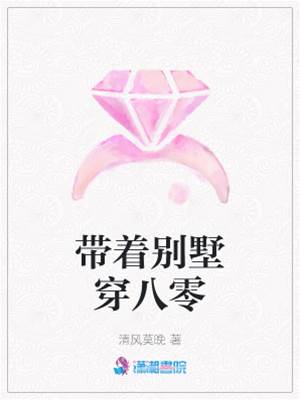《致命牽引》 第十二章 祝你如愿
原來是他先霸占了這里主人的位置,難怪,這頂帳篷怎麼看都太過豪華了。
莊念著后頸,強烈的自責和愧疚涌了上來。
他重新回到房間,垂著頭,模樣認真的找著什麼,最后視線鎖定在床頭柜的一腳,彎下撿起了掉在地上的兩顆紐扣。
昨晚換下的服里還揣著幾塊餅干,是他看顧言一直在喝酒沒有吃東西下意識帶出來的東西。
現在看上去有些好笑,索放棄了酒店的早餐,用這份無用的關懷果腹。
他徒步走過漫長的草坪,腳下很,托的腳步也輕,白大褂隨風掀起一角又落下。
都著輕松,然而昨天初到這里的松弛卻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莊念在一木亭旁邊駐足,像是被飄起的輕紗擋住了去路。
他屈指了,發紅的耳朵讓這位從容溫和的醫生看上去有些窘迫。
...
醫務室安排在游樂設施旁邊,地勢較高,能俯瞰整個智能游樂場。
門外靠右的位置同樣有一間木亭,白紗輕飛,不一樣的是中間原木雕刻的長桌上放著一套茶,一只細口的白瓷花瓶,里面點了幾只郁金香。
莊念四欣賞了一圈,提前準備起工作要用的東西。
來這的人基本上都拖家帶口,很多小孩子。
莊念挑揀了幾瓶碘伏和酒棉放在順手的位置,將紗布剪至適合大小,一切都準備的差不時,醫務室的門被推開了。
來人的腳步聲很快,顯得有些氣急敗壞。
Advertisement
莊念偏頭看了一眼,皺了皺眉,眼底的驚訝一閃即逝,仿佛早有預料似得,轉眼就變了揮不去的厭惡。
“你們昨晚都做了什麼?!”唐周雙手猛地一拍桌面,將碘伏震的搖晃,咕嚕一聲翻倒。
莊念長睫撲簌,垂下眼慢慢扶起了那瓶碘伏,開口道,“慌什麼,你不是都盯著嗎?”
因為不是在醫院工作,不用穿的那麼正式,他在白褂下面搭配了一件藏藍的短袖,款式簡單,只在心口位置有一個口袋,里面了一只鋼筆。
他將鋼筆出,緩緩在記事薄上寫下日期和今天要注意的事項等人到期了簡單開個早會。
期間沒有再抬眼,只淡聲說,“你大老遠追過來,就是為了杵在這嗎?”
“你!”唐周目眥裂的瞪著他,指尖在桌面上按蒼白,咬牙切齒道,“莊念,你別忘了我曾經跟你說過的話,你的喜歡會毀了他!”
莊念長吁一口氣,難得的顯出耐心用盡的煩躁,冷眼看過去,“你就只會說這些?抱歉,我沒有時間安你的不安和自卑,請你”
一句請你離開卡在間。
他想起昨晚橫眉冷目的趕主人離開,現在當然不會再忘了這里也是主人家的地盤。
而他才是那個該離開的‘外人’。
前期準備工作做的差不多,他起準備離開,卻又被唐周纏住了手臂。
“顧言需要我。”唐周息仍急,一字一頓道,“他的父親病了,他想要順利接任顧董事長的位置,想要保住顧伯伯這一輩子的心就需要唐家的支持,我們一定會訂婚,而且會向全世界宣布。”
Advertisement
莊念不耐煩的目微微一,“顧伯伯怎麼了?”
唐周終于在他的眸子里看到如從前一般的恐懼,這才滿意的松了手,“其他的你不用知道,你只要記得,你離顧言遠遠的,才能保證他繼續擁有現在的全部。”
莊念猛地抓住唐周的領向后一聳,將比他矮了半頭的男生推撞在辦公桌上,溫的桃花眼向下一,“我是在問你,顧伯伯怎麼了。”
唐周對七年前莊念發火的模樣還心有余悸,一時忘了呼吸,抿在一起的雙輕微抖,“腦袋里長了東西,在國外治療,大概...活不長了。”
莊念心下一沉,腦子里瞬間涌現出許多顧穆琛溫暖又慈祥的模樣。
孩時的顧言像爸爸,連溫暖的舉和有些天真的話都如出一轍。
他最初開始敬慕那個一手創建顧氏集團的男人,并不是了解到他的實力有多雄厚,能力多強大,只是因為他在顧言的眼中看到了極致崇拜,才開始不由自主的仰慕那個如山一般的男人。
莊念力一般的松了手,不敢去想那個把父親看做是天的顧言要怎麼面對。
憂外患,顧言現在的力該有多大。
“我不管你們昨晚都做了什麼,但莊念,你應該知道顧言這輩子都不會再你了。”唐周松了松領口,偏頭咳嗽兩聲譏笑道,“他做的一切,只是不甘心當初被你像垃圾一樣丟掉而已。”
“所以連難過都不要表現出來,莊念。”唐周笑的越發肆無忌憚,面目甚至有些猙獰,“顧言會覺得你連難過都不配。”
Advertisement
莊念是個溫子,所有的刺都是這些年被著瘋長出來的,一刺破,再去刺痛別人。
他早就在除顧言之外的人給的痛中免疫了。
他也并不是個睚眥必報以眼還眼的人,覺得累,覺得可笑。
唐周是唯一一個例外,他傷他的,他恨不得千倍百倍的傷回來。
憎惡、怨恨本就如破土而出將要參天的樹,現在都隨著這些讓人不快的消息,隨著昨晚令人窒息的心痛與無奈,一并暴的鉆出了心底。
莊念驀地轉打斷他接下來要說的話,角掛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那你呢,我原還以為他是真的上你了。”
他輕笑兩聲,盡顯輕蔑,“你說顧言會為了守住顧家跟你在一起?唐周啊,那我就祝你這次能如愿吧。”
留下驚愕憤怒的唐周,莊念信步走出門去。
山腳下的游樂場里人多了起來,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如沐春風的笑意。
莊念一眼就看到遠的顧言,他站在一群西裝革履的人群里仍是最惹眼的一個,偶爾抬手指向旁邊的山水在說著什麼,言談舉止間盡是風度。
想是早上說的合作方。
他緩步走向醫務室旁邊的小亭子里,目遠眺著逐漸沒了焦距。
“莊醫生?”有人拘謹又小心翼翼的了他一聲。
莊念轉過頭,木亭外的白沙被風扶著掀起又落下,吹得他額前略長的發卷了上去。
亭外那人目微滯,就這樣盯著他紅了一張臉。
莊念立刻想起,這人就是周易給他照片的其中一個,冀北。
他輕聲嘆息,突然有一種前狼后虎把他包抄在中間的煩躁,并開始想念醫院的生活了。
“你好,我冀北。”他了短發,步邁進了亭子里,“呃..明天顧總組織了爬山的活,能順利登頂的人不有禮品還會給獎金,莊醫生要不要參加?”
莊念看著他笑了笑,“不了,我還有工作。”
猜你喜歡
-
完結1531 章
顧少的替嫁甜妻
走廊裏一片昏暗,沈月西跟在林叔身後,走的小心翼翼。她穿著鮮嫩柔和,皮膚白嫩,五官精致,跟這棟陰森的別墅顯得格格不入。“沈小姐是學醫的,應該懂得如何照顧病人……”
295.8萬字8 30451 -
完結379 章

結婚后我懷崽出逃了
傳言紀修然冷酷無情,心狠手辣,得罪他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偏偏趙凝初不怕死的不僅和她結了婚。 新婚第二天,紀修然陰鷙暴戾的丟給她一盒藥。 冷聲的威脅:“不想被我送上手術檯,就把藥吃了!” 五年後 紀修然看到原本已經死去的前妻出現在人羣中。 他像是瘋了一下衝上去緊抓着她不放。 “趙凝初,孩子呢?” 趙凝初神色清冷的看着眼前的男人,嫣然一笑 。 “死了,這不是你希望的嗎?” 紀修然瞬間氣紅了眼:“那就在給我生一個。” 說完直接將人抵在牆角。 這時,兩個小傢伙衝過來:“壞叔叔,放開我媽咪!” 紀修然:……
88.8萬字8 31818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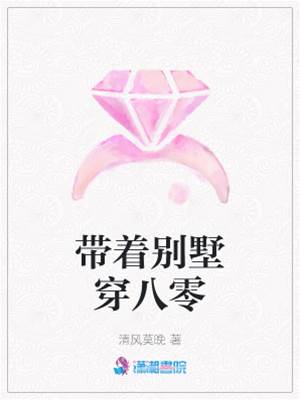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297 章

非分之想
北城的豪門圈子裏都在議論,姜家找回了失散多年的親生女兒,養女姜時念一夜之間變成最尷尬的存在。 連她定下婚約的未婚夫也有恃無恐,豪車遊艇陪伴真千金,還漫不經心地跟友人打賭:“姜時念馬上就要一無所有了,不敢生氣,她只會來做小伏低,求我別分手。” 姜時念當時就在現場,當衆跟他分得轟轟烈烈,轉頭走進紛揚的大雪裏。 她拖着行李箱渾身冰冷,獨自在空曠的街邊蜷住身體時,一輛車穿過雪霧,在她身邊停下,如同等待捕獵的兇獸。 後排車窗降下來,男人西裝革履,矜貴的眉眼如墨,溫文爾雅地朝她彎脣:“沒地方去了?我剛好急需一位背景乾淨的太太,婚後可以相敬如賓,互不干擾,姜小姐願意幫忙嗎?” 大雪漫天,這位站在北城金字塔頂的先生,有如救贖的神祇,溫和典雅,毫無危險性。 姜時念最無助的這一刻被驚天大餅砸中,她站直身體,盯着他直白問:“什麼時候領證?” 他莞爾:“現在。” 姜時念以爲婚姻只是形式,於是拿出戶口本,做了這輩子最瘋狂的決定,鬼使神差上了他的車。 她卻完全沒有看透他溫柔的僞裝底下,到底壓抑了多少年的掠奪和佔有。 也是到後來姜時念才知道,當初她跟別人辦訂婚宴的晚上,這個在婚後對她索求無度的僞君子,究竟怎樣爲她撕心裂肺,痛不欲生過。
48.7萬字8.18 23675 -
完結118 章

無人區玫瑰
夏星眠喜歡她的金主陸秋蕊。她在陸秋蕊身邊默默待了3年,以為對方總有一天能愛上她。可3年來,陸秋蕊的目光從來都不曾在她的身上停留。在夏星眠21歲生日那天,陸秋蕊對她說:“結束吧,我喜歡上別人了。”當晚,夏星眠喝得酩酊大醉。酒精上腦后,她依著本能恍恍惚惚地晃到了陸秋蕊家里。第二天早上,酒意褪去,夏星眠驚覺身邊躺著一個陌生的女人。女人媚眼如絲地玩著夏星眠的頭發,說:她叫
29.7萬字8.18 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