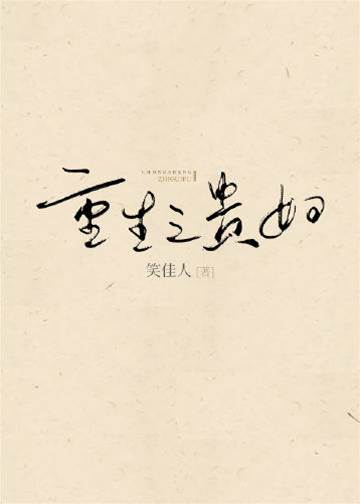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恰如天上月》 第8頁
良久,高陵侯長嘆一聲,唏噓道:“誰能想到,烏巷這代最出眾的兩個郎竟雙雙歸于北府,這在陳郡謝氏和瑯琊王氏的過往中,可算是頭一遭了。”
士庶不婚,高嫁低娶,此為本朝南渡以來形的慣例。王謝兩家鼎盛時,只見公主紛紛嫁烏巷為兒媳,卻不見王謝之嫁給司馬氏為婦,二族之盛可見一斑。
如今倒好,先是王靈素嫁給了馮毅,接著是謝韶音嫁給了李勖,林下雙璧均為武人所得,世事之變莫測如斯。
謝太傅笑笑,向前邁開步伐,“人事有代謝,哪有千古不變的郡。玉公,多思無益,萬事須得向前看吶!”
如今會稽王父子把持建康,謝太傅、高陵侯空有虛位而無實權;何氏父子雄踞荊州、江州,與位于下游的建康朝廷分庭抗禮。司馬弘與何威這兩個老家伙都沒有將對方一擊斃命的把握,彼此都不敢輕舉妄,荊揚之間得以維系脆弱的平衡。
然而,司馬弘耽溺酒,每況愈下,何威亦臥病多時……這二位一旦故去,取而代之的小郎君司馬德明、何穆之都是年輕氣盛的驕矜之徒,荊揚之戰幾乎不可避免。
Advertisement
一旦荊揚開戰,徐州就變得尤為重要——徐州擁有一只悍勇的軍隊:北府兵。
長生道作之前,這支軍隊由韶音的五叔、徐州刺史謝澤和鎮北將軍趙勇共同統領,這也是朝廷希二者彼此挾制之意。
此次長生道作,謝澤戰死,北府兵盡趙勇之手。謝家痛失一梁柱,手中再無兵權,謝太傅沉痛之余,更有蕭瑟秋涼、骨悚然之。
王氏同樣如此,高陵侯之弟、韶音的姑父會稽史王珩殞命于叛軍刀下,王氏子弟再無一領軍之人。
高門綺戶,興也忽焉,亡也忽焉。
謝太傅與高陵侯不得不未雨綢繆,雙雙擇武人為婿。
更深重,晚夏的江濱已有了瑟瑟涼意。兩位人到中年的風流名士踩著木屐,在草叢中深一腳、淺一腳地前行。
“渡之”,高陵侯走兩步跟上謝太傅,“阿紈提出那條件你怎麼就答應了”
都知道謝公疼獨,高陵侯又何嘗不疼阿泠,只是形勢迫人,不得不將們嫁北府。若是韶音真的在三個月后與李勖離異,謝太傅這番辛苦籌劃豈不落空
謝太傅不答,腳步愈發穩健從容,高陵侯跟得辛苦,待到出了沉香林,行至空闊的河谷地帶,謝太傅方才放慢了步伐,仰頭看天上的月亮。
Advertisement
今宵逢朔,一牙彎月高懸中天,清輝麗映,明朗可。
月有晴圓缺,變化無窮,此為明月本。月之人,自然每一種月相,若只滿月無虧,人與月便不得長久。
謝太傅想到此不由揚起微笑,“我兒恰如天上月。”
高陵侯一愣,隨即“嘁”了一聲,不服道:“我兒亦是天上月!你莫要以為阿紈貌,那李勖就能由著胡來,你我都是男子,怎會不知男子喜什麼樣的妻室……”
夜風習習,似有笛聲自江畔而來,如咽如訴,林中約可見一角白袍。
謝太傅瞇起眼向那邊去,只見一人瘦削拔,側立于江畔吹笛,眉宇廓如雕如琢,令人想起他父親王玉公年輕時的風姿,風神秀徹更在乃父之上,一如瓊林玉樹。
“那不是九郎麼”
謝太傅轉頭與高陵侯道。
高陵侯立即示意謝太傅噤聲,隨后重重嘆了口氣,輕聲道:“阿紈出嫁,我兒的心已然傷了。你莫要高聲,讓他聽到了,只怕傷了面。”
……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問君,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繚之。
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Advertisement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
船艙床榻隨波起伏,韶音躺在上面,一顆心似乎也漂浮不定。阿筠和阿雀已經睡了,二人均勻的呼吸聲令人愈發難以眠,耳畔似乎有約的笛聲,吹的像是《有所思》,側耳細聽,又仿佛只是艙外的江聲。
王微之最擅吹笛,韶音大概是被他氣狠了,以至于夜不能寐,耳中盡是幻聽。
這斗艦巨大,乃是北府軍作戰時用以指揮的戰艦。此次用于迎親,雖已是仔細打掃過,此刻仍能聞到一子油汗味道,像是木頭里散發出來的一樣,令人忍不住反胃。
韶音實在睡不著,不想驚阿筠和阿雀,躡足出了船艙,鉆進了來時的馬車中。
母家的馬車寬敞舒適,車里熏了蘇合香,有墊可靠,有被可蓋,躺在車里,整個人都被悉的氣息包圍了。
月過車窗照在氍毹上,照亮了上面堆放的東西,韶音出一手指頭,漫不經心地挨個拉,心里一一數著那些人的名字:何穆之,司馬德明,庾家郎君,郗家郎君……忽然覺得委屈,上岸前那種口、嚨酸無比的覺又涌了上來,忍不住搭搭地哭了起來。
從小到大,所有的郎君都喜歡、恭維,唯獨王微之例外。他總是捉弄,嘲諷,從不肯順著的心意。
就連出嫁這麼大的事,他都不聞不問,也不過來送送,只打發十二郎送了個怪味的香囊,還說他討厭。
這麼討人喜歡,他怎麼能討厭呢!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08 章
重生之農家釀酒女
現代調酒師簡雙喪生火海又活了,成了悽苦農家女簡又又一枚. 一間破屋,家徒四壁,一窮二白,這不怕. 種田養殖一把抓,釀酒廚藝頂呱呱,自力更生賺銀兩 培養哥哥成狀元,威名赫赫震四方. 曾經的嫂嫂一哭二鬧三上吊,撒潑後悔要復和,陷害栽贓毀名聲,讓你仕途盡毀;霸氣新嫂嫂一叉腰——打. 酒莊酒樓遍天下,不知從哪個犄角旮旯裡冒出來的七大姑八大姨齊上陣,奇葩親戚數不清,老虎不發威,當她是軟柿子? 大燕丞相,陷害忠良,無惡不作,冷血無情,殺人如麻,人見人繞之,鬼見鬼繞道;只是這賴在她家白吃白喝無恥腹黑動不動就拿花她銀子威脅她的小氣男人,是怎麼個意思? ************** 某相風騷一撩頭髮,小眉一挑:"又又,該去京城發展發展了." 某女頭也不擡:"再議!" 再接再厲:"該認祖歸宗了." 某女剜他一眼:"跟你有半毛錢關係?" 某相面色一狠,抽出一疊銀票甩的嘩嘩響:"再囉嗦爺把你的家當都燒了." 某女一蹦三丈高:"靠,容璟之你個王八蛋,敢動我銀子我把你家祖墳都挖了." 某相一臉賤笑:"恩恩恩,歡迎來挖,我家祖墳在京城…"
66.4萬字8 73556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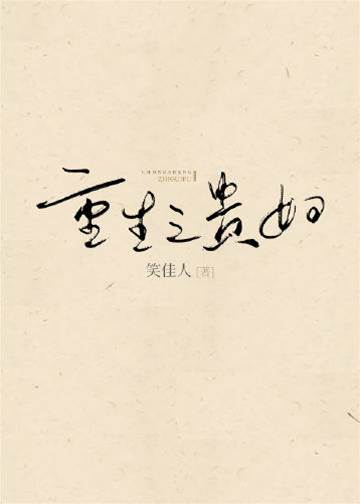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171 章

錯撿瘋犬后
病嬌太子(齊褚)VS聰慧嬌女(許念),堰都新帝齊褚,生得一張美面,卻心狠手辣,陰鷙暴虐,殺兄弒父登上高位。一生無所懼,亦無德所制,瘋得毫無人性。虞王齊玹,他的孿生兄長,皎皎如月,最是溫潤良善之人。只因相貌相似,就被他毀之容貌,折磨致死。為求活命,虞王妃許念被迫委身于他。不過幾年,便香消玉殞。一朝重生,許念仍是國公府嬌女,她不知道齊褚在何處,卻先遇到前世短命夫君虞王齊玹。他流落在外,滿身血污,被人套上鎖鏈,按于泥污之中,奮力掙扎。想到他前世儒雅溫良風貌,若是成君,必能好過泯滅人性,大開殺戒的齊褚。許念把他撿回府中,噓寒問暖,百般照料,他也聽話乖巧,恰到好處地長成了許念希望的樣子。可那雙朗目卻始終透不進光,幽深攝人,教著教著,事情也越發詭異起來,嗜血冰冷的眼神,怎麼那麼像未來暴君齊褚呢?群狼環伺,野狗欺辱時,齊褚遇到了許念,她伸出手,擦干凈他指尖的血污,讓他嘗到了世間的第一份好。他用著齊玹的名頭,精準偽裝成許念最喜歡的樣子。血腥臟晦藏在假皮之下,他愿意一直裝下去。可有一天,真正的齊玹來了,許念嚴詞厲色地趕他走。天光暗了,陰郁的狼張開獠牙。齊褚沉著眸伸出手:“念念,過來!”
26萬字8 7269 -
完結59 章
念遙遙
白切黑和親公主X深情鐵血草原單于,遙遙”指“遙遠的故鄉”。“遙遙”也是女兒的小名,瑉君起這個名字也是寄托自己想要回家的念想。同時也算是一種宿命般的名字吧,女兒小名是遙遙,最后也嫁去了遙遠的西域,算是變相的“和親”月氏的大雪終于停了,我仿佛看見天山腳下湍湍溪流,茂盛的樹木與金燦燦的油菜花。我騎著馬去看我剛種下的小芽,一對鐵騎打攪了我的早晨,我沖到他們面前,指著最有氣勢的一個人破口大罵。他卻不惱,逆著陽光,將我籠罩在他的身影里,低下頭來,笑問道:“漢人?哪兒來的?”
9.2萬字8 11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