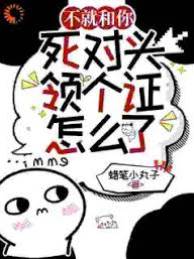《假乖!京圈太子他哥纏上我》 第六章 謝笙
遲非晚輕嘆了聲。
要是沒有謝政樓,等到老師的病好轉,或許真的會一心一意和謝嘉樹在一起。
可現實是不僅有謝政樓,還有遲淺淺。
橫亙在他們之間的,是遲非晚一直回避的人。
“謝先生……”
話音未落,謝嘉樹的手機鈴聲不合時宜地響起。
他本想直接掛掉,看了一眼來電人后,按下了接聽。
“大哥。”
遲非晚幾不可察地僵住。
不知電話那頭的謝政樓說了什麼,謝嘉樹的表變得嚴肅。
“好,我馬上就回去。”
掛了電話,謝嘉樹拉著遲非晚的手腕:“有什麼話,我之后再聽,現在笙兒需要你,到了上課的時間你沒去,現在在家里緒崩潰,誰都沒辦法靠近。”
遲非晚一聽,也顧不得那麼多:“趕走吧。”
謝笙今年十五歲,有嚴重的自閉癥,不能去學校,請的家庭教師也不能接近。
唯獨對鋼琴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可因為格問題,請了無數鋼琴老師,最后都被謝笙嚇跑了。
只有遲非晚,舍不得謝家給的高薪,而且謝家為了請到鋼琴老師也不看學歷,所以一直堅持了下去。
謝笙緒崩潰時有很強的攻擊,最嚴重的一次,遲非晚額角被用凳子砸破,去醫院了好幾針。
謝家給的高額賠償,一下子解決了阮英三個月的化療費。
或許是發現遲非晚怎麼都打不走,謝笙才漸漸對放下戒備,也只有,能安住崩潰的謝笙。
Advertisement
保時捷一路呼嘯,駛進寸土寸金的別墅莊園。
車停在院子里,遲非晚下車就奔向一樓的琴房。
謝笙尖銳的喊和里面玻璃碎裂的聲音不斷傳來,一群傭人焦急地圍在門口想要進去,又被謝笙用東西砸了出來。
一片狼藉中,謝政樓就立在那里。
他還是一深黑,西裝革履,高大拔,隔著人群看向琴房里面,冷峻的臉上沒什麼表。
遲非晚腳步停住,謝政樓偏頭看來。
四目相對的一瞬間,遲非晚仿佛又回到了那晚的電梯里,連呼吸都被奪走。
后謝嘉樹跑了過來,他沒注意到走廊里的暗流洶涌,以為遲非晚害怕,攬著的肩膀。
“大哥,這位就是我跟你說的遲非晚,上次在拍賣場你們遠遠見過一面,也是笙兒的鋼琴老師,這種況,只有能安住笙兒了。”
謝笙凌厲的尖再一次傳來。
遲非晚一凜,不去看謝政樓探究的目,撥開人群走了進去。
兄弟二人并肩站在門口,視線都落在遲非晚上。
只見緒激的謝笙在看見遲非晚的那一刻奇跡般地安靜了下來。
遲非晚慢慢上前:“笙兒,別怕,是我,老師來了。”
拿下謝笙手里的玻璃碎片,一下下輕拍著,聲說:“今天我們繼續學你最喜歡的《致麗》,好不好?”
謝笙遲鈍地點了點頭。
遲非晚就牽著在鋼琴前坐下,同時給門外的傭人使眼,讓他們進來把地上的垃圾全都收拾干凈。
Advertisement
門外的謝嘉樹松了口氣,笑著對謝政樓說:“晚晚來上課的這些日子,笙兒進步了很多,連醫生都說的病好轉了。”
謝政樓沒什麼波,轉往走廊盡頭走。
謝嘉樹跟上去:“哥?”
走廊盡頭的落地窗外是謝家的花園,兄弟二人相對而立,謝政樓量更長些,周縈繞著上位者積威日久的迫。
“母親明天回來。”謝政樓說。
淡淡的一句話,讓謝嘉樹的笑容僵在臉上。
謝政樓沒有顧及他的,平聲道:“讓我轉告你,盡快和那個人分手。”
謝嘉樹仿佛有了應激反應,聲線繃:“我不會和晚晚分手的,誰來勸都沒用。”
謝政樓沒有勸他,只是平靜地陳述事實。
“母親會把手里那部分份轉給你,集團也將正式給你,但前提是你聽的話。”
“我不要份,也不想要集團,大哥你一直都做的那麼好,沒人比你更適合坐那個位置,”謝嘉樹語氣堅定,“我只要晚晚一個。”
謝嘉樹不愿再聽,轉離開。
謝政樓站在原地,從兜里拿出手機放到耳邊。
“您都聽到了。”
電話那邊是一個中年人的聲音,正是謝政樓口中的母親駱惜璟。
“嘉樹就是被那個遲非晚迷了心智,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必須讓離開嘉樹,而且,不能讓嘉樹發現背后有你的手筆,嘉樹這孩子單純,我不想他太傷心失。”
Advertisement
謝政樓結輕滾:“是。”
“還有,”駱惜璟質問,“我讓你提前回國,就是為了替嘉樹去參加遲家的生日宴,你怎麼沒去?”
“集團臨時出了問題,已經解決了。”
駱惜璟沒再追究:“他們遲家能做出苛待親,偏寵外人的事,就說明他們遲家配不上咱們謝家的門第,他們兩個兒更是哪個都配不上我的嘉樹,但是這婚約畢竟是長輩定下的不能取消,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明白就好,在嘉樹分手前,集團總裁的位置還是你的,”駱惜璟說,“你結婚,我也會為你備一份厚禮。”
“謝謝母親。”
謝政樓最后一個字還在嚨里,聽筒里就已經傳來了忙音。
屏幕上彈出助理韓山發來的消息。
【謝總,那晚下藥的人已經抓住了,您要怎麼理?】
【問清是誰指使,剩下的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是。】
發完消息,謝政樓盯著手機看了會兒。
琴房里這時傳出琴聲,節奏滯,曲不調。
謝政樓收起手機往回走,快到琴房門口時,琴聲停止,他聽見遲非晚溫的聲音:“很不錯,有進步,老師再給你示范一遍,笙兒仔細聽哦。”
這次的音樂明顯更加婉轉流暢。
謝政樓自小就聽駱惜璟彈琴,知道母親彈得很好,是位國寶級的音樂家。
可現在聽遲非晚的,竟然毫不輸鼎盛時期的駱惜璟。
謝政樓盯著遲非晚拔纖薄的背影,窗外落在上,為整個人都鍍上一層茸茸的金邊。
的隨著節奏微微搖晃,腦后的馬尾末端輕掃過后頸的吻痕。
那是他留下的。
一節課差不多結束,謝笙要自己練習,遲非晚站起來了個懶腰,和謝笙道再見。
一轉,發現謝政樓還在門外站著。
遲非晚視線環顧,沒看見謝嘉樹的影。
“他有事,先走了。”謝政樓說。
又是這種無所遁形的覺。
遲非晚都懷疑是不是自己臉上寫的有字,不然謝政樓怎麼總能看出在想什麼。
“哦,那我也走。”
遲非晚和他錯而過的剎那,手腕被一巨力攥住。
謝政樓低頭看著:“我送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04 章

難辭
大家都知道邵總身邊的金牌助理姓田, 卻沒幾個曉得邵總夫人也姓田。 邵夫人好不容易離了婚, 臨了發現這破工作卻沒法辭。 邵總發了話——離婚可以,辭職沒門。
10.4萬字8 14625 -
完結487 章

蓄意熱吻
(雙潔,男二上位,國民初戀vs斯文敗類) 程微月初見趙寒沉是在父親的退休宴上。 父親酒意正酣,拍著男人的肩膀,喊自己小名:“寧寧,這是爸爸最得意的學生。” 趙寒沉聞言輕笑,狹長的眉眼不羈散漫,十八歲的少女心動低頭。 後來鬧市,天之驕子的男人於昏暗角落掐著美豔的女人,往後者口中渡了一口煙。他余光看見她,咬字輕慢帶笑:“寧寧?” 心動避無可避。 可浪子沒有回頭,分手鬧得併不好看。 分手那天,京大校花程微月在眾目睽睽下扇了趙公子兩個耳光,後者偏過臉半晌沒動。 卻無人知低調的商務車裡,眾人口中最端方守禮的周家家主,律政界的傳奇周京惟捏著少女小巧的下巴發狠親吻。 許久,他指腹擦過她眼角的淚水,斯文矜貴的面容,語氣溫和:“玩夠了嗎?” … 程微月見過周京惟最溫柔的樣子。 正月初一的大雪天,涇城靈安寺,鵝雪輕絮的天地間,人頭攢動,香火繚繞,她去求和趙寒沉的一紙姻緣。 直到周京惟逆著人流朝自己走來,將姻緣符塞在自己手中,“所願不一定有所償。” 他頓了頓,又說:“寧寧,玩夠了就回來。” 佛說回頭是岸,那一天程微月頻頻回頭,都能看見周京惟站在自己身後,於萬千人潮裡,目光堅定的看向自己。 佛真的從不誑語。
87.9萬字8 22718 -
完結613 章

大叔,你的嬌氣包哭了要貼貼
(雙潔 甜寵 治愈)京都第一豪門司家少爺司伯珩,三十歲都不曾有過一段戀情,外界揣測他不是身體有問題,就是取向有問題,直到司家忽然多了一位年齡很小的少奶奶。 據說這位少奶奶還在上大學,據說少奶奶是故意在酒吧賣慘勾引到了司少,一眾擁有豪門夢的女人紛紛嫉妒的捶胸頓足,這樣也行? 因此,這位小少奶奶也收獲了一批黑粉,她們不遺餘力的爆料著她在司家的悲慘生活,被司少的小三小四小五等暴揍,被家族旁支當眾羞辱,跟家裏傭人們同吃同住,被婆婆要求馬上離婚。 顏茸茸表示,自己真的冤枉啊,她明明沒勾引,也沒挨揍,而且肚子裏還踹著司家的乖孫,婆婆公公一天三趟的來勸她搬回老宅要親自照顧。 她努力想了想,在黑粉超話留下一句話。 “其實,我真的不悲慘呀!”
92.1萬字8.18 619000 -
完結572 章

顧少有令:追回前妻生寶寶
綠茶高調上位,安予甜才新婚就慘被離婚。摸著越來越大的肚子,她發誓:“去特麽的愛情,我要搞錢!”搖身一變成了風光無限的何家大小姐,開啟逆襲人生,沒想到卻被某人圍追堵截。“老婆,撩完就跑,很刺激?”“老婆?誰是你老婆?”“少裝傻,你肚子裏懷著的可是我的寶寶!”安予甜傻眼:“你又不愛我,何必呢?”男人直接一吻封唇。
105.8萬字8.18 22359 -
連載51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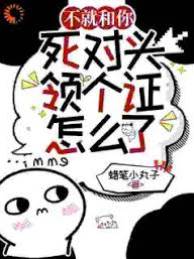
不就和你死對頭領個證,怎麼了?
第三次領證,沈嶠南又一次因為白月光失了約;民政局外,江晚撥通了一個電話:“我同意和你結婚!” 既然抓不住沈嶠南,江晚也不想委屈自己繼續等下去; 她答應了沈嶠南死對頭結婚的要求; 江晚用了一個禮拜,徹底斬斷了沈嶠南的所有; 第一天,她將所有合照燒掉; 第二天,她把名下共有的房子賣掉; 第三天,她為沈嶠南白月光騰出了位置; 第四天,她撤出了沈嶠南共有的工作室; 第五天,她剪掉了沈嶠南為自己定制的婚紗; 第六天,她不再隱忍,怒打了沈嶠南和白月光; 第七天,她終于和顧君堯領了證,從此消失在沈嶠南的眼中; 看著被死對頭擁在懷里溫柔呵護的江晚,口口聲聲嚷著江晚下賤的男人卻紅了眼眶,瘋了似的跪求原諒; 沈嶠南知道錯了,終于意識到自己愛的人是江晚; 可一切已經來不及! 江晚已經不需要他!
92.8萬字8 96 -
完結106 章

閃婚后,霸總高冷人設崩塌
愛情中有很多陰差陽錯。年紀輕輕就事業有成的秦墨對婚姻沒有什麼強烈的向往。他帶著自己的目的和許昔諾閃婚。他自信自己能夠掌控一切,卻在相處中一點點淪陷,慢慢地失去了主動權。原本高冷的秦墨也變成了黏人的舔狗,慢慢攻克許昔諾冰冷的心。受變故打擊的許昔諾在相處中打開心扉,被秦墨的溫暖和熱情治愈。
27.6萬字8 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