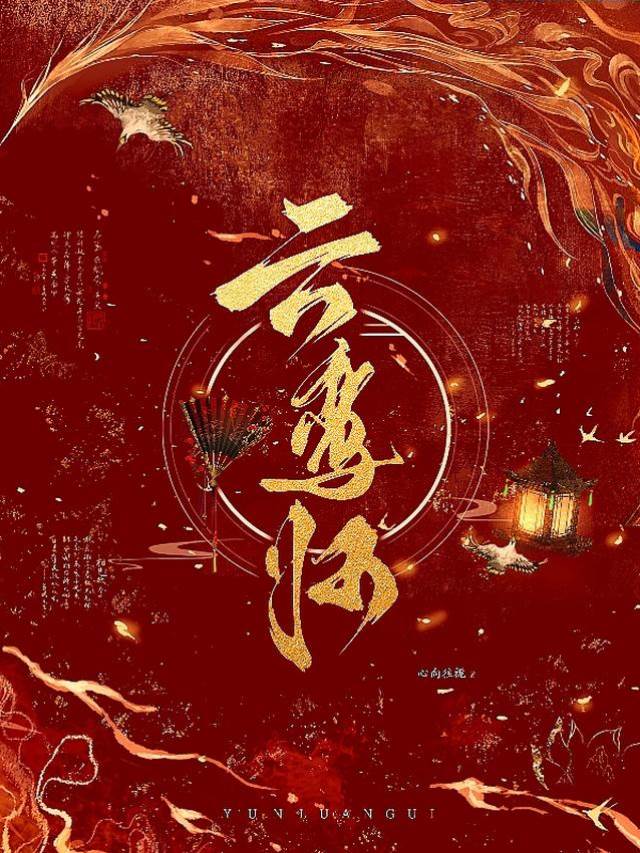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枕邊嬌色》 第4頁
令頤像只貓兒般窩進他懷里,小腦袋著他前的料,嗅著他上的香氣。
回屋后,徹擰干溫熱的帕子,作輕地為令頤凈面拭手。
他指了指床:“回去躺好。”
令頤乖巧“嗯”了一聲,鉆回被窩躺好。
以為徹要走,不料,他搬了把春山凳過來,掀袍而坐。
就那麼自然而然坐在的床頭。
他量高,這般坐著,幾乎將半張床榻都籠在影子里。
姿態優雅從容,仿佛只是隨意尋了個地方看書。
令頤眨了眨水靈靈的杏眼。
即便是父親和伯聿阿兄也很踏的閨房,更不用說離的床這麼近。
令頤幾乎能看到他眼瞼下的淡青,還有細的睫影。
出手拽了拽他的袖:“哥哥?”
片刻后,徹清冷的聲音響起。
“妹妹平常讀什麼書?”
令頤一怔,隨即眉眼彎彎:“哥哥要給我念書嗎?”
徹沒答,從案幾上拿來幾冊話本。
令頤看過去,神立刻雀躍起來:“是《山海記》,哥哥怎麼知道我聽這個!”
“猜測罷了。”
對徹來說,一個小姑娘的心思并不難猜。
他翻開書頁,低沉的嗓音緩緩流淌。
徹念書時語調平穩,音介于溫潤和低沉間,像山澗清泉,泠泠淙淙。
那些神神鬼鬼的故事經他一念,聽上去都沒那麼可怕了。
令頤起初還睜著圓溜溜的眼睛盯著他瞧,漸漸地,眼皮開始發沉。
過了沒多久,小腦袋一點一點的,最終歪在枕上,呼吸綿長。
徹合上書冊,垂眸看。
小姑娘睡得香甜,長睫如蝶翼般垂著,角還帶著淺淺的笑意。
Advertisement
他手替掖好四個被角,作極輕。
窗外月如水,年輕郎君的影默默守在榻前,許久未。
翌日清晨,令頤是被徹溫醒的。
小姑娘了懶腰,糯聲糯氣道:“哥哥,昨晚我睡的好香啊……”
是這麼長時間來最香的一次。
徹眼里含著。
他早已起多時,上的墨長衫穿戴得一不茍。
可偏偏手里拿著小姑娘的花服,整個人看上去顯出幾分生來。
令頤半瞇著眼,慢悠悠從服下面鉆了進去,一點點拱出腦袋。
穿戴整齊后,徹將抱到了梳妝臺前,執起木梳,指尖拂過的發,細心梳好一個發髻。
“哥哥梳得這樣好,是不是常給家里的姐妹梳頭啊啊?”
徹淡淡道:“不曾。”
令頤心里疑,他卻似乎不愿談論這個話題,道:“過來用早膳。”
桌上擺著兩碗熬得濃稠的米粥,還有幾碟小菜。
徹夾起最的菜心放到碗里:“別挑食,馮大娘說你要多吃些蔬菜。”
“好嘛……”
令頤不愿吐了吐舌頭,把臉埋進碗里。
徹垂眸道:“吃三口菜,獎勵一顆棗。”
令頤瞬間眼睛亮起。
午后換藥時,正好。
椅子上的小姑娘咬著,可憐看著自己的腳。
腳踝的傷口已經結了深褐的痂。
徹的指尖沾著藥膏,在到皮的瞬間,小姑娘疼得直氣。
淚眼汪汪,委屈道:“哥哥……”
“忍一忍。”
他不聲從袖中出油紙包,展開是幾顆漬梅子。
令頤兩眼放手去抓,卻被他輕輕拍開:“先上完藥。”
……
Advertisement
這麼相了幾日,令頤覺得這個哥哥非常會照顧人。
白日里,兩人溫馨相,暮四合,他就在房中點一盞青瓷燈,就著昏黃燈火讀書。
讀到有趣,會輕聲念與聽。
“妹妹的先生平常都教什麼書?”
某夜,他忽然問道,手指輕輕挲著書頁邊緣。
燈影在他眉骨投下深淺不一的影,將那雙平靜的眼睛映得格外溫。
令頤晃著腦袋想了想。
“《千字文》《學瓊林》,有時來了興致,先生還會教《史記》,朱子的《蒙須知》……”
徹道:“《史記》太深,《蒙須知》又太板,都不適合你的心。”
于是,他便尋來幾本《學瓊林》,教與聽。
“學到哪一篇了?”
“《科第》。”令頤如實回答。
徹指尖翻至那一頁:“鹿鳴宴,款文榜之賢;鷹揚宴,待武科之士……”
他輕笑:“倒是應景。”
“妹妹可知何為折桂?”
年輕郎君問著,聲音里帶著幾分考校的意味。
令頤搖頭,徹便順勢講起蟾宮折桂的典故。
“傳說,月宮有一棵桂樹……”
年輕郎君的聲音漸漸低下來。
不是像夫子那樣掉書袋,而是將晦的文字換通俗易懂的話。
令頤拍手笑道,綻開頰邊兩個梨渦:“哥哥比我夫子教的好多了,若哥哥教書,一定有人搶著聽哥哥講學!”
“不像令頤的教書先生,每次念文章砸得令頤一個頭兩個大。”
向來不吝于對別人的贊,喜歡讓邊人都開心。
徹抿微笑:“你心思細膩,凡事一點即通,是個不錯的學生。”
他就這般給念著 ,直到眼皮打架,才輕手輕腳為掖好被角。
Advertisement
有時令頤清晨醒來,見他斜靠在窗邊長椅上,闔著雙目。
羽睫在熹微晨中投下淡淡影,手中書卷將落未落。
令頤便數他的睫,聞到他袖口染著昨夜的燈油香。
似乎在這里待了一整晚。
令頤以為,這樣平靜的日子會一直持續下去。
誰知這日,正在院中逗弄白兔,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傳來。
徹開了門,一個書生打扮的人慌慌張張進門。
“兄,你得趕走,離開京城!”
徹頓時警覺:“出了什麼事?”
張書生道:“方才錦衛和東廠的人闖進貢院,把今科和姜大人好的舉子都鎖拿了,說他們私結朋黨!”
“有個不肯就范的,已經當場被捅死了……”
徹趕忙回頭看了看院子里的小丫頭,見歪著腦袋似是沒聽到,方松了半口氣。
“好,我馬上帶令頤離開這里,多謝張兄。”
他轉向令頤走去,月白袖掠過花架,掃落幾瓣香雪。
“令頤,我們得離開京城一段時間。”
庭花枝沙沙作響,斑駁花影映在兩人上。
令頤手中草葉倏然落地,仰起臉不解道:“離開?那我們什麼時候回來呢?”
“等這里歡迎我們的時候,再回來。”
年輕郎君溫說著,像是怕驚擾了薔薇的春夢。
為保險起見,這春闈,他數年寒窗等來的春闈,大概是參加不了了。
倒是憾。
徹正想著如何躲開城門搜查,耳畔忽然傳來泣聲。
他問:“怎麼哭了?”
“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令頤嗒嗒著抓住他的袖:“只是看哥哥出這種表,令頤心里心里好疼,像是有人把心尖那塊給剜去了……”
“阿爹在家里經常夸贊哥哥,說哥哥十六歲中舉,是、是瓷,”
“京城沒有不歡迎哥哥,他可能只是最近心不好,所以讓哥哥誤會了……”
搭上他的手,眼眸蓄滿了淚。
莽撞、笨拙、熾烈。
泛紅的眼眸比春日更耀眼,帶著灼人的溫度。
徹怔了半響。
他從未見過哪個閨閣約束出來的有這樣的眸子,干凈,剔,不染一塵埃。
淚珠滾落時,他看見自己略帶錯愕的倒影。
徹向來疲于與閨閣子周旋。
家還未出事前,因為徹神的譽,上門說親的踏破了門檻。
其中不乏當地世家大族家的兒,那些小姑娘皆是聰明伶俐,冰雪可人。
個個玲瓏剔,又個個像心雕琢的玉人。則矣,卻是連笑靨的弧度都量好了分寸。
背后連系著各自的家族,一言一行都帶著目的。
而眼前這個傻丫頭,連哭都不會用帕子掩面,眼淚鼻涕全蹭在他袖子上。
可在徹眼里,卻比那些姑娘看著順眼。
“傻丫頭,不是瓷,是國。”
年輕郎君一聲輕嘆,飄飄然散在了風里。
他溫低眉,指腹拭去腮邊淚珠。
“彬江是個很的地方,這個時候正是溫暖怡人,六煙橋邊春江水暖,很適合小姑娘游湖踏青。”
“不知妹妹可愿同行?”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301 章
鳳謀天下:毒妃當道
前世她嘔心泣血為他謀奪皇位,最終卻落個慘死。唯一疼愛自己的祖母被火燒死,兒子讓人生生的放幹了血。 雲君立誓做鬼也不能放了雲家人,不能放了雲馨母女。重活一世,她要做的是毀了整個雲家,讓對不起她的人都生不如死。 將欠了她的債都討回來,哪怕是踩著森森白骨,也都要討回來!李瑾瑜瞧著麵若寒霜的雲君,嘴角微揚:「嫁給我,你就是他們的皇嬸,逢年過節他們可是要跪地磕頭的。」
69萬字8 30751 -
完結1308 章

厲王的替嫁王妃(沈朝陽蕭君澤)
因身份低微,她被迫替嫁廢太子。那人心中只有白月光,厭惡她欺辱她,卻不肯放過她。她委曲求全,與對方達成協議,助他權謀稱帝,助他穩固朝政外邦,以此換取自由身。可誰知,他一朝登基稱帝,卻再也不肯放過她。“你說過,得到這天下就會放過我。”“朝兒……你和天下朕都要。”可如若這江山和美人只能擇其一,他又會如何抉擇?愛江山還是要美人?
238.3萬字8 158648 -
完結115 章

繼室難為
安家老姑娘安寧成了張家二婚老男人張清和的繼室, 上有婆婆,下有姑娘,左有二房,右有姨娘,中間還有麵癱大老爺,繼室也不好做啊。 隨身空間,不喜誤入。 溫馨打底,小虐略有。
32.5萬字8 27009 -
完結48 章

史上最強腹黑夫妻
牧白慈徐徐地撐起沉甸甸的眼皮,面前目今的所有卻讓她沒忍住驚呼出聲。 這里不是她昏倒前所屬的公園,乃至不是她家或病院。 房間小的除卻她身下這個只容一個人的小土炕,就僅有個臉盆和黑不溜秋的小木桌,木桌上還燃著一小半截的黃蠟。 牧白慈用力地閉上眼睛,又徐徐地張開,可面前目今的風物沒有一點變遷。她再也顧不得軀體上的痛苦悲傷,伸出雙手用力地揉了揉揉眼睛,還是一樣,土房土炕小木桌••••••
14.5萬字8 9753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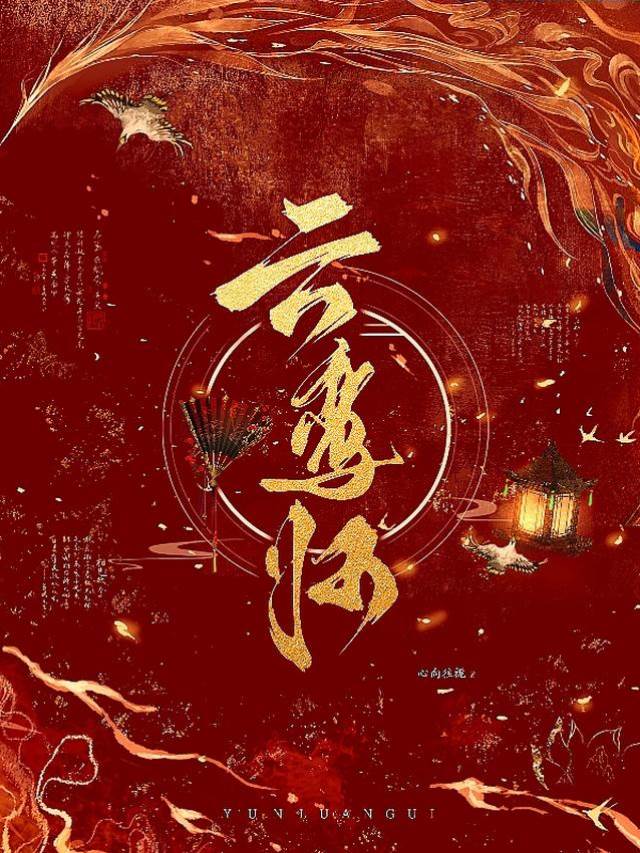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