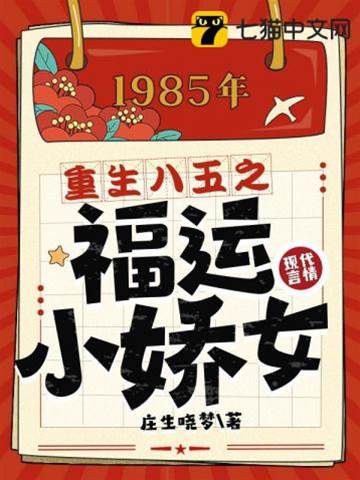《在冷漠的他懷裏撒個嬌》 第34章 喝醉了
“這件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
陸微微臉慘白,不住哆哆嗦嗦地栗著,張極了。
“叮!”電梯門打開,寂白無言地走了進去。
陸微微也趕跟進來,拉住了寂白的袖子,懇求道:“求你了,寂白,求你幫幫我,千萬不要告訴別人,不然我的名聲就毀了!”
寂白走出一樓,來到人的茶廳,方才開口對道:“保可以,但有一個條件。”
陸微微眼睛裏閃過一希冀:“什麽條件,你,我都答應!”
寂白麵無表道:“跟蔣仲寧分手。”
陸微微攥著袖子的手緩緩鬆開了。
睜大了眼睛看著寂白,難以置信道:“你、你讓我和仲寧分手,為什麽?!”
“既然你對他的喜歡比不過對於質的追求,他現在又給不了你想要的生活,為什麽不分手?”
“我、我已經知道錯了,我真的知道錯了,我不想分手。”
“不分手,留著他當備胎,騎驢找馬嗎?”
“寂白,你話也太難聽了。”
“我的話難聽,但你的行為更難看。”
寂白著那漂亮的臉蛋,冷漠地道:“我隻給你這一個選擇,要麽分手,要麽”
從包裏出手機,手機裏已經錄下了剛剛段興宇和幾個朋友的葷段子玩笑話。
“要麽我就把這個公之於眾,別怪我不給你臉。”
陸微微沒想到居然還錄音了,這是早就算計好了啊!
全栗著,聲音都不住發抖:“寂白,我本來以為你是個溫單純的姑娘,沒想到心機這麽深,你為什麽一定要破壞我和蔣仲寧的關係,你又不喜歡他!”
“但我不希你傷害他,背叛這種事,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無數次”
“可這和你有什麽關係!你為什麽要這樣做?”
Advertisement
寂白側過臉,著落地窗外那橫亙臉麵的雪山,傾灑,雪峰泛著粼粼的芒。
為什麽要這樣做。
寂白想了想,或許是因為……在死後,蔣仲寧是為數不多來看過的人,還在寂寥的墓前,放了一束喜歡的純白梔子花。
那些無心的溫與善良,都是曾照亮枯槁靈魂的。
陸微微不可能知道這一茬,現在著寂白,就像著一個心機深沉的可怕怪——
“寂白,我勸你善良!不要把人往絕路上。”
寂白目如刀鋒般掃在的臉上,看得心頭發怵,本能地往後麵退了退。
卻聽寂白一字一頓道:“你沒有經曆過我所經曆的事,憑什麽勸我善良。”
**
整個下午,段興宇都心不在焉,時不時地去落地窗邊掃視一圈,搜尋孩的影。
可是陸微微一直沒有出現。
他也知道,幾個兄弟麵上沒什麽,但心裏無一不是在嘲笑他。
段興宇沉不住氣,給陸微微發信息,問為什麽沒有過來泡溫泉,得到的結果卻是家裏有事,提前離開了西鷺嶺雪山。
段興宇正要假惺惺地關心幾句,卻不想,關切的話語發出去,竟然收到一個被拉黑的歎號。
居然把他刪好友了。
段興宇麵子是徹底繃不住,放下手機,喃喃地罵了聲:“媽的,耍老子啊。”
寂白看著段興宇一整晚沉的臉,還痛快。
目前事件的進展還是很滿意的。
陸微微沒有機會綠了蔣仲寧,而是跟他和平分手,蔣仲寧即便是難過一陣子,但不會遷怒旁人,更不會把段興宇這王八蛋揍了。
這樣他就不會退學,不會被起訴,更不會去坐牢
寂白覺得,這件事是重生回來,幹得最幹淨利落、漂漂亮亮的一件事了。
Advertisement
晚上,有些不放心蔣仲寧,給謝隨發了一條信息,問他現在在哪裏。
謝隨的回複也相當及時:“酒吧街。”
“又喝酒?”
“仲寧分手了,我陪他幾杯,不喝醉。”
酒吧裏,謝隨看著手機屏幕,角不自覺地彎了起來,那一句“又喝酒”,分明就是在關心他。
蔣仲寧紅著眼睛了謝隨,謝隨的笑容立刻沉下去,故作悲傷地喝了一杯,然後拍拍他的肩膀:“人而已,不重要。”
坐在另一側的叢喻舟很想,不重要,你別看到白的信息就笑得跟條狗似的啊。
不過他估著出這話會挨揍,還是咽了下去。
謝隨順手給寂白發了一個定位,卻沒想到二十分鍾後,竟然真的來了。
風景區的酒吧比較規範,都是很有資調的清吧,歌手在臺上安安靜靜地唱著民謠調子,客人也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聊著。
謝隨不經意間側過頭,看到孩從門邊走進來。
穿著白的羽絨服外套,進來的時候帶進一風雪,呼出白白的霧氣,發梢間綴著幾片雪花瓣。
寂白在蔣仲寧的邊的空椅子落座,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也沒有想好要什麽,難過的人其實最不需要的就是安,因為別人很難會當事人心的,什麽都是蒼白無力的。
蔣仲寧喝了不酒,眼睛也有些紅,他看到寂白過來,越發難了,很多緒對著一幫男孩子無法發泄,但是對著孩,蔣仲寧故作堅強的那一麵崩壞了,拉著寂白訴心的苦悶——
“我知道想住五星級酒店,我也了,可以住,我自己掙了錢,可以讓住,可是又不願意,不想隻是僅僅為了驗去住好的酒店”
寂白明白陸微微心裏的掙紮,想快速提升自己的消費檔次,而此時此刻的蔣仲寧無法實現的願。
Advertisement
“我什麽都可以給,我掙的錢全給用,還是嫌我。”
“如果你能振作起來,一定會明白自己錯過了什麽。”
蔣仲寧又給自己倒滿酒,同時又拎來杯子,給寂白也倒了半杯:“白,就衝你這句話,我敬你。”
謝隨出手,慢條斯理地兜開酒杯:“未年不喝酒,我代。”
叢喻舟笑了笑:“你是人家爸爸啊還是人家男朋友,管這麽多?”
“是啊,你喝你的,白喝白的,除非白認你當爸爸。”
“人家有爸爸,幹嘛要認隨哥,不過白,你沒男朋友吧,我們隨哥人帥好,考慮考慮?”
寂白過來,幾個男孩開起無傷大雅的玩笑,沉悶的氣氛一掃而空,蔣仲寧心也好了很多。
謝隨指尖拎著寂白的酒杯,眼梢挑起微笑:“爸爸還是當男朋友,你選一個。”
寂白瞪了他一眼,撇道:“我幹嘛要做這種奇怪的選擇。”
謝隨眼角醞著些許醉意,輕挑地:“不選,我不能幫你喝酒了。”
寂白拎過謝隨手裏的杯子:“誰要你幫我喝酒。”
一幫臭屁孩,還當未年人,兩世的年齡加起來都可以給他們當爸爸了好不。
謝隨本來也是玩笑話,沒想到寂白真的仰頭將杯裏的酒一飲而盡。
“喂!”
他連忙奪過杯子,不過已經晚了,丫頭杯子裏的啤酒一滴沒剩下。
謝隨拍了拍的後腦勺,怒道:“誰他媽同意你喝酒了。”
寂白後腦勺,不爽地瞥他:“我自己同意了。”
謝隨把啤酒杯重重地倒扣在桌上,手將寂白拉到自己邊,嗓音低沉地問:“會煙,還喝酒誰教你這些?”
“問這個幹嘛。”
“我弄死他。”
“”
又來了,寂白真的好想,那請你弄死你自己吧。
“不準再喝酒了,年以前,不準,年了我不在場,也不準。”
謝隨板著臉,試圖嚇唬:“再讓我看到,打斷你的。”
他本來就生得兇相,加之脾氣暴躁,眉還斷了一截,看著更加滲人。
寂白卻已經不怕他了,他就跟條狗似的,嚷嚷瞎喚,也不會真咬。
酒吧裏,朋友們陪著蔣仲寧呆了一晚上,終於將他這顆失的男玻璃心給安好了,蔣仲寧重新振作,他會聽寂白的話,好好努力,讓陸微微知道,到底錯過了什麽。
寂白其實喜歡謝隨的這幾個朋友們,和陳哲周圍那幾個紈絝子不同,這些男孩雖然看著一個個落拓不羈,野難馴,不過他們努力又自信,正直且善良。
謝隨並不知道,寂白居然這麽不能喝。
這事連寂白自己都不知道。
以為一杯啤酒沒有什麽大礙,慢慢地酒催化,覺意識有些恍惚了,想去一趟洗手間,結果剛跳下高腳凳,整個人直接栽了。
要不是謝隨眼疾手快攬住,估著是要重重地摔個屁墩兒。
寂白重心不穩,本能地攬住了謝隨的脖頸,試圖讓自己站穩。
“咦?”
自己好像還不解,發出一聲沉沉的驚歎:“怎麽轉起來了?”
暈暈乎乎地趴在謝隨的懷裏,臉也埋進了他的膛裏,揚聲喚道:“謝隨?”
他應了聲:“昂。”
“你在哪兒呢?”
“……”
我踏馬不就被你抱著嗎!
謝隨蹙眉,這丫頭居然喝醉了?
寂白誠然是真的喝醉了,而且還醉得不輕,臉頰緋紅,都快暈得找不到北了。
撲鼻而來的是上甜的馨香,謝隨鼻翼,也跟著躁了起來。
叢喻舟目瞪口呆地著一杯倒的寂白,抓起被他倒扣的酒杯檢查,詫異地:“隨哥,你下藥了?”
“……滾。”
他連酒都舍不得讓喝,能給下藥?
寂白聽著“下藥”兩個字,慌得一批,提狠狠地踩了他一腳。
謝隨吃痛,角搐起來:“!”
“謝隨你在哪兒呢!救…救我啊!”寂白跌跌撞撞地想往外跑:“他們給我下藥了!”
謝隨拎著的領,讓在原地沒完沒了地撲騰。
“別鬧,我在這兒。”他將孩兜回來,抱在懷裏聲安:“沒人給你下藥,睡一覺就好了。”
寂白看清了麵前的年就是謝隨,依賴地出手抱住了他的脖子,慌張失措地:“謝隨,你千萬千萬別把我送回去,我會死的…”
謝隨蹙眉:“胡八道什麽啊。”
孩拱進了他的頸項窩裏,找了個舒適的位置,安安穩穩地閉上眼睛,還用臉頰蹭了一下。
謝隨頭皮都麻了。
他求助一般地著幾個兄弟:“這…怎麽搞?”
幾個男孩麵麵相覷,流出羨慕嫉妒恨的表。
這題對單狗兼男來,殘忍地超綱了。
謝隨目垂了下來,著懷中的孩。
皮白裏紅,瑩潤如櫻,細的睫輕著……
他漆黑的眸子裏湧著暗流波瀾。
謝隨絕對不是什麽正人君子,也從來不當紳士。
他毫不猶豫將打包扛在了肩上,離開了酒吧,朝著自己的酒店走去。
猜你喜歡
-
連載1152 章

初戀是你,餘生是你
五年前,江小柔被妹妹算計懷上一對雙胞胎,五年後,江小柔強勢歸來,成為人人口中的財神爺。“江總,許總派人送來兩對十克拉耳環,想跟您合作。”助理說。庸俗,扔掉。“江總,張總買了輛飛機送過來,問您下個項目準備投哪?”助理說。“陳總剛纔也打電話問……”江小柔瞪著助理:“以後誰再送車送房送鑽戒通通讓他們滾,我像是差錢的人嗎?”“那如果送孩子呢?”助理指著某總裁,牽著倆萌寶。
174萬字8.18 26067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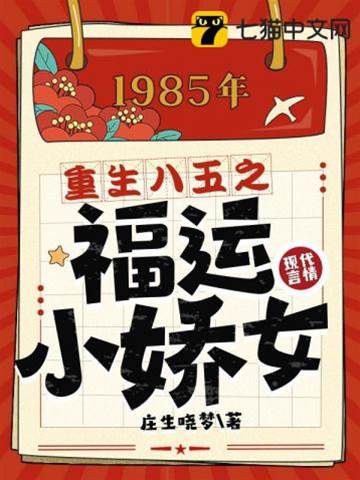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1891 -
完結244 章

一眼著迷
五歲那年,許織夏被遺棄在荒廢的街巷。 少年校服外套甩肩,手揣着兜路過,她怯怯扯住他,鼻音稚嫩:“哥哥,我能不能跟你回家……” 少年嗤笑:“哪兒來的小騙子?” 那天起,紀淮周多了個粉雕玉琢的妹妹。 小女孩兒溫順懂事,小尾巴似的走哪跟哪,叫起哥哥甜得像含着口蜜漿。 衆人眼看着紀家那不着調的兒子開始每天接送小姑娘上學放學,給她拎書包,排隊買糖畫,犯錯捨不得兇,還要哄她不哭。 小弟們:老大迷途知返成妹控? 十三年過去,紀淮周已是蜚聲業界的紀先生,而當初撿到的小女孩也長大,成了舞蹈學院膚白貌美的校花。 人都是貪心的,總不滿於現狀。 就像許織夏懷揣着暗戀的禁忌和背德,不再甘心只是他的妹妹。 她的告白模棱兩可,一段冗長安靜後,紀淮周當聽不懂,若無其事笑:“我們織夏長大了,都不愛叫哥哥了。” 許織夏心灰意冷,遠去國外唸書四年。 再重逢,紀淮周目睹她身邊的追求者一個接着一個,他煩躁地扯鬆領帶,心底莫名鬱着一口氣。 不做人後的某天。 陽臺水池,紀淮周叼着煙,親手在洗一條沾了不明污穢的白色舞裙。 許織夏雙腿懸空坐在洗衣臺上,咬着牛奶吸管,面頰潮紅,身上垮着男人的襯衫。 “吃我的穿我的,還要跟別人談戀愛,白疼你這麼多年。”某人突然一句秋後算賬。 許織夏心虛低頭,輕踢一下他:“快洗,明天要穿的……”
36.7萬字8 11823 -
完結534 章

一夜燃情:韓少他如狼似虎
訂婚當夜,喬語被未婚夫陷害。酩酊大醉走錯房間。竟一不小心將傳聞中不近女色的韓少吃幹抹淨。原本喬語隻想拍拍屁股走人。誰知,那個男人打著高冷的名號,私下各種粘人。他義正嚴詞道:“我原本清白之身,你睡了我,要負責任。”喬語:蒼天啊。往後的日子裏,某人在外一臉豪氣衝天,“在家都是我老婆聽我的,我說一她不敢說二。”一回到家,某人跪在搓衣板上,對著喬語又一頓彩虹屁式的狂誇:“能娶到我老婆,實在是三生有幸,實在是祖墳裏冒青煙了……”
97.1萬字8 121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