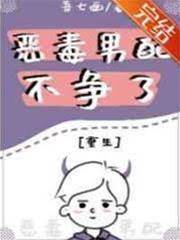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帝王的寵妃是個O》 46
那一邊彎下腰手抓,一邊瘋跑向前的樣子,是看著背影,都被他連滾帶爬的狼狽力勁震撼到,太拼了!
聞鳴玉愣在那,好一會都說不出話來。
終于,霍鴻羽抓到了,從灌木叢里爬了起來。不過,之前那貴族小公子的模樣完全沒了,服蹭到不泥土,臉臟了好幾,頭發糟糟的,頭頂甚至著幾長長的草,最后,他手里抱著一只……山。
簡直搖一變,了地主家的傻兒子。
霍鴻羽是追著猞猁去的,看到一個影子想都不想手就去抓,抓到了心里樂壞了,但等他站起一看,他媽的居然是只!
霍鴻羽當僵了石頭。
“咯咯咯咯咯咯——!!!”
他手里的山撲騰著翅膀,擺出了向往自由的姿勢,聲無比高昂。
霍鴻羽人都傻了,臉上的表開始崩潰。
他手一松,像拿了塊燙手山芋一般,把山扔了出去。
這山是只擅于抓住機會的,困后立刻就扇著翅膀向前飛,跑得十分干脆賣力,中間不知怎麼的,還回頭看了霍鴻羽一眼。
聞鳴玉懷疑自己的眼睛可能出了病,他竟然從一只眼里看到了鄙視——你這人類是不是神經病?嚇死個了!
霍鴻羽折騰完之后,站著好一會沒,似乎還沒從那巨大的尷尬和悲傷中緩過勁來,然后才慢慢轉,異常頹廢地爬上了自己的馬。
考慮到人在青年時期自尊心很強,聞鳴玉早早就沉默地馬轉走開,表示自己什麼都沒看到。
最終時間到,他們兩人要清點獵完賭約。
聞鳴玉倒是想裝作沒有這回事,隨便過掉,但霍鴻羽用力拍著口表示自己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Advertisement
聞鳴玉一看他的臉,就想起他抱著只的樣子,很艱難才能憋著不笑出聲來,幾乎憋出傷,要斷氣了。
確定要繼續賭約之后,兩人站著,空氣里彌漫著一種無聲的尷尬。
畢竟,一個是第一次做狗。
一個雖然以前接過真的狗,但從來沒試過把人當狗。
所以,一時之間,他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完賭約。
聞鳴玉猶豫了一下,說:“不如……我們還是正常點,做朋友吧。”
“我不要朋友!我要做狗!”霍鴻羽像是被侮辱到了,氣憤到口不擇言,說完之后,他反應過來,瞬間漲紅了一張臉,“不是……是那個,賭約!賭約明白嗎?!”
聞鳴玉咬住,拼命忍笑,手藏在袖子里掐自己的虎口,艱難說:“明白,但這總有個期限吧?總不可能,你給我當一輩子的……”
霍鴻羽這才發現自己隨口說的賭注存在,不皺了眉,思索一會才說:“狩獵期間,怎麼樣?”
聞鳴玉點頭,正要說話,旁就走過來一個高大拔的影,擋住,將他籠罩在影里。
“說夠了嗎?”穆湛神不耐,冷聲道。
霍鴻羽瞪大了眼睛,十分驚訝,然后才行了個禮,“參見陛下。”
低著頭,等穆湛讓他起前,他終于遲鈍地意識到聞鳴玉的份。
“你是廣侯的兒子?!”
聞鳴玉很詫異,“你才知道?”
霍鴻羽眼神有些飄,他已經可以想象到他爹娘要是知道這事,那臉會是多難看,瘋狂追著他打,說不定還要他跪祠堂了。
但是,那又能這樣?他話都放出去了,總得說到做到,而且那個可怕的暴君就在旁邊盯著,什麼都知道了。
Advertisement
“孤允許你平了嗎?”
頭頂傳來冷颼颼的聲音,刺得霍鴻羽一個激靈,剛因為震驚抬頭和聞鳴玉說了話,瞬間又低下去,恨不得把頭埋進口里,做一只鴕鳥。
“平。”
霍鴻羽:“……”
暴君是在故意耍他麼?
接著,穆湛從太監手里接過了什麼,慢悠悠說:“你不是不知道該怎麼做嗎?孤可以教你。”
教什麼?
霍鴻羽腦中警鐘大響,不由得防備。
然后,他就看到穆湛晃了兩下手,說:“看見這個球了嗎?孤現在扔出去,你去撿回來給你的主人。”
說完,穆湛還真的手腕一甩,將球扔了出去。他的力氣不小,扔的距離自然也遠。
霍鴻羽:“……”
他一不,沉默地看著球消失在視線里。
他覺得暴君的傳聞顯然不夠全面,可怕是真的,格還極其惡劣,連小孩子都好意思欺負。
穆湛自然能看出他眼底的憤懣和不滿,但作為暴君,他會在乎嗎?穆湛反倒覺得自己太過寬容大度了。答應了讓聞鳴玉去玩,就一直沒阻攔,只是在旁邊看著,當這個霍家小子叭叭叭說話時,也忍住了不爽,沒人打板子,溫和得都有辱暴君的稱號了。
聞鳴玉都沒預料到,被穆湛這一出作弄得有些錯愕,總覺得像在欺負小孩子,忍不住手扯了下穆湛的袖子,小聲說:“陛下……”
沒直接說出來,但眼神里有明顯的意思。
穆湛這回沒順著聞鳴玉,而是說:“是孤他定下這個賭注的嗎?你今年多大了?”
后面那句話,是看著霍鴻羽說的。
霍鴻羽這個叛逆小孩怎麼可能承認自己小,不說今年,而是說:“馬上就十五了。”
Advertisement
穆湛偏頭就瞥了聞鳴玉一眼,眼里的含義顯而易見——看吧,都不小了,說到做到理所應當。
聞鳴玉愣了下,這才想起來,眼前這個所謂的暴君是個年輕帝王,也才十八歲而已,只是他平時做起什麼事來都游刃有余,沒有東西能難倒他的樣子,讓人下意識就把他的年齡放大了。
認真一想,其實穆湛比霍鴻羽大不了多。
不過,高中生欺負個初中生也不是什麼多彩的事吧?
聞鳴玉抿,很想笑。
他忽然發現,穆湛其實……有點稚。
但這點稚放在一個暴君上,竟不讓人覺得反,反而變得不那麼可怕了。
穆湛抬了抬下,居高臨下地看著霍鴻羽,“還不去?”
霍鴻羽心里郁悶,不不愿,但哪里斗得過皇帝,只能聽話點頭,轉跑去撿球了。
穆湛一偏頭,就發現聞鳴玉正盯著他看,雙眼圓潤明亮,像只乖巧又甜滋滋的小貓兒。
“怎麼?”
聞鳴玉搖了搖頭,收回視線,無意識用腳踢了一下地上的小石子,“……沒什麼。”
語調輕快,像是有小人在心里轉圈蹦蹦跳跳。
等霍鴻羽去撿球回來,果然他爹娘已經發現了他和圣上站得很近還說了話的事。
他娘眼圈都紅了,氣得想打他,“都說了多次,讓你小心注意,怎麼就不聽!”
霍鴻羽有些心虛,畢竟是自己之前沒認真聽,才導致現在的局面,又因為自尊心,不想和爹娘說賭約的事,就瞎扯。
“什麼?你還要過去?不怕死嗎!”
霍鴻羽搖頭,“不是,娘,其實那個聞鳴玉人好的,圣上……格是很差,但看起來也不是會隨便殺人的殘忍暴君。”
安寧公夫人都想堵上他的,這是什麼能說的話嗎?!
霍鴻羽又要回去圣上那邊,安寧公夫妻二人簡直就像是看見兒子傻呵呵地主跳進火坑。夫人趴在公爺懷里,眼淚控制不住,低聲說:“怎麼辦?兒子都糊涂到幫圣上說話了,肯定是嚇傻了,還有得救嗎?”
安寧公一臉嚴峻,顯然也覺得事不簡單,心里想著各種方法怎麼救兒子。霍鴻羽完全沒想到,自己給爹娘帶來了那麼大的誤會和驚嚇。
因為狩獵結束了,穆湛已經帶著聞鳴玉坐下來休息。
霍鴻羽撿了球回來,就跟著宮人過去,到了才發現,不只有聞鳴玉和穆湛,旁邊還坐著一個清俊斯文的男人,他后站著一個魁梧如山的男人,那人手里正拿著幾顆核桃,手指一,就咔咔地全碎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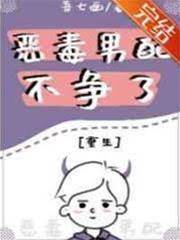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