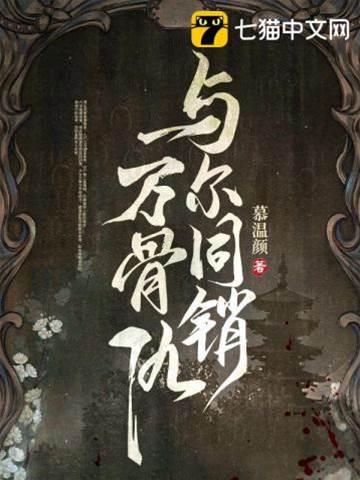《皇城有寶珠》 第96章 不對 不是因為母妃偷偷吃東西嗎?……
“誰說的?”安王被宸王的問題弄得滿頭霧水, “母妃告訴我的,這……有什麼問題嗎?”
雖然鬧出一點意外,但此風景確實還是不錯的。
安王妃與玖珠齊齊扭頭看他, 宸王的表也耐人尋味:“呂昭儀久居深宮,為何知道此的花開得好?”
安王妃意識到事有些不妙, 見自家王爺還不知道事的嚴重, 趕開口:“五弟, 我家王爺一向是糊涂子, 不如我們回宮問母妃?”
“二嫂說得對。”宸王點頭,看了眼被護龍衛擋著,已經嚎不出聲的世家家主, 揮手招來一個護龍衛,對他耳語幾句。
“明小豬,走, 我們回宮。”宸王轉頭看玖珠, 見的目落在那幾個捧酒上,在耳邊小聲道:“你放心, 京兆府的府尹,是秉公執法的好, 并且是寒門出,不會偏幫世家的。”
“我知道。”當第一次走在京城街道上,就知道這是一個太平盛世。
只是即便是盛世,也有人過得苦。
好在, 能有人還們一個公道。
忽然間有些明白, 為何父親與兩位伯伯當年,即使全家被發配,也不愿屈服昏聵之人。
愿輔一明君, 護天下萬民安寧。
剛與家人見面時,父母對很愧疚。但知道,就算重來一次,他們還是會那樣選擇。
而,不怨。
只有父親伯父這樣的員多了,天下的百姓,才有安寧平靜的好日子。
“殿下。”把手放到宸王掌心:“父皇,是一個很好的皇帝。”
宸王微愣,隨后笑了:“你說得對,不過你還說了一句。”
“說什麼?”
“云渡卿,是個很好的王爺。”
“嗯。”玖珠點頭:“殿下是個很好的王爺。”
Advertisement
余簡帶著金吾衛往山上爬,后還跟著兩個拎著藥箱的大夫。
“這些世家貴族喝個茶,吃杯酒,還往這麼高的山上跑,現在被人刺殺,抬下山都費盡。”金吾衛甲問同伴:“一年多以前,被宸王當街嘲諷的讀書人,好像也是世家出?”
當時好像是位世家出的學子,嘲笑一名武將,引起的爭端。后面事鬧得太大,金吾衛這邊怕打起來,足足派了兩隊人馬過去。結果等他們趕到現場時,武將沒跟世家大族的府衛打起來,倒是宸王騎在一匹高頭白馬上,言辭犀利的把世家學子嘲諷得灰頭土臉。
從那以后,在士子文人里口碑本就不怎麼樣的宸王,名聲就變得更差了。
“這事我記得,當時咱倆一起趕過去的。”金吾衛乙來了勁:“那幾個世家學子能說會道,若不是宸王在,那幾個武將肯定會吃虧。”
“等等,前面下來的人……好像就是宸王?”金吾衛甲看著從山上下來的一行人,半瞇著眼仔細看了好幾眼:“還真是宸王。”
余簡停下腳步,心里只有一個想法,怎麼又遇上了。
“參見安王殿下,參見宸王殿下,參見兩位王妃。”余簡抱拳行禮。
“你們來得正好。”看到余簡,宸王已經毫不意外,他指了指山上:“山上那些世家家主,全部關押起來。”
“全部?”余簡有些猶豫:“殿下,您的意思是說,所有都帶去京兆府?”
“先查,能夠證明清白的,再放出來。”
“五弟。”安王拉了拉宸王的袖子,小聲勸道:“那個杜青珂,在文人中頗有清名,而且他還是三弟妹的大伯,連他都帶去京兆府,會不會有些麻煩?”
雖然他一直都知道五弟的膽子很彪,但他萬萬沒想到,五弟的膽子有這麼彪。
Advertisement
“若是他無罪,京兆府自然會放他走。若是有罪,他是誰的大伯都沒用。”宸王道:“二哥不用擔心,若是三嫂有意見,讓來找我便是。”
至于給不給面子,就是他的事了。
“話也不是這麼說的,既然我們倆一起出來,事也由我們一起擔著。”安王想起那幾個可憐的捧酒,又想起自己還要抱大,咬了咬牙道:“你說得對,不管他是什麼份,有沒有罪,由府說了算。”
宸王轉頭看了他一眼,面上出笑意。
“二哥豪氣。”
安王堅強一笑,只是笑容有些苦。
豪氣不豪氣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已至此,他總不能視而不見。
金吾衛趕到山上,兩位大夫看著那個脖子上扎著發釵,已經痛得暈厥過去的世家主,彼此搖了搖頭。
“小將軍。”大夫對余簡作揖:“此傷極為兇險,這位大人只怕兇多吉。”
“兩位大夫請盡力救治,盡量保住他的命。”對這種沉迷酒,欺平民的世家后人,余簡沒有多好。若不是擔心此人現在死了,刺傷他的捧酒會保不住命,他不想管這種冠禽。
“杜大人,請跟末將走一趟。”余簡走到杜青珂邊,對他抱拳。
“誰給你的膽子,讓你來捉拿我?”杜青珂看著這個六品金吾衛小將,把手背在后:“奴仆刺殺朝廷命,你們不去管他們,反而來尋我的不是?”
“末將只是按律辦事,還請杜大人諒。”余簡了腰間的腳鐐,腳鐐發出撞的聲音:“杜大人仁德知義,末將實在不愿用其他手段,把大人帶去京兆府。”
杜青珂冷笑一聲:“那便走吧。”
一個小小的金吾衛,有這麼大的膽子,肯定是背后有人撐腰。
Advertisement
究竟是是誰
難道是……宸王?
呂昭儀正躲在屋子里吃聞起來不太好,吃起來卻很香的一種民間小吃,聽到兒子求見,趕讓宮把小吃端走,漱口,洗手。
“把香也點上。”呂昭儀想起韋昭儀前幾日給送來的香:“韋昭儀送來的那些熏香,味道還不錯。”
玖珠剛走進呂昭儀居住的正殿,就被熏香嗆得噴嚏連連。宸王趕用袖子掩住的口鼻,扶著往外走:“呂昭儀,我家王妃聞不得熏香,請昭儀撤去熏香。”
“快快快,把香爐拿走,窗戶都打開。”呂昭儀慌了手腳,待屋里的熏香味道散盡以后,才重新把宸王夫婦請進屋:“王妃現在可好些了?”
“多謝娘娘,給您添麻煩了。”玖珠聞到屋子里有很淡的,奇怪的味道。
“你們都快座,別站著。”呂昭儀瞪了一眼兒子,邀請宸王一起過來,也不提前說一聲,這個沒用玩意兒。
“母妃,兒媳方才在宮外買了些小玩意兒,您看看喜不喜歡。”安王妃笑瞇瞇地湊到呂昭儀邊,三言兩語把哄得心花怒放,很快就把兒子忘到了一邊。
“幸好母妃告訴了我們那邊風景好,不然我們還不能賞到此等景。”安王妃把茶端到呂昭儀面前:“母妃好生厲害,不出宮都知道京城的景。”
“哪是我知道這些。”呂昭儀接過茶喝了,笑著解釋:“前幾日徐妃娘娘不適,我與韋昭儀一起去探時,聽徐妃宮里人提起的。”
“原來是徐妃娘娘宮里人說的啊。”安王妃扭頭看了眼安王:“徐妃娘娘怎麼樣了?”
“還是老樣子,這些年一直纏綿病榻,好在皇后娘娘心疼,用好藥一直養著,神頭雖然不太好,但無命之憂。”說到這,呂昭儀對宸王與玖珠笑了笑:“這些年,皇后娘娘對我們一直都不錯。若是別人,我們的日子定無這般愜意輕松。”
這話,一半是當著宸王的面拍皇后馬屁,另一半是出于真心。
更重要的是,當年在潛邸做錯過事,這些年一直心虛愧疚,本不敢往陛下跟前湊。
“不打擾娘娘與二哥的天倫之樂,晚輩先告辭。”宸王站起,出言告辭。
“留下用了午膳再走吧。”呂昭儀客套地出言挽留。
“好的,謝謝娘娘款待。”玖珠當場答應了下來。
宸王疑地看一眼,沒有問為什麼,順勢跟著坐了回去。
呂昭儀微微一愣,這不是一句客套話嗎,怎麼還有人當真了?
“能讓二位在鄙用膳,是本宮的榮幸。”呂昭儀很快緩過神來,安排人去小廚房準備膳食。
就是心里非常疑,宸王從不在其他妃嬪宮里用膳,今日這是怎麼了?
安王心卻十分激,五弟愿意在他母妃這里用膳,是不是代表著他抱大功了?
“你們年輕人坐在一起說會兒話,我回屋換服。”呂昭儀扶著宮的手,起離開正殿后,臉上的笑意才消失,轉頭問陪安王一起出去的太監:“王爺今天出去,發生了什麼事?”
特意出去賞景,結果連午時都沒到,就回了宮,肯定是有事發生。
太監回頭看了眼正殿,小聲把事的前因后果告訴了呂昭儀。
“那些世家大族干出這種事,一點都不奇怪。”呂昭儀語氣里,帶著對世家毫不掩飾的厭惡:“先帝在時,世家比現在張揚多了。我還以為陛下登基后,他們已經學會了低調做人,看來他們學得還不夠好。”
太監小聲道:“靜王妃的大伯,也被帶去了京兆府,這是……是殿下與宸王殿下的意思。”
呂昭儀沉默片刻,開口道:“我兒干得好。”
這些年他們母子從不不參與前朝后宮的事,只是不想踏上顯德末年的覆轍,并不代表他們弱可欺。
“命令下就下了,靜王妃心里若有怨,本宮擔著。”呂昭儀看了眼神略有些不安的太監:“更何況還有宸王幫著撐腰,怕什麼?”
“二嫂。”待呂昭儀走后,玖珠對安王妃道:“昭儀娘娘宮里的熏香味道好像有些奇怪。”
“是,是嗎?”安王妃不好意思告訴玖珠,母妃有私下吃民間小吃的習慣,順口答道:“多謝弟妹提醒,我這邊請醫過來,查一查熏香。”
安王不知道母妃私下的好,聽到玖珠這麼說,嚇得臉都變了,趕派人去請擅藥理的醫。
“方才我進殿,也覺得熏香味道不太對。”安王小聲對自家王妃道:“難道有人在熏香里做了手腳?”
安王妃笑得臉都僵了,哪來的什麼手腳,不過是母妃吃東西,來不及讓味兒全部散出去罷了。
至于為什麼如此清楚,不過是婆媳同心,喜歡一塊兒躲著吃罷了。
醫趕過來,看到宸王與宸王妃也在,腳步微微一頓。
上次張嬪香囊有問題,他去查驗時,這兩位好像也在。
這是什麼樣的緣分啊?
“殿下,你別擔心,這些熏香不會有太大問題。”安王妃見夫君擔心得臉都變了,出言安道:“可能是娘娘新換了熏香,您聞得不習慣……”
“殿下,王妃,這熏香確實有些問題。”醫放下熏香,拱手道:“可能是制法的問題,里面有兩味香料藥理相克,若是聞久了,會讓脾胃虛減,消瘦。”
“什麼?”安王妃忍不住口而出:“味道不對,不是因為母妃吃東西嗎?”
猜你喜歡
-
完結642 章

退婚后我成了皇城團寵
一朝穿越,楚寧成了鎮國將軍府無才無德的草包嫡女。 當眾退婚,她更是成了一眾皇城貴女之間的笑話。 可就在眾人以為,楚寧再也無顏露面之時。 游園會上,她紅衣驚艷,一舞傾城。 皇宮壽宴,她腳踹前任,還得了個救命之恩。 入軍營,解決瘟疫危機,歸皇城,生意做的風生水起。 荷包和名聲雙雙蒸蒸日上,求親者更是踏破門檻。 就在楚寧被糾纏不過,隨意應下了一樁相看時,那位驚才絕艷的太子殿下卻連夜趕到了將軍府: “想嫁給別人?那你也不必再給孤解毒了,孤現在就死給你看!”
112.9萬字8 2071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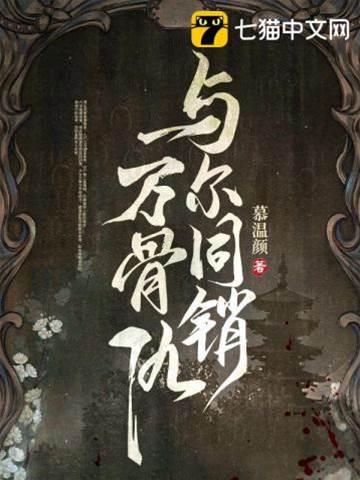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746 -
完結182 章

夫君他清冷又黏人
姜初妤爲了逃婚回到京都,正好在城門口遇上少年將軍顧景淮班師回朝。 他高坐馬上,衆星捧月,矜貴無雙。 是她從前的婚約對象。 正巧,皇帝忌憚顧家勢力,把她這個落魄貴女依婚約賜婚給了他。 新婚夜裏,顧景淮態度冷淡,不與她圓房,還在榻中央放了塊長橫木相隔。 知他不喜自己,姜初妤除了醉酒時抱着他喊“茂行哥哥”,唯一的越界,便只有以爲他身死時落下的那一吻。 可誰知,顧景淮“復活”後,竟對她說: “我也親過你一回,扯平了。” “?!” 她的夫君不對勁。 再後來,顧景淮某夜歸來,毫無徵兆地把橫木撤下,摟她入懷。 姜初妤十分驚訝:“夫君,這不妥吧?” 沒想到素來冷麪的他竟一臉傷心:“夫人怎與我生分了?” 姜初妤:? 翌日她才知道,他不慎傷到了腦袋,對她的記憶變成了一起長大、感情甚濃的小青梅。 他一聲聲皎皎喚她,亂吃飛醋,姜初妤無比篤定這個記憶錯亂的他喜歡自己,卻捉摸不透原來的他是怎麼想的,不敢與他太過親近。 可某日她忍不住了,踮腳在他脣上親了一口。 顧景淮霎時僵住,耳廓爆紅,不敢看她。 姜初妤頓覺不妙,臉色也由紅變白:“你是不是恢復記憶了?” 顧景淮捂着下半張臉,可疑的紅從耳根蔓延到了脖頸。 看來將錯就錯這步棋,下得有些險了。
27.3萬字8 54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