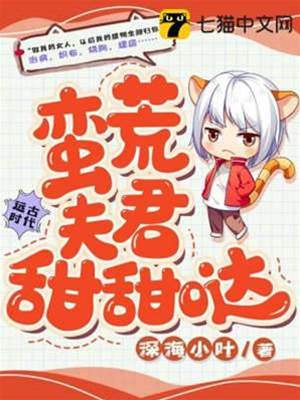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盛世嬌醫》 第三百十八回一對狗男女
["盛方毫不猶豫地接過來,轉,道:“王爺,這軍中旁的人我不信,我隻信我的幾個兄弟。”
趙璟琰角又有黑滲出,了兩口氣道:“好!”
說罷,頭一歪,人便昏了過去。
“爺——”
阿離眼眶又熱,正要撲上去,卻被盛方拉住,“暗衛有幾人?速派二人去報信,餘下的一刻鍾後出發。”
阿離了一包眼淚,道:“共二十人,我立刻去集結。”
“抓!”
日子過得如指尖的流水般飛快。
這日青莞從太醫院回來,剛進院,習慣的問道:“鬆音呢?”
月娘迎上來,“史小姐在後花園呢!”
又往那裏去!
青莞笑笑,道:“我去瞧瞧!”
鬆音自打清明大病一場後,便一直在青府修養,一晃已三四個月了,方養得稍稍好些。
史家派人來接過一回,那時剛端午,鬆音連走路都微有些。青莞怕有事,一口回絕了去。
端午過後,史磊又京打理生意,與青莞一商議,索讓鬆音養到中秋,再跟著送節禮的船回南。
因這一回陸芷雨留在了杭州府主宅大事,青莞又怕史磊在外頭奔波著,無心照顧,所以就一直留鬆音在邊。
青莞剛後花園,便見藥圃中,一老一兩道影穿梭其中。
“小姐,史小姐對藥倒是頗有幾分天份,天天纏著福伯問東問西呢。若不是子不好,隻怕這京中還能出個醫。”
青莞掃了月娘一眼,笑道:“什麽醫不醫的,隻要開心,就讓玩著。這幾日七爺過來著了,沒吵架吧!”
月娘笑道:“小姐說的是什麽時候的老黃曆了。史小姐搬過來後,就再也沒與七爺吵過,兩人見麵雖不熱絡,都恪守著禮數呢。”
青莞苦笑。
Advertisement
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怕就怕這兩個冤家當著的麵,一團和氣,背過頭又吵作一團。
貓兒有九條命,這鬆音卻將將一條命,還是條殘命,可不敢保證下次發病時,自己能救回。
“走吧,不去打擾,這兩天暑氣足,多弄些清火的飯菜調養,不可怠慢。”
“放心吧,小姐,奴婢們怠慢誰,也不敢怠慢史小姐。”
青莞滿意的點點頭,心裏似想到了什麽,收了笑道:“月娘,陪我去那府裏看看。”
“是,小姐。”
青莞所說的那府,便是一牆之隔的顧府。顧府離京,命陳平找中人與顧府買賣。
中人見顧家急著出手,狠了價格,最後以十萬兩銀子。
殊不知當初顧家買下宅子時,整整掏了二十萬兩,再加上當年修葺的銀子,顧家虧了不。
宅子買下後,便一直空著,青莞忙著太醫院和錢莊的事,也沒時間要去打理。
後來,錢福見宅子越來越荒涼,後花園裏野草叢生,遂回了青莞,建議把兩個宅子打通了,並作一。
青莞細細一想,也好,顧府那後花園極大,便是種了草藥也是使得的。
再者說,素來有一個心願,開醫館讓錢家的醫流傳下去,造福百。若心願達,總得有地方讓醫徒們住下。
如此一想,青莞便忍不住了手。正好錢莊那頭分了些利錢,錢放在手上也無事,便索命陳平請了匠人重新翻新。
青莞走進顧府,心頭便有幾分抑。
陳平迎上來,“小姐,都差不多了,還有些收尾的事兒。”
青莞點頭,道:“我去壽安堂瞧瞧。”
“小姐忘了,早沒有壽安堂了,那房舍早就拆了。”
青莞微微一愣,方想起工第一天,便命人把壽安堂連同顧硯啟的書房,一道拆了。
Advertisement
如今的顧府,都是照著記憶中錢家的樣子整修的。
笑了笑,道:“我竟糊塗了!”
陳平笑道:“小姐哪裏是糊塗了,心裏裝的大事太多,便裝不下這些小事。我陪小姐走走看看,如何?”
青莞上下凝視陳平片刻,笑道:“什麽大事,小事,幫你娶一房媳婦,把那些個丫頭片子嫁出去,便是我心中的事。”
陳平一聽小姐說這話,臉漲得通紅。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自己對家立業一點子興趣也沒有,像如今這樣跟著小姐,侍奉老母,日子過得舒坦極了,何苦找個人管著自己。
青莞瞪了他一眼,道:“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與他們不同,大娘養大你不易,絕不可能放你參軍,你死了這條心。”
陳平當場愣住了。自己這點小心思,誰都沒有說過,小姐又是如何知曉的。
青莞不去理他,徑直走進了二門,落腳在從前的壽安堂院門口。
從前每回這宅院,心裏總要膽寒幾下,如今是人非,自己了這院子的主人,卻還有些舊日的影。
皇帝那句罵顧家的話傳出後,顧家在南邊的日子,也不好過,雖說食不缺,但到底不同以往,江南的名門族避之不及,門庭冷卻。
兩位爺也不往外頭去,隻在閨廝混著;夫人魏氏病容纏,吃齋念佛,等閑已不出來見人。
周氏雖理著家,卻早已沒有當年大的風,隻是苦苦支撐著。有道是坐吃山空,賣宅子的錢能撐個幾年,卻撐不了一輩子。
周氏愁白了頭發。
二房兩個庶出的姑娘,因為顧家的原因,遲遲未有人上門提親,仍待字閨中。
劉姨娘,許姨娘心中焦急,卻無計可施,急得如那熱鍋上的螞蟻。
Advertisement
真正應了那句話,因果回,報應不爽。
心裏正想著,卻見銀針滿頭是汗的小跑過來,氣籲籲道:“小姐,小姐!”
“出了什麽事?”
銀針一抹汗,道:“小姐,英國公世子和八小姐來了,正在花廳裏等著呢!”
顧青莞聽罷,不解道:“他們來做什麽?”
“說是給六小姐送喜來了。”
給送什麽喜帖,怕是炫耀來了吧!
青莞淡淡一笑,“不必理會,且讓他們等著吧!”
話音剛落,春泥蒼白著小臉,飛奔過來,“小姐,小姐……”
“你慌什麽?”
春泥咽了口口水,道:“小姐,蔣七爺也來了,幾句話一說,便和世子爺打了幾來,勸都勸不住,這可怎麽是好?“
顧青莞抬頭看了看紅得刺眼的晚霞,清亮至極的眸子微微一彎,“那咱們便不急,讓他們打累了再去。”
“呃?”銀針和春泥對視著,一頭霧水。
小姐怎麽這麽淡定,換了別人急都急死了。
花廳裏,兩冰盆散著淡淡冷意。
蔣弘文高大的形斜坐在太師椅子裏,玉冠不知掉落在何,幾縷發垂落在眼前,一副放不羈樣子。
無人察覺到,那被發遮住的眼中,出一抹痛。剛剛得到消息,亭林出事了。
對麵的殷立峰也不曾好到哪裏,月牙白的袍上占了灰,臉上有抓痕,很狼狽。
簡單莫名其妙,他好好的在花廳裏等顧青莞,不料這蔣弘文衝進來,就像隻瘋狗一樣咆嘯。
他堂堂英國公世子,貴妃最寵的侄兒,哪裏能咽下這口氣,當場與他幹起架來。
殷黛眉心疼弟弟傷,看向蔣弘文的目,帶了幾分不屑,“堂堂戶部侍郎,語出狂言,手傷人,一點子世家大族的規矩都沒有,莫不是你欺負我英國公府無人。”
蔣弘文冷笑,“欺負你們又怎樣?”
“你……”殷黛眉氣結。
“我什麽我?”
蔣弘文起,挑釁的抬了抬下,“我是沒規矩,不過你也沒好到哪裏去,當年你足蘇、錢兩家的醜事,爺記得清楚的很!還世家小姐呢,哼,萬花樓的也不如!”
“你個混蛋!”殷立峰豈會讓人這麽侮辱他的姐姐,又衝了上去與蔣弘文扭打在一。
蔣弘文忙裏空,朝氣得兩眼冒火的殷黛眉挑了挑眉,“什麽狗屎的金玉,依爺看,就是一對狗男!夫婦!”
殷黛眉捂著心口搖搖墜。
長這麽大,還從來沒有被人如此狠毒的罵過,這蔣弘文……這蔣弘文……
殷立峰一聽,氣得肺都炸了。
直娘賊,吃了熊能豹子膽,竟然敢這樣罵八姐,本世子不打得你滿地找牙,跟你姓!
蔣弘文見殷立峰目兇,眼中芒一閃,一個,把原本著他的殷立峰翻倒在地,雨點般的拳頭落了上去,邊打還邊罵。
“別仗著宮裏有個貴妃,便不知天高地厚,今兒個,就讓你嚐嚐我蔣七爺的拳頭。”
殷黛眉心頭大怒,對著外頭帶來的人,厲聲罵道:“你們都是死人啊,還不回府搬了救兵來,世子爺被人欺負這樣,天子腳下沒王法了不?”
一旁的春泥,彩雲一聽這話,急得都了。
小姐呢,小姐怎麽還不來,這兩位爺,勸又不敢勸,攔又攔不住,哪一位都得罪不起,事鬧大了可如何是好啊!
“誰在我府上撒潑?”
人未到,聲先至。
春泥等人一臉劫後餘生的表。小姐,你總算是來了,再不來,這天都要塌下來了。
一道清麗的形慢慢走進來,紅輕輕一,“沒關係,你們繼續,誰傷了,誰瘸了,我來治!”
此言一出,適才還聒噪喧嘩的花廳裏,靜謐如水。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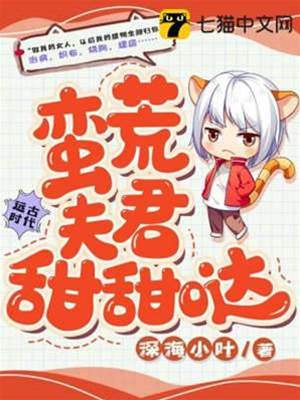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完結1138 章

世子妃重生後黑化了
【真假千金】她楚妙,本是丞相府嫡長女,卻與村婦之女錯換了人生;被家族尋回,成為父母與皇室的一顆棋子。 她被哄騙嫁給平南王的嫡子蕭容瑾;公公是從無敗績的戰神,婆婆是燕國首富之女,丈夫體貼溫柔也是頂天立地的好男兒,蕭家兒郎個個尊稱她為一聲「嫂子。 可她滿眼是那站在陽光下的白月光,負了蕭家滿門。 蕭家倒,她被家族棄如螻蟻,捧那村婦之女為帝后,告訴她「你天生命賤,怎配得上孤。 重生回來,蕭家七子皆在,她依然是他的世子妃,蕭家眾人捧在掌心的嬌嬌媳;但這一次,她要顛覆這江山!
110.3萬字8.18 318897 -
完結509 章

戰神醫妃要休夫
她堂堂星際戰神,竟然穿成備受欺凌的懦弱王妃?被人欺負可不是她的風格! 下人欺辱,她打了! 小三猖獗,她滅了! 老公不愛,她休了! 一個人富可敵國她不香嗎?一個人隻手遮天不爽嗎?只是這廢柴王爺怎麼回事?死皮賴臉要做她的上門老公?看在他能接她那麼多招的份上,勉為其難的收了吧!
95.2萬字8.18 206547 -
完結193 章

榻上歡:冷麵攝政王索取無度
昭國太後蘇傾月是寧國公府自幼被抱錯的嫡女,可是大婚之夜,先帝駕崩,攝政王慕瑾辰入了她的洞房。他們立場敵對,目的相悖,他給予她所有的冷酷,漠然,卻又在深夜,抵死糾纏。密不透風的深宮牢籠之中,她清醒地掙紮,沉淪,期盼與絕望中輾轉,本想一走了之,卻又被慕瑾辰緊緊攬進懷裏,訴說著從不敢期待的情意綿綿。
35.4萬字8 145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