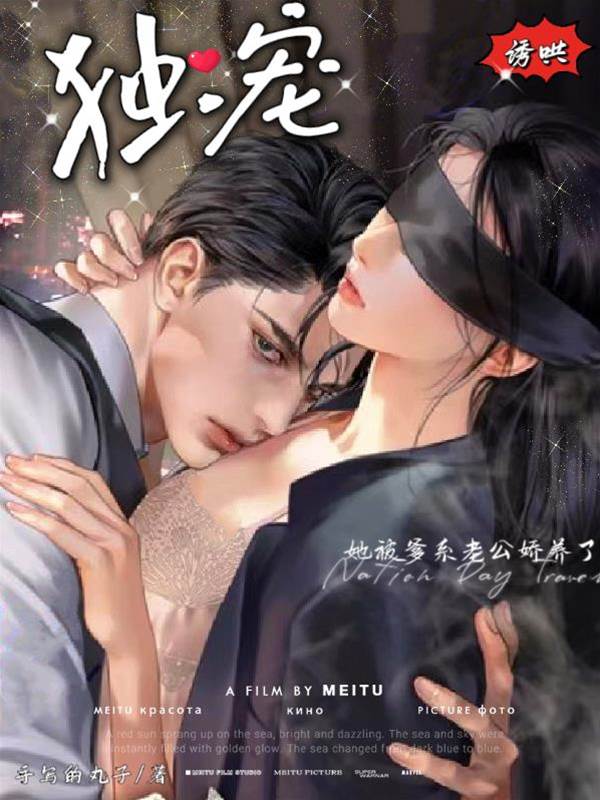《女校》 第八十二章 隨便
高二暑假龍七在靳譯肯家長期留宿的那幾天,他弟靳暠上了一項追星的燒錢活,倒不是說真飯上了某個豆,而是這小子那時在泡的一個姑娘,正好是一個明星。
到底是富裕家庭里養出來的小孩,小小年紀看中的妞都不一樣,還興姐弟,說對方是星出,也是高二在讀生,雖然年齡上和靳暠差了半,但他從小看著的電視劇長大,簡直是不得了的迷弟,巧人家把房子買進了朗竹公館,前兩天剛住,靳暠一打聽完就在家里忙得連軸轉,抓耳撓腮想方設法和人家搭上話。
那時候也是夏季里最熱的伏天兒,靳譯肯家院里的遮篷壞了,天泳池簡直是一鍋沸水,就天和他弟窩在別墅里,靳譯肯要帶去見朋友吃飯,不樂意,要帶遛狗,不樂意,要帶去涼快的省市玩幾天也不樂意,反正踏出這個冷氣大別墅就不樂意(因為來他家之前被龍信義家的破空調吹得差點中暑,被靳譯肯撈過來才撿了一條命),然后就迷上了那賽車游戲,天天玩,被好歹也打GTA的靳譯肯鄙視了兩天,后來他閑得無聊,隨口問了靳暠的泡妞進度。
靳暠這小子賊機靈,立刻沖著他哥把局勢一擺,說人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除了傍晚五點準時遛兩小時狗外本見不著人,靳譯肯問是什麼狗,靳暠說是約克夏。
靳譯肯也沒說什麼,從網上找了種狗糧照片,給靳暠一發,靳暠就秒懂,第二天這附近寵店囤積的這類牌子的狗糧就全運到了靳家,他還唆使他弟弄了只小型犬過來,每到五點帶去遛,之后靳譯肯就不管了,開始管怎麼教龍七開車這事兒了。
Advertisement
也虧了靳暠每天乖乖遛狗,每天五點到七點之間就是靳譯肯跟好好辦點“正經事”的時候,龍七閑來沒事問他打的什麼算盤,他說就是把他弟支出去,說:“不是,我說囤狗糧,你幾個意思?”
“那家子剛搬來,狗糧沒帶夠,狗又專挑一種牌子吃,網上買不到,你說能去哪里買。”
“寵店啊,”又問,“那你怎麼知道狗糧沒帶夠?”
“耳朵用來干嘛的?”
“你這麼牛,千里耳?”
“寵店打電話進貨說況的時候,這家伙,”那只傻阿拉斯加叼著龍七的文在床尾竄來竄去,靳譯肯朝它“嘖”一聲,“正被我帶著修。”
“!”龍七攥枕頭扔向狗,阿拉斯加躲得極快,叼著文跐溜一下往門外竄。
而靳暠果然也不負眾,三天之后,妞就上門了,靳暠在那之前早把狗糧藏得嚴嚴實實,只在客廳放個半包,然后一副大義分的樣兒送人家,接著又說儲室里還有一包,恭恭敬敬地將在客廳供著,自己去找。
龍七那個時候在樓上洗澡,靳譯肯下樓去了趟廚房,等洗完澡下樓的時候,那姑娘正在客廳的中央站著,懷里抱著一只約克夏,手輕輕地著,而視線,正投向開放廚房的靳譯肯。
靳譯肯那會兒里叼著半塊切片面包。
他一手開冰箱,一手拿蘇打汽水,飲料罐在他手心咔一聲拉環,氣泡上浮,把冰箱門合上的同時側頭,注意到客廳站著的人,但沒看第二眼,只往傳出聲響的儲藏室撂了撂視線,繼而專注自個兒手上的事,問:“等我弟?”
姑娘還沒答,他又說:“吃過晚飯了?”
“……晚飯?”
Advertisement
“我弟還沒吃過。”
龍七套著件白T恤下樓,頭發半半干,發語音催促龍信義修空調,無前兆地打斷兩人的對話,靳譯肯的注意力往那兒挪,用下指了指鍋子里滋滋響的煎蛋。
那孩隨之收了視線,手指在約克夏的邊逗了逗。
而龍七沒來得及看客廳,就被樓梯口一陣巨響的下樓聲轉移注意力,阿拉斯加又叼著的文竄下來“領賞”,瞬間炸,返就去追狗,這傻狗越跑越興,哈赤哈赤地著氣,一路追到樓上,從臺追到閣樓,又從閣樓追到臥室,最后發飆:“靳譯肯你給我弄它!”
那個時候,龍七不知道,靳譯肯被這出“鬧劇”惹得笑嘻嘻上樓的時候,客廳中央的那孩依舊長久地看著他。
空調無聲地出冷氣,院子蟬聲高鳴,空氣里冒著煎蛋的油焦味,看著靳譯肯從前經行的樣子,看著他的眼,他的眉,他勾著的角,他拿著盤子的手,看著這個只與自己產生過一次對話的人,沒有對視,沒有任何神上的相通,卻就是有燥熱在兩人之間流,靳暠興高采烈地帶著狗糧遞到跟前,置若罔聞,任由懷里的約克夏咬的手指頭,那種細微的從指尖蔓到心頭,調制著一種連自己都說不清的,天雷勾地火般的初見鐘。
也不住。
鄔嘉葵就是這樣惦記上靳譯肯的。
可憐的靳暠,費盡心思弄來搭訕機會,卻不知不覺為他哥鋪好了另一張溫床。
完完全全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龍七已經在頤明灣地下停車場,凌晨一點整,停車場萬籟俱寂,一小時前從夜場大門出來時的寒風早已將里的酒消磨殆盡,此刻腦袋無比清醒,坐在蘭博基尼的主駕駛,車窗全開,左手在窗外,指頭夾著煙,撣著煙灰。
Advertisement
車浮滿嗆人的煙味兒。
約十分鐘后,口傳來跑車厚重的低鳴聲。的指頭在方向盤上一下一下,緩慢地叩,直到引擎聲越驅越近,轉進所在的車道,看到標志車頭的剎那,打開車前燈。
“啪”地一聲。
明亮又刺眼,使靳譯肯的車停頓了一下,副駕駛的鄔嘉葵抬手遮額,兩輛跑車一明一暗,一黑一藍,猝不及防地在停車場的兩端對峙,等到燈的刺激漸漸減小,鄔嘉葵才放下手,看清遠車的龍七。
之后的反應,是在當下側頭,看主駕駛的靳譯肯。
靳譯肯并沒反應。
他原用單手控著方向盤,另一手拿著手機,正回著什麼消息,因前方刺眼的而抬眼,隨后,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瞇一下,就這麼八風不地看著幾十米外“攔道”的龍七,慢悠悠地放下手機,也不鳴笛,不進不退。
龍七看著他們倆。
甚至已經想象到,他倆上樓后能做些什麼,也仿佛聽見鄔嘉葵此刻如同擂鼓的心跳。
怨。
煙燒到了尾端,煙頭掉到地上,竄起微小火星。
踩油。
車胎與地面,儀表盤指數飆高,停車場一陣嘯鳴,車子直沖著靳譯肯的方向去,睜眼看著,看靳譯肯到底給不給反應,在兩車距離只剩30m的時候仍不減速,油門踩得更重,副駕駛鄔嘉葵的口起伏,沒什麼表緒的肢作,但一眼不眨,靳譯肯的手搭著方向盤,安靜地看著一個近乎發瘋的。
直到兩車相距10m,近乎相撞的前一秒。
靳譯肯的手部才有作。
車子隨之往后退,一個利落的大倒轉,不偏不倚地轉一空車位,鄔嘉葵因慣朝前傾子,手撐住車子前臺,柯尼塞格的車頭與蘭博基尼的車近乎“”而過,他就這麼為龍七的“同歸于盡”讓出了條道,龍七的油踩得更重,那一秒已經沒什麼理智,也本不想在這個地方逗留,越過他,豪無減速地上坡出停車場。
引擎聲從地下傳到空曠的地表,除夕夜后凌晨一點十一分的馬路沒有第二輛車,寒風凜冽,咬著下,看到路燈下的飄雪,看到頤明灣萬家燈火,卻從后視鏡看不到那輛本該跟上來的車,牙齒松開,嘗到一腥,手指仍摳著方向盤,被一本無法松口的氣死死纏著,指甲都快摳斷。
靳譯肯一直,始終,都沒有跟上來。
回劇組酒店的時候,已經近乎行尸走。
上仍掛著臧習浦的大,一步,一步,一步地走,曾在腦導演過一萬遍靳譯肯回來時的場景,卻本沒想到這一種,沒想到有一天導演的畫面會出現另一個人,靳譯肯親過,開車載過,帶著回頤明灣,回那幢連龍七的服都沒搬完的房子,因為預想得到在那個房子里能發生的每一個畫面,全都細微發抖。
怎麼回事呢,怎麼之前和董西在一起的時候,就沒換位思考過靳譯肯的呢。
所以,原來是這種。
就這麼無意識地走,覺不到零下的溫度,還沒到自己房間,經過的一間房正好開了門,暖照亮一方地毯,到刺眼,朝另一邊側額,臧習浦的王助理帶著一些外賣盒從那扇門出來,看見,口而出:“咦?
隨后返進門,沒過幾秒,臧習浦的聲音就從房傳出,龍七適應亮看向他時,他正將門敞開,暖罩著他半邊臉,他穿著單件的高領,戴著副平時不常見的眼鏡,手持用不同的筆做著記號的臺本,似乎剛看到一半,問:“回來了?”
隨后,視線掃過上的羊大,把在門把上的手進兜,再輕問:“沒回過家?”
……
“沒有。”
腦子昏昏沉沉的,低聲回,但意識還是稍微有一點,抬手到領口解扣:“臧老師,我把服還你……”
大褪到肩部,被臧習浦的手止住,王助理在一旁著門看著,龍七冰冷的手與他的手有一秒相,他說:“明天再還。”
隨后往一旁吩咐:“小王,陪回房,照顧照顧。”
老坪和邊的助理都回家了,酒店房間的暖氣剛開,也是冷颼颼,又往窗邊的沙發坐著,不肯挪位也懶得添,王助理往的上蓋了條毯,隨后看了看圓茶幾上的兩瓶紅酒(之前讓PUB的服務員送來的),最終沒有多管閑事,把暖氣開到最足后,走了。
一個人的胃里到底能消化多酒。
喝到多的時候,能把腦袋里臆想的畫面都散盡。
不知道,只近乎出神地著酒店樓底,這個除夕夜的雪那麼大,下不盡似的,在道路兩邊積起厚厚一層,看到凌晨兩點整的時候,在酒店門口吵架的周以聰與其經紀人,他們吵得那麼激烈,仿佛積了多年的緒一并發,奔潰的經紀人被落在酒店門口,看著甩車門而去的周以聰。
冰塊在杯底撞,晶瑩剔。
看到凌晨兩點一刻的時候,酒店門口徘徊著打電話的鄔嘉葵姑媽,在空氣中比劃著手,快速講話不停,看似強悍的臉上布滿未老先衰的法令紋,的助理在一旁瑟瑟發抖地等著,堅守自己收微薄的崗位。
……
凌晨兩點半的時候,一輛出租車停駐在酒店門口。
龍七在布滿暖氣的房間里看著,看到從車中下來的鄔嘉葵,側沒有旁人,垂頸的短發被吹得凌,孤零零地迎向著急上前的助理,沒說話,沒有多余表,只在姑媽試圖拉住手臂時不著痕跡地開,一行人沉默地進酒店。
相距幾十米的樓上,龍七循環往復地喝酒,腦袋里遲鈍地計算著頤明灣到這里的路程,以跑車的速度,約半個小時,以出租車的速度,大約一個小時,所以從一點十分到兩點半,加上出租車的時間……鄔嘉葵在那里待了十分鐘不到。
靳譯肯沒有送回來。
空酒杯放回桌面,杯底與玻璃面發出清脆撞聲,那個時候肢已稍許麻木,全管再次被酒灌滿,看著樓下那輛出租車,大概除夕雪夜接不到乘客單子,司機仍將車停在門口,熄了火,靜止不。
猜你喜歡
-
完結376 章

離婚后渣攻后悔了
蘇墨這輩子都沒有想到自己26歲時收到的最大的生日禮物會是楚世瀟的一句,“離婚吧。”“如果我有了孩子呢?”蘇墨緊緊咬著自己的嘴唇,試探性地看著他。“打了,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牽扯。”“我……只是開玩笑的。”—五年的相知相守,終究抵不過白月光輕描淡寫...
90.7萬字8.33 17763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
完結301 章

寶貝乖,京圈大佬日日誘吻小公主
已完結,歡迎入坑!【奶兇哭包小瞎子VS陰鷙腹黑忠情狗】【雙潔 甜寵 先婚後愛 破鏡重圓 雙向救贖】蘇南星有一雙漂亮得會說話的眼睛。隻可惜一場車禍讓她失去了光明,也失去了記憶。為了給哥哥還債,她做了衝喜新娘。嫁給了京圈人人畏懼的瘋批大佬薄司宸。薄司宸是頂級豪門薄家掌舵人,他性格暴躁,冷血陰鷙。為了奶奶娶了一個小瞎子當老婆。可他沒想到,小瞎子竟然是兩年前渣了他的前女友。他目光陰鷙地盯著她:“想賣慘讓我再愛你?這輩子都別想!眼睛好了就離婚!”可是後來有人看到,小瞎子演出結束,被男粉絲抱著鮮花追求。向來清冷禁欲的小薄爺突然把人拽到自己懷裏,親了一下小姑娘的唇說:“我老婆,懂?”看到蘇南星直播,跟粉絲一口一個‘我愛你們’互動,隱忍很久的男人終於按捺不住,把人抵在牆上,滿眼瘋狂和熾熱,“寶寶,求你也愛我好不好?”這大概就是一個口是心非的狗男人真香現場的故事。備注:女主眼睛會好,女主不渣,當年分手有原因,後期會解釋
56萬字8 33247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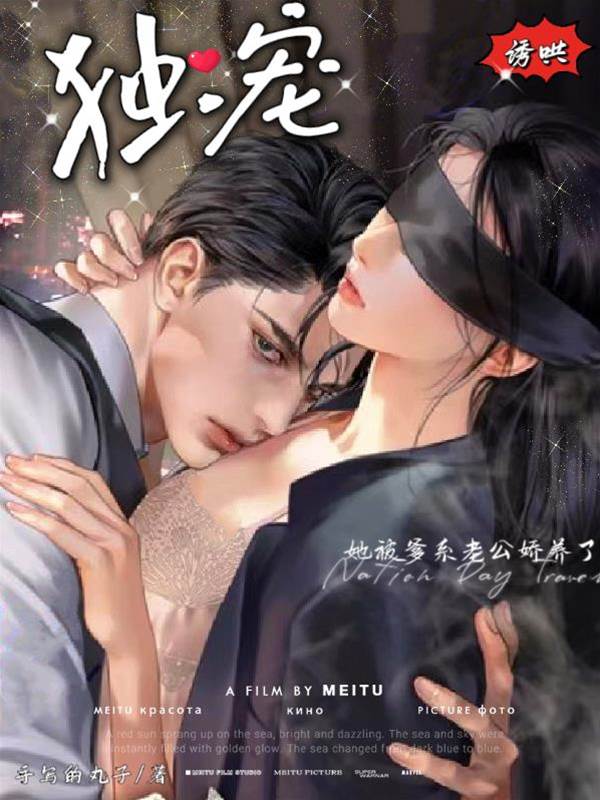
獨寵!誘哄!她被爹係老公嬌養了
1v1雙潔,步步為營的大灰狼爹係老公vs清純乖軟小嬌妻 段硯行惦記那個被他撿回來的小可憐整整十年,他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設下圈套,善於偽裝人前他是道上陰狠殘暴,千呼萬喚的“段爺”人後他卻是小姑娘隨叫隨到的爹係老公。被揭穿前,他們的日常是——“寶寶,我在。”“乖,一切交給老公。”“寶寶…別哭了,你不願意,老公不會勉強的,好不好。”“乖,一切以寶寶為主。”而實際隱藏在這層麵具下的背後——是男人的隱忍和克製直到本性暴露的那天——“昨晚是誰家小姑娘躲在我懷裏哭著求饒的?嗯?”男人步步逼近,把她摁在角落裏。少女眼眶紅通通的瞪著他:“你…你無恥!你欺騙我。”“寶貝,這怎麼能是騙呢,這明明是勾引…而且是寶貝自己上的勾。”少女氣惱又羞憤:“我,我才沒有!你休想在誘騙我。”“嘖,需要我幫寶寶回憶一下嗎?”說完男人俯首靠在少女的耳邊:“比如……”“嗚嗚嗚嗚……你,你別說了……”再後來——她逃他追,她插翅難飛“老婆…還不想承認嗎?你愛上我了。”“嗚嗚嗚…你、流氓!無恥!大灰狼!”“恩,做你的大灰狼老公,我很樂意。
15.9萬字8 12612 -
連載232 章

嬌縱她
嫁給厲衍川三年,薑晚是海城所有貴婦的標桿。白天是端莊大方的厲太太,晚上是厲衍川食髓知味的小妖精。可即便如此,他心中仍有不可碰觸的白月光。當他又一次選擇護住對方時,薑晚終於明白,有性無愛的婚姻,永遠是虛無的海市蜃樓。於是她放下執念,選擇離婚。離婚後的薑晚宛如新生,驚豔世界,享譽全國的新貴當眾求婚。“沒興趣結婚,更不會和你結婚。”“不結婚,那複婚呢?”海城最衿貴清冷的厲先生開始死纏她不放。厲衍川瞇起黑眸,抵她在床,“P友也行!薑晚,沒有人比我更能滿足你。”她撩開發,笑了。“所以,你選周一三五還是二四六?”
42.4萬字7.58 13927 -
完結141 章

倒追三年沒結果,轉身大佬攬入懷
【追妻火葬場直接揚灰+男二上位+腹黑男主+雙潔】娛樂圈這個花團錦簇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真心,梁瓷卻偏偏捧著一顆真心到時宴跟前,毫不意外,被摔得支離破碎; 男人居高臨下地問她:“梁瓷,你是不是忘了,我們之間是什麼關系?” 梁瓷沒忘,不過她在此之前一直心存幻想,如今幻想破滅,她也逐漸清醒。 梁瓷退圈的那一天,網上幾乎都是冷嘲熱諷,更有甚者,明目張膽地指出她退圈不過是被金主時宴拋棄了。 消息傳到宴時那,男人只是笑笑,毫不在意地問著“關我什麼事”; 直到有一天,他路過一家寵物店,看到那熟悉的低眉淺笑,時宴卻發了瘋般的沖進去緊緊地把人拽住:“你去哪了?!” 往日溫順柔軟的梁瓷卻強硬地弄開他的手,笑盈盈地看著他的身后:“不好意思,你擋住我先生了。” 那天之后,時家二少瘋了。
25.9萬字8 175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