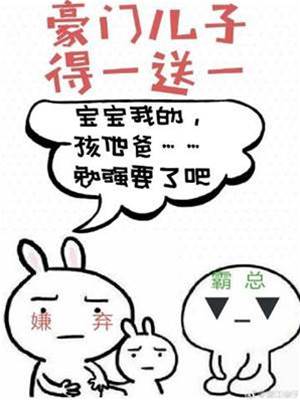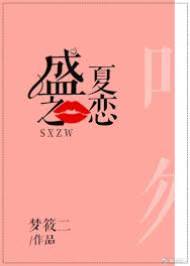《誤撞成婚:緋聞總裁複仇妻》 第七十一章 回國發展
不管怎麽說,一定要照顧好自己,照顧好自己的安全。
季晴不知道,一向都膽大心細的閨,為什麽對那個白碧萱背後的男人那樣的擔心。
顧一笙告訴:“因為景琛過去就查過這個男人,他是白碧萱的第一個男人,在和簡晟風在一起的時候,就是和他廝混在一起,才能有了進上流宴會的權利。”
不然,就憑借一個小小的孩,如何能認識簡晟風他們這些人,顧一笙還告訴,重重資料顯示,白碧萱陷害他住監獄的那個孩子,也是他的骨,而非簡晟風的。
“我靠,這個人,真可怕!那你為什麽和那個姓耿的對話那麽久,都認不出來他是不是景琛調查的那個人?”
他們的手裏有一堆資料,足以證明兩個人有非凡的關係,但是耿祁是做什麽生活的,他們誰都查不出來。
同時,陸景琛說過,他是自己見識過的最狡猾的一個人,從來都不會摘下那個當了半張臉的,反效果極佳的墨鏡,估計隻有最親的人,才能見識到他的本來麵目。
所以,憑借這殘存的片段,顧一笙隻是猜測,那天見到的男人,就是他,卻不敢篤定。
“張助,我的琴幫我取下來吧。”在沙發上發呆坐了半響,還是拉拉琴吧,音樂能使人冷靜下來,不要繼續胡思想。
陸景琛耳聰目明,如果把琴放在明,他肯定會敏銳的捕捉到,所以每次顧一笙拉過了之後,都會擺張琪把琴舉到最高的櫃子上,推到最裏麵死角的位置。
“好的。”張琪挪過去凳子,其實蠻羨慕這個顧小姐的,雖然現在是一個沒有背景沒有親屬的孩,顧氏集團也隻是S市一個故去的神話。
但是你在上,無論什麽時候,都能看到一種積極生活的態度,一點破落的跡象都不曾在上看出來。
Advertisement
一曲悠揚的曲子之後,顧一笙的眼神有些呆滯,顯然是在思考著問題,剛剛拉親的時候也有些不走心:“張助,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從你的角度分析下,白碧萱是一個無利不起早的人,為什麽突然要進這個行業。”
這個問題,陸也問過,說是問到不如說是自問自答,陸的意思是,這是一步棋,下在了棋盤的中央,四周還會有其他的棋子包圍過來,隻是現在還沒有啟而已。
而自己的理解卻是:“一直是一個自負貌的人,或許是真的不甘心一直在簡氏默默無聞吧,又或許,是你和陸合力讓的那些技倆敗,他和簡晟風已經岌岌可危,貌合神離,為自己找的一條後路?”
一切,似乎都是合合理,但是總覺得並沒有那麽簡單。
太的位置突突的跳,算了,不想也罷,景琛的生日就快要到了,現在需要憧憬那些即將發生的浪漫的事兒。
太平洋的另一端。
“譚總,您最近讓我一直關注的國市場,有了新的向。”
“譚總,這是S市這兩年來,中央辦公區的寫字間的租金和賣價,都在這裏。”
譚晨的手指按在紙張上,是的,自從那個蠢人,不遠萬裏的執意要回到那個大坑之中,他就在研究國的市場:“把這些國一直想和我們合作的客戶電話給市場部,讓他們把我準備回國開市場的消息散發出去。”
“是。”
助理端正的立在一旁,但是步履踟躕,好像有話要說。
“有什麽話,直說就是,言又止的,在我邊工作多年,我有那麽不近人嗎?”他把鼠標扔在一邊,雙手叉的看著他的助理。
別的老板總裁,總是男總裁邊配一個助理,強人邊有一個小男人,但是譚晨從來不遵循這種潛規則似的規矩,到談生意的時候,後跟著的都是一個和他一樣清瘦的年。
Advertisement
年張凡,眉宇間有一濃濃的書卷氣,不知道是不是做件的男人都是這樣,從表上就能看出來,是一個習慣用代碼運行,代替語言辯論的人。
“譚總,我不懂,你作為一個華人在國能夠創業,擁有很多國人都不能取得的就,為什麽還要回去國發展,你應該比我更清楚,在國外發展,回到國或許很容易被接,但是從國再回來,想要達到繼續蒸蒸日上的狀態,就是難上加難!”
他是在為他跟隨多年的老板擔憂,畢業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留學生,拿著簡曆到壁。
無一例外的看見他的國籍之後,都是淡淡的搖頭拒絕著他的簡曆。
“先生,你的履曆真的很優秀,但是很抱歉,暫時我們沒有位置給您。”這句話他聽的幾乎耳朵都起了繭子,一度懷疑,這是這幫國佬同氣連枝打好的草稿一般。
機遇巧合,或許就是上天的命運,譚晨剛剛起步的公司就被他撞上,也許那個時候還不夠做公司的規模,隻是一個小小的寫字間裏的兩個對著電腦敲代碼的野心家。
“張凡,你還記不記得咱們剛剛起步的時候。”
他當然記得,“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吃隔壁街角的一家熱狗吃到後來,問道熱狗的的味道就想吐。”
那個時候都能熬過來,並且現在已經做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麽是舍棄不下的。
“你人機靈,又是和我一起打拚出來的,我不打算完全把國這邊的公司放下,所以,我必須把他付給一個我信任的人。”
他的目落在張凡的上:“你留下來,在這裏幫我繼續運營這公司,我回國,就當是立一個分部。”
不得不做這樣做,那個人對他來說,比一個IT公司的董事長重要的多。
Advertisement
“這樣不妥啊總裁,還是我去中國吧,你有什麽吩咐,無論是生活上的還是工作上的,都可以給我,我幫你照顧。”
誰能代替的了自己呢?他果斷的搖搖頭,這是他深思慮之後做下的決定,去國的機票需要盡快定好,把這邊手頭的事解決的差不多,就趕快回去在S市紮穩腳跟。
注定是輸給了,那個人。
既聰明又蠢的人。
“醫生,我想諮詢你一個問題。”齊雨薇流利的用英文詢問著麵前的醫生,小心翼翼的把墨鏡帶好,肚皮上的服放下。
“請說。”
“您說我的狀況,做飛機的話,會不會對胎兒和自己造什麽危險?”
齊雨薇的聲音小小的,弱弱的,醫生湊近了一些才勉強聽的出來。
“坐飛機?要坐飛機去哪裏?”
“a!”
碧藍的眼睛瞬間是掙的圓圓的,這個中國的人是不是瘋了,在胎兒還沒有穩定的時候,竟然要坐飛機橫一個太平洋。
隻不過,驚訝隻是持續了一瞬間,這沒什麽不可以的,因人而異,的機能,和府中孩子的長都一切順利,所以隻是把所有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和如何應急的方法都說了一遍。
至於還會不會冒險去坐飛機,就是個人的問題了。
回到家的齊雨薇換上了寬鬆的睡,坐在沙發上喝了一大杯的白水,手勢輕的在還並不明顯的肚子上:“寶貝,你要堅強些,要知道,咱們回去是看爸爸的!”
這是的主要目的,至於顧一笙,的嫉妒心在作怪。
擁有的東西,竟然忽然橫空出來一個人與爭搶,就算不要了,不喜歡了,也不應該到一個做過監獄的人分。
簡晟風說的對,就算陸景琛對自己隻有恨,毫無覺了,自己的回歸,也定然會讓某些人各歸各位。
“顧一笙,顧一笙。”茶幾上的那張照片被拿起來,放在眼前細細的端詳,這個人清麗俊俏,如果不是陪伴在陸景琛邊,說不定自己並不會對這麽大的敵意。
那可是,陪伴了四年的男人。
翻了翻手機,從這個月宣布取消一切工作和活安排開始,手機的備忘錄裏空空如也,隻有一條。
景琛的生日,回國趕通告。
兩個事件拍在一起,一個是生活,一個是工作,回國的行程看起來無懈可擊。
對於準備今後選擇在國發展主要事業的決定,也引起過的采訪,各種各樣的猜測也紛杳而至。
但是都一直保持著沉默,選擇了一個方的答案,無論是誰詢問,都會說是因為,故土難離。
陸家的大門,朝哪裏開的都快要忘了,但是仇恨並沒有忘記。永遠記得那個迂腐的老頭,和那個勢力的士,他們當年毫不客氣的將自己貶低的一無是。
如今,的角一抹冷笑浮起,再也不是那個初出茅廬,遇到事隻會逃走的齊雨薇了。
產檢報告被收好,在行李箱的最底層,下一次的產檢,就會在S市的醫院進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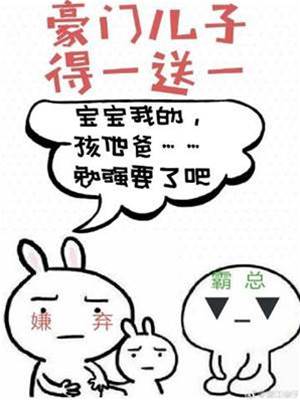
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別人去當后媽,要麼是因為對方的條件,要麼是因為合適,要麼是因為愛情。 而她卻是為了別人家的孩子。 小朋友睜著一雙黑溜溜的大眼,含著淚泡要哭不哭的看著林綰,讓她一顆心軟得啊,別說去當后媽了,就算是要星星要月亮,她也能爬著梯子登上天摘下來給他。 至于附贈的老男人,她勉為其難收了吧。 被附贈的三十二歲老男人: ▼_▼ ☆閱讀指南☆ 1.女主軟軟軟甜甜甜; 2.男主兒砸非親生; 3.大家都是可愛的小天使,要和諧討論和諧看文喲!
31.8萬字8.33 47271 -
完結437 章

少帥的冷情妻
結婚三年,她是雙腿殘疾的卑微愛慕者,他是令人畏懼的江城少帥。他從來不屑碰她,對她厭惡至極:”我不需要你生的孩子。“真相大白,婚約不過是一紙陰謀,她終于下定決心離婚。沈晚吟:“簽字吧,以后我們各不相欠。”“少帥,夫人懷孕了!”傅北崢震怒,撕碎…
93.1萬字8 35840 -
完結439 章

敬我余生不悲歡
凌墨言愛著冷冽,從五歲開始,足足愛了二十年。冷冽恨著凌墨言,恨她暗中搗鬼趕走自己此生摯愛,恨她施展手腕逼得他不得不娶她。這場婚姻困住了冷冽,同時也成了凌墨言精致的牢籠。所有人肆意踐踏她的自尊的時候,尚未成形的孩子從她的身體里一點一點流掉的時候,冷冽始終冷眼旁觀嘴邊掛著殘忍的笑。“冷冽,我累了,我們離婚吧。”“離婚?別做夢了凌墨言,地獄生活才剛剛開始!”
80.2萬字8 2518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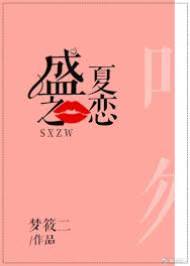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7.92 9024 -
完結143 章

透明的雪
盛衾從小性子溫和淡然,除了偷偷暗戀一個人多年以外。 做過最出格的事,莫過於在聖誕節的雪夜表白,將多年的喜歡宣之於口。 這次表白距離上次見宴槨歧已經有兩年多。 男人一頭烏黑的發變成了紅色,看上去更加玩世不恭。 他被一群人圍在中央,衆星捧月,人聲鼎沸中看向她,神色淡漠到似乎兩人並不相識,雪落在他的發頂格外惹眼。 等盛衾捧着那顆搖搖欲墜的心,用僅剩的勇氣把話講完。 四周幾乎靜謐無聲,唯獨剩下冷冽的空氣在她周身徘徊,雪花被風吹的搖晃,暖黃色的路燈下更顯淒涼狼狽。 宴槨歧懶散攜着倦意的聲音輕飄響起。 “抱歉,最近沒什麼興致。” 那一刻,盛衾希望雪是透明的,飛舞的雪花只是一場夢,她還沒有越線。 —— 再次重逢時,盛衾正在進行人生中第二件出格的事情。 作爲紀錄片調研員觀測龍捲風。 無人區裏,宴槨歧代表救援隊從天而降。 男人距離她上次表白失敗並無變化,依舊高高在上擁有上位者的姿態。 盛衾壓抑着心底不該有的念頭,儘量與其保持距離。 直到某次醉酒後的清晨。 她在二樓拐彎處撞見他,被逼到角落。 宴槨歧垂眸盯她,淺棕色眸底戲謔的笑意愈沉,漫不經心問。 “還喜歡我?” “?” “昨晚你一直纏着我。” 盛衾完全沒有這段記憶,呆滯地盯着他。 宴槨歧指節碰了下鼻子,眉梢輕挑,又說。“還趁我不備,親了我一下。” —— 雖不知真假,但經過上次醉酒後的教訓,盛衾怕某些人誤會她別有居心,癡心不改,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他卻步步緊逼。 有天被忽視後。 宴槨歧懶散地靠着車門,睨她:“看見了,不知道叫人?” “我覺得,我們不是可以隨便閒聊的關係。” 片刻後,盛衾聽見聲低笑,還有句不痛不癢的問話。 “那我們是什麼關係?” 盛衾屏着呼吸,裝作無事發生從他面前經過。 兩秒後,手腕毫無防備地被扯住。 某個混球勾着脣,吊兒郎當如同玩笑般說。 “之前算我不識好歹,再給個機會?”
33.8萬字8 1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