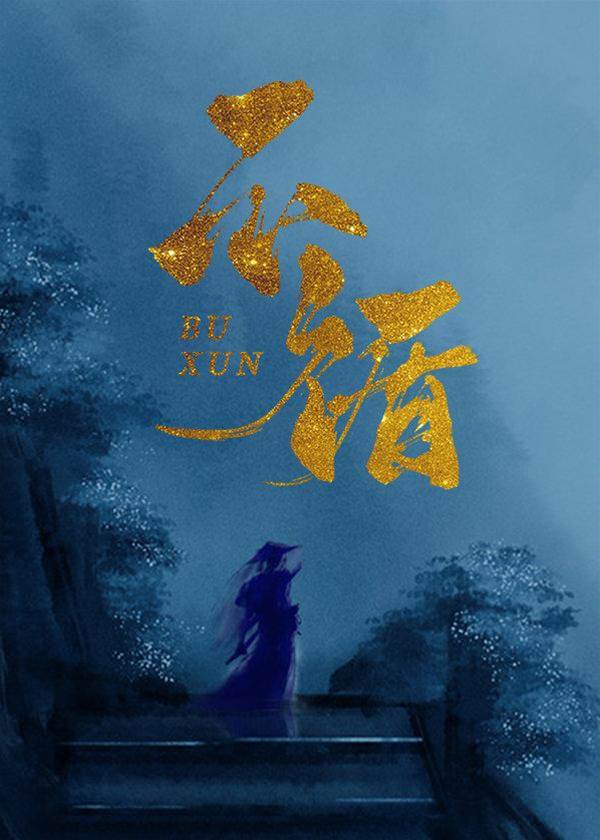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洞房前還有遺言嗎》 第三十七章 世子,你缺丫鬟嗎
不等卿如是走過來, 他先迎了過去。
月隴西回味著方才問的話, 想明白說了什麼之后, 答道,“我不是因為不愿意和你站在一邊才沒告訴你這樁差事,我也是剛得到的消息。我明白, 你想參與編修作,可是國學府明文規定不招收子, 我也是告訴過你的。”
“原本我想著可以跟著父親來參與這樁差事, 且那時不知道這差事里還有修復作這一條, 所以才跟你妥協了。但現在國學府請來了月世德,明擺著這樁差事不全歸我父親管, 屆時我想手還得看你們長老的臉。”
說至此,卿如是頓了頓,語氣不屑地嗤道,“我當那些流言真的是謠傳, 原來陛下不過是換了個法子想將崇文的書銷……”
的話沒說完,被月隴西捂住了。抬眸看見月隴西神嚴肅,恍然明白此或許隔墻有耳,便也閉不再說。
他卻沒有要松開的意思。
漸漸地, 他眉頭輕舒, 眸里浮上些許笑意。的又溫暖,的鼻息拂過他的手背, 淡淡地,唯有靜謐無聲、無人驚擾的此刻方能得到。
卿如是抿了抿, 有點別扭,拉開他的手。而后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想找回自己方被打斷的語言。
“跟我進屋來說。”月隴西引著往房間里走。
斟給兩人倒茶,而后就站在月隴西后不了。
月隴西看了斟一眼,后者沒明白。
“斟,外邊風大,有些冷,去把門關上。”月隴西吩咐。
斟狐疑地問,“世子,你方才起來的時候不還說熱嗎?”
“……”月隴西淡然道,“你先出去。沒重要的事,不要進來打擾我們談話。”
Advertisement
斟這才明白剛剛那一眼是何意。麻溜地滾了,走之前還順便帶上門。
“他好像對我沒什麼敵意了。”卿如是覷了眼門,兀自慢悠悠坐在茶桌邊,“從前不是我說一句他懟一句的嗎?現下乖巧了許多,還曉得給我倒茶。”
月隴西與對坐,“前幾日我說教過他了,以后不會再對你不敬。”
“哦,無礙,他那樣還蠻好玩的,不過多謝你了。”卿如是撐著下顎,打量他的房間,“住得不錯……你缺隨侍的丫鬟嗎?”
“不缺。我邊從來不用丫鬟。”月隴西回完,笑了笑,“怎麼,你要送我一個不?”
卿如是搖頭,鄭重地道,“你看我怎麼樣?我端茶遞水、鋪床疊被都賊厲害,要不要考慮一下,收我做你一個月丫鬟?”
“……”月隴西一怔,懵了。
向來最喜歡出其不意,回回讓人招架不住,但實在不知道這般的出其不意,究竟是讓誰撿了便宜。
“修復作的事復雜,我爹多半不會要我跟他來國學府摻和。且選拔人才這塊不還是你們月家首要管著的嗎?倘若你們徇私,凈撿著選那些毫不懂崇文先生所思所想的人進國學府……和助紂為有什麼區別?”
卿如是直言道,“我時讀崇文先生的書,時常慨世間怎會有擁有如此新穎想法的人,所以,若是崇文先生的書不能流傳下去,折了這一代先賢,往后等人漸漸醒悟,明白他的思想過后,得有多憾多惋惜?你就給我個機會幫你們選選人,后面修復的事等以后再說。”
按理來說,月隴西應該拒絕,可他的心卻不允許。
這種便宜只能他撿。獨的機會是卿如是自己送上門來的,這回可不能怪怨他無賴纏人。
Advertisement
月隴西挑起眉,角微翹,“好啊,我同意啊。但你要如何跟你爹娘說?二老怕是不會同意。”他端起茶杯,借著抿茶斂住眸中的笑意。
卿如是果然已經想好了對策,“那還不簡單,我就和我爹說,你看中我與崇文先生有著莫名相近的覺悟,專程請我去幫忙選拔扈沽才俊國學府。當然了,我不會告訴他我給你做丫鬟的,但那些端茶遞水的事我肯定會做,就當是還你人。”
月隴西放下茶盞,角的弧度似笑非笑,“好,那我們一言為定。你打算何時住過來?我給你在我院子里安排一間房。”
卿如是思忖了下,先問道,“你們什麼時候正式開始選?”
月隴西:“后日開始。倘若所料不錯,應該是以文會的方式。也就是采滄畔一貫用的斗文。”
卿如是點頭,“這法子公平。那我明日就來,今日要先回去和爹娘說一聲,順便收拾些裳。”
“裳就不用收拾了,一個月罷了,搬來搬去地麻煩。”月隴西笑道,“我的侍衛都是有補的,丫鬟自然也不例外。我給你買。”
怕拒絕,月隴西又補了一句,“月家不缺這點錢。你來當丫鬟,不論是什麼理由,月銀還是要照發的。”
本想說不用,聽及此,卿如是便隨他了。
兩人說定后,卿如是心里的擔憂消散了些,這麼看來月隴西和月氏家族的那些人不是一路貨。跟月隴西告辭,后者卻堅持要送出府。
來的時候還擔心沒人管,不想走到門口將那枚玉石亮出來就有小廝上趕著帶路。
想到玉石,卿如是反應過來,忙從荷包里取出,遞過去,“反正我都要住進來了,不必再用這個進府。你拿回去罷。”
Advertisement
月隴西垂眸掃了一眼,抿思考了須臾,道,“留著,以后還有許多用。”
“什麼用?”卿如是挲著玉石,怪嫌棄地說,“難看的一塊石頭,你還在上面刻名字,不能換塊好看點的刻嗎?”
“……”日常被嫌棄,月隴西低頭一笑,眉尾微揚,“我好看就可以了,不必講究它。它的用很多,以后就知道。你收好了,莫要弄丟。”
卿如是滿不在意地收回荷包里,回味他方才的話,又心生擔憂,“如果弄丟了的話,怎麼辦?”
說話間,兩人已走至府門口,斜方長廊里走來一人,步履蹣跚,速度極慢。來者看見兩人,微訝異片刻,兩人自然也看清了他,神各異。
月隴西來不及回答卿如是的話,先迎上去施禮喚了聲,“長老。”
月世德微微點頭,看向一旁默然看著別并不打算與自己見禮的小輩卿如是,含著淡笑,語調無不譏諷不識禮數,“小姑娘傲氣得很吶。”
卿如是睨著他,“下午在書齋的時候,您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不等月世德再自持份說什麼,月隴西擋在前,話道,“長老是要出府?”
“……隨意轉轉。”月世德的目從卿如是的上挪開,“隴西,今晚沒什麼事的話來我這里,我有事代你,是關于你提到的那個蕭殷的。”
卿如是微凝神看他一眼,收眼后忍不住心中揣測著。這麼快,月隴西就把蕭殷介紹給了月氏長老這等人?
“好。我先送卿姑娘出府。”月隴西與他告退,稍側眸示意卿如是跟著他走。
待走出月世德的視線,卿如是正打算一吐為快罵上兩句。
然則,還沒開口,旁這位月氏子弟先一步笑說道,“族中不曾出世又上了些年紀的人大多都虛偽得,沒見過些世面,卻總喜歡端著架子。你罪了。”
卿如是:“???”這突如其來的同一繩上的螞蚱是怎麼回事?
他在說什麼?為月氏得意子弟,他竟然能跟自己說出這種話?
這話直接把卿如是說懵了,沒口的臟字盡數憋了回去。
不是,怎麼就忽然罪了?
卿如是稀里糊涂地想了片刻,最后只能回道,“哦……還好。”
月隴西笑地側眸去瞧。擰著眉頭苦苦思索的模樣,和當年別無二致。
年初識滋味,那時候,他最喜歡的就是看著聽自己講解完月家宗親關系后不明所以,只好咬著筆頭苦苦思索的樣子。
如今依舊,他依舊很喜歡。
卿如是是騎馬來的,去時月隴西吩咐人給牽馬,讓乘著他的馬車回去,免得天黑了騎馬危險。
到卿府時天黑得只剩下幾點星子在,門口的燈籠也點上了,映照著一個人的面龐。
他筆地站在那里,對門口的侍衛說著什麼,并遞去一張類似于名帖的東西。
卿如是走過來瞧了一眼,疑地“嗯”了一聲。
果真是一張名帖。
蕭殷聽見的聲音時子似乎僵了下,抬眸看向,畢恭畢敬,低聲喚,“卿姑娘安好。”
“小姐回來了?”侍衛笑道,“老爺夫人正等著您呢。”
卿如是“哦”了聲,往府中走去,走了幾步又轉過來看向門口訥然看著,等說話的蕭殷。
挑眉問,“你來我府上做什麼?”
蕭殷淡笑了下,恭敬回道,“替國學府的諸位學士給卿大人送帖子,并講解一二。明日卿大人須得住進國學府去了。有些事宜都寫在帖子上的,需要事先悉。”
聽完,卿如是恍然,又想起剛剛在國學府時月世德也提到了蕭殷,不彎了彎角,卻不像是發自心的笑,挑著眉頭隨口說了句,“蕭殷,你爬得快啊。”
無心之言,卻因語調上揚,聽著就像是譏諷。
蕭殷愣住了,半晌沒有說話。
卿如是示意侍衛放他進去,他就跟在卿如是的后走著,保持適當的距離。
快要到正廳的時候,他忽然輕聲問了句,“卿姑娘……現在是把蕭殷當敵人來看了嗎?”
“嗯?”卿如是在門口停下腳步,轉過來看他。
但似乎,蕭殷并不是要個答案,見卿如是駐足,他垂著眸,輕道,“我的心口,真的有條疤。不曾騙你。”
猜你喜歡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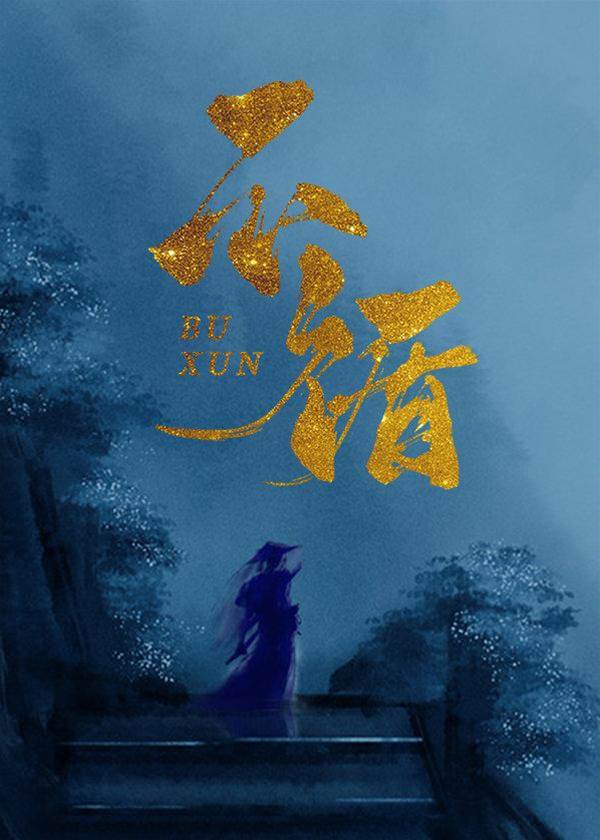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216 章

有嬌來
前世,定遠侯府滿門含冤入獄,身嬌體貴的宋五姑娘在被賣入勾欄紅院的前一晚,得那光風霽月的江世子相助,養於別院一年,只可惜宋五姑娘久病難醫,死在了求助江世子的路上。 【女主篇】 重生後的宋晏寧只想兩件事:一是怎麼保全侯府,二是怎麼拉攏江晝。 傳聞江世子不喜嬌氣的女子,被笑稱爲京都第一嬌的宋晏寧收斂脾氣,每天往跟前湊一點點,極力展現自己生活簡約質樸。 一日,宋晏寧對那清冷如霜雪的男子道:往日都是輕裝簡行,什麼茶葉點心都不曾備,可否跟大人討點茶葉? 後來,江晝意外看到:馬車裏擺着黃花梨造的軟塌,價值千金的白狐毛墊不要錢似兒的鋪在地上,寸錦寸金的雲錦做了幾個小毯被隨意的堆在後頭置物的箱子上...... 宋晏寧:...... 剛立完人設卻馬上被拆穿可如何是好? 清荷宴,宋晏寧醉酒拉住江晝,淚眼朦朧,帶着哽咽的顫意道:我信大人是爲國爲百姓正人的君子......,只想抓住幫助侯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晝聞言眼底幽深,又些逾矩的用錦帕給人拭淚,看着姑娘因低頭而漏出的纖白脖頸,心裏卻比誰都清楚,他對她可稱不上君子。 世人都道江晝清風霽月,清冷剋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縱容和徐徐圖之......
34.9萬字8.18 10522 -
完結144 章

與君同
朔康五年,齊皇室式微,諸侯四起。 爲籠絡權傾朝野的大司空藺稷,天子接回遠在封地的胞姐隋棠長公主,賜婚下降。 大婚當日,隋棠獨守空房。 直到七日後,月上中天時分才迎來新郎。卻被他一把捏起下顎,將藏於牙中的毒藥摳了出來。 彼時隋棠因在婚儀路上被撞,雙目暫且失明,正惶惶不安時,昏暗中卻聞男人道,“今日天色已晚,先歇下吧。” 這夜隋棠做了個夢。 夢中她看見自己,難產誕下一子,後不到兩炷香的時辰,便毒發身死。 死前一刻,她抓着藺稷的手,平靜道,“不必喚醫官,不必累旁人,無人害孤。是皇弟,曾讓太醫令鑿空了孤半顆牙齒,在你我二人大婚之日將一枚毒藥埋入其間,用來毒死你。” “非孤仁心下不了手,實乃天要留你。送親儀仗在銅駝大街爲賊人驚馬,孤被撞於轎輦瘀血堵腦,致雙目失明,至今難尋機會。所以,司空府數年,原都無人害孤,是孤自備之毒,漸入五臟。” “大齊氣數盡,孤認輸,君自取之。” 她緩了緩,似還有話要說,譬如她幫扶的皇弟,她家搖搖欲墜的江山,她才生下的孩子……然到底再未吐出一個字。 所有念想化作一聲嘆息,來生不要再見了。 隋棠在大汗淋漓中醒來,捂着餘痛未止的牙口,百感交集。不知該爲毒藥被除去而慶幸,還是該爲毒藥被發現而害怕…… 卻覺身後一隻寬厚手掌撫上自己背脊。 男人嗓音暗啞,“別怕,臣明日便傳醫官來府中,給殿下治眼睛!” * 藺稷攏緊榻上人,他記得前世。 前世,隋棠死後,他收拾她遺物。 被常年監控的長公主寢屋中,幾乎沒有完全屬於她自己的東西。他整理了很久,纔在一方妝奩最底處,尋到一份她的手書。 久病的盲眼婦人,筆跡歪扭凌亂。 此生三恨: 一恨生如浮萍,半世飄零久; 二恨手足聚首,卻做了他手中棋; 三恨雙目失明,從未見過我郎君。 世人道,藺氏三郎,霸道專權,欺主竊國。 但他是第一個待我好的人,我想看一看他。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
37萬字8 12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