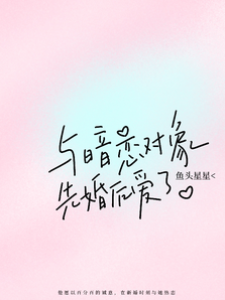《王牌特戰之軍少追妻》 第一章
墨上筠擰服的作一頓。
記得每個人選的位置。
丁鏡為了離的地面遠點兒,特地選的樹上,再在上面的樹杈上蓋上一層塑料,勉強可以抵擋一下雨水的侵。
以墨上筠斜上的角度來看,的位置非常明顯。
X特戰隊的三位學員,都分別坐在三棵樹下,呈三角形的組合,所以一目了然。
剩下的,就只有在右手邊的傅哲了。
嘆了口氣,墨上筠從地上站起。
袖、擺以及子,都在往下滴水,眼下狀態跟在水里撈出來似的,土地松,在雨水的浸潤下,一腳下去滿是泥濘。
剛睡醒的墨上筠連多走一步都覺得費勁。
但是,這樣的地形,也能讓墨上筠順利分辨出傅哲的腳印,在短時間迅速找到傅哲離開的方向,走出一段距離后,拿出防水手電,但猶豫了一下后,始終沒有打開。
剩下的電池不多了,省著點用吧。
樹上。
一直閉眼睡覺的丁鏡,倏地掀了掀眼瞼。
偏了下頭,在黑暗的叢林里,可見墨上筠的影。
扯了扯角,丁鏡將視線收了回去。
在滿是泥濘的地面走出很長一段路,墨上筠才在一視野比較寬闊的地方見到傅哲。
這里是一植被較的斜坡,往下沒多遠植被茂一些,但再往下就是萬丈高淵,正前方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產,因夜太暗墨上筠看不清晰,可前方空曠遼闊的空間,忽然從空中斷裂的懸崖廓,對面遙遠的山脈,都能看個大致模樣來。
還有在兩高山峭壁之間的河流。
覺近,實則遠,聽著洪流的聲音,像是遙遠之傳來的。
傅哲就坐在斜坡上,抬頭看著對面的山脈,中間洶涌的河流,或許還看著這漆黑卻寬廣無際的夜。
Advertisement
在這種地形里,沒有任務在,墨上筠沒有放輕腳步,也沒做任何遮掩。
一走近,傅哲就聽到樹葉撥的聲音,以及從泥濘地面行的聲響。
不知是誰,傅哲下意識地轉過,左手一把抓住就近的石頭,以做好防準備。
下一刻,他聽到墨上筠冷冷清清的聲音,“跑這兒來做什麼?”
傅哲一怔。
意料之外的人,讓他一時間沒回過神,半響,直至墨上筠慢慢撥開樹枝,一路走到視野來,他才緩過神來。
“你……”傅哲驚訝出聲,“怎麼找到這里來了?”
“出來散散步。”
墨上筠懶洋洋地說著。
的形靈活,轉眼便落下來,在傅哲側停下。
斜了傅哲一眼,將外套的袖往上一拉,然后隨意地在傅哲旁邊坐下來。
距離不過二十來厘米的距離,傅哲忽然就有些張,一顆心惴惴不安的,不知該往哪兒安放才好。
墨上筠道:“下次出來散心,要提前跟組長說一聲。”
“對不起。”
傅哲非常慚愧地道歉。
他只是心里裝著事,晚上睡不著覺,所以才隨便跑跑,后來找見這里打算回去,可一看到那條擋住他們去路的河流,一時之間就走不道了。
但,他在一個集里,忘了跟組長稟報就離開,確實是他做得不對。
“手怎麼樣了?”墨上筠問。
猶豫了一下,傅哲將手稍稍往下移了移,說:“好很多了。”
眸微微一,墨上筠偏頭看他,忽然問:“我們認識的時間有幾個月了吧?”
“啊?”傅哲不知所措地點頭,“嗯。”
“被分配到一組的況,也有幾次了?”
“嗯。”
墨上筠笑了一下,繼而又問:“那你覺得我像能被你糊弄過去的傻子嗎?”
Advertisement
“……啊,抱歉。”
心思被破的傅哲,匆匆忙忙說著,剛一低下頭去,臉頰就止不住地發燙。
他只能慶幸現在是晚上,墨上筠看不到他的表和臉。
有一種說不出的窘迫。
墨上筠早猜到他的心思,但他還是死撐著不說——這一意識,讓傅哲尷尬得很。
他一直覺得自己在團隊里是不起眼的。
無論再哪個團隊里,都是。
就算是在五月的訓練里,他當時因為會做飯而被學員“支持”,為“搶手”的存在,他也不覺得自己有多重要。
GS9的學員早就學會關心邊最容易被忽略的戰友,盡管很多時候,他們經常會忽略那些存在不強的戰友,但事過后他們也會想辦法來彌補。
都是一群心地善良、心的人。
這也是他在早就想放棄的時候,一直堅持到現在的原因。
可是,就算他不起眼,就算他能力不行,他也不想讓自己拖后——這也不是他能心安理得拖后的理由。
他每次換藥都小心翼翼的,為的就是不讓他們發現、擔心,可沒想到,傷勢依舊沒能瞞過墨上筠的眼睛。
墨上筠說:“手給我看看。”
傅哲愣了愣,有點猶豫。
墨上筠偏頭,定定地看著他。
黑暗里看不到的眼睛,但卻能覺到眼睛里的力量,注視著自己,帶有讓人并不反的力。
沒有催促他,也沒再說話勸說,而是就這麼看著他。
鬼使神差的,傅哲將自己包得跟個粽子似的的右手出來,慢慢遞到墨上筠跟前。
墨上筠拿起一直抓著的手電筒,打開了手電筒的開,在突如其來的線里,右手的況一目了然,繃帶一圈圈地纏繞,但全部,因逞強背包前進,中間不可避免會抓到一些東西,所以繃帶也是臟兮兮的,滿是泥濘。
Advertisement
看了傅哲一眼,墨上筠將他的繃帶給松開,然后一圈圈地繞出來,到最后幾層的時候,膿浸繃帶的痕跡非常明顯。
直至最后一圈松開,手背的傷口頓時映眼簾。
蛇咬的正好是手背中間部分,此刻半邊手背都腫了起來,傷口部位因化膿而擴散,又一圈白的,中間部分是,至今沒有愈合,傷口邊緣是鮮紅的,紅腫出一片,看起來慘不忍睹。
“傷口染,”墨上筠擰眉說著,然后問,“現在有發燒癥狀嗎?”
傅哲道:“暫時還沒有。”
將繃帶遞還給他,墨上筠說:“你需要接治療。”
“……嗯。”
傅哲輕輕應聲,低頭給自己的手纏著繃帶。
墨上筠將手電筒一關,視野忽然暗下來,抬眼看著前方,“想退出嗎?”
稍作猶豫,傅哲說:“正在想。”
墨上筠沒說話。
傅哲便說:“我聽說,丁鏡今天去探路時,發現一可以過那條河的地方,有點風險。”
“嗯。”
“他們當時在議論,如果我們隊伍里沒有傷員的話,其實是可以冒這個險的。那樣我們就可以節省大半天的時間,不用走得那麼辛苦。”
“……”
“可我當時就想,你應該不會同意的。”傅哲將繃帶給纏好,側過頭看向墨上筠,繼續說,“你會考慮更穩妥的方法。”
墨上筠輕笑,有些玩味地說:“是嗎?”
傅哲也笑了笑,“我們私下里都說,你看起來最不好相,但實際上是最好相的。”
“哦?”
“你一個人做事會有點……嗯,有點瘋狂。”傅哲說,“但組隊的時候,永遠會顧及到我們。”
墨上筠停頓了下,視野里映著這遼闊的自然景觀和夜,可如此漆黑的夜晚,的眼里依舊有的亮。
“墨教……不好意思,我覺得是可以這麼你的。可能是因為你是長,以前帶過兵,又當過教,所以跟你在一組的時候,總覺得不是在跟學員在一起,而是跟教在一起。”傅哲說到這兒,有些不好意思,可停頓片刻后,又鼓起勇氣補充道,“安心的。”
“謝謝。”
墨上筠輕聲說。
傅哲低下頭,忽然用袖子抹了把眼睛,他說:“我不想拖后。”
“我知道。”
“信號彈我一直帶在上,我剛剛在想,離出發之前還有兩個小時,我可以在這段時間里,任何一個時間,拉開它。”
“嗯。”
傅哲愧疚地說:“但我不想走,不想就這樣走了。對不起,我還是想留下來,留在GS9。”
他一直在膽怯。
想不拖后,就此解,這樣墨上筠他們就可以冒險了;可他又想著就這樣吧,接墨上筠的照顧,努力撐一撐,爭取留下來。
愧疚著,膽怯著,極其矛盾。
坐在這里的時候,他無數次地將信號彈掏出來,想要發,結束自己這一段特種部隊的旅程。
但是,他每每手的時候,蠢蠢的自私,又讓他停了下來。
他告訴自己,沒必要非得這樣,既然墨上筠決定了,他就裝作什麼不知道,不知道那一條捷徑,不知道自己是累贅……裝作一無所知地走下去。
這是一個團隊,他拖累戰友應該覺得恥,但這并非罪無可赦。
于是,他又無數次地安自己。
在墨上筠來之前的一分鐘,他剛剛被那份自私的心打敗,不知廉恥地將信號彈放回了兜里。
他跟墨上筠的對話,讓他為那個自私懦弱的自己而覺得恥辱,他不得不向墨上筠主坦白。
他將這番話說出口,心張而忐忑,忽上忽下的,一下跳到嗓子眼,一下又沉到心底最低,攪得他不得安寧。
——墨上筠會怎麼想呢?
他想到很多不好的答案。
可是,在短短幾秒的等待里,他就聽到墨上筠贊同地說:“這是個很不錯的地方,它值得你這麼想。”
不是諷刺、貶低,而是贊同。
窘迫到極致傅哲,忽然抬起頭來,不可思議地看著墨上筠,就如同看到一抹曙,閃耀到驅散他心里的邪惡和暗。
“想留下來是正常的,這不該是一件讓你覺得愧疚的事。”墨上筠說,“你是一個軍人,為一個軍人,堅持不懈、勇往直前,是值得稱贊、肯定的品德。而且,我們多走一段路,你們也在走同樣的路,跟我們不一樣的是,你們一個著傷,一個生著病,承的要比我們還要多。”
“可我——”想拖累你們啊。
“為一個集,我們能夠不丟下一個戰友,就是我們的榮。”歪了歪頭,墨上筠揚了一下眉頭,繼續道,“你不要不能走捷徑而有負罪。或許你和病著的不在,我們確實會選擇那條危險的捷徑,但你們在的話,我們理所當然會選擇穩妥的方式。換言之,這件事并不存在選擇,而是一件最合理的發展的事,它順理章,中間不該有任何停頓,你能懂嗎?”
傅哲有點懵,似懂非懂。
“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一起抵達重點,這將是我們所有人的榮耀。”
墨上筠道:“傷和生病,不可避免,你們運氣不好,但這事會發生在我們任何一個人上,倘若我因為傷或生病而拖累團隊,我確實會覺得愧疚,但這并不代表我能接他們放棄我、拋棄我。如果這個團隊里,有任何一個人這麼想,那這個團隊就不該是一個軍人的團隊。你知道,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在戰場上丟下一個傷的同伴,只要他尚有一生存的希。”
“……”
傅哲有些恍然。
“我一直覺得,特種部隊的考核,不該只考慮學員的能力,還應該考驗在,因為我們今后會向留下來的戰友付自己的生命。”
“嗯。”
傅哲忽然覺得鼻子酸酸的。
“話說開了,”墨上筠笑了笑,繼續道,“如果你愿意留下來,覺得自己還可以堅持,我們會盡量幫你克服,幫你堅持下去。”
“謝謝。”傅哲舒出一口氣,他定定地看著側墨上筠的影,終于不再張而慌,而是一字一頓地強調道,“我想再堅持一下。”
“好。”
墨上筠點點頭。
下一刻,晃了晃手電筒,從地上站起,“先回去吧,這時候趕過去,還可以再休息會兒。”
朝傅哲出手。
“嗯。”
傅哲用力點頭,連聲音都比先前大了些。
抓住墨上筠的手,傅哲從地上站起。
可那明顯細而纖細的手指,讓傅哲站定的那一瞬瞬間松開,耳有些泛紅。
因為墨上筠的那一番話過于震撼,他甚至有些忘了墨上筠的別。
那剛剛那個時候,他覺得墨上筠跟自己是一樣的,不存在任何區別——
墨上筠說,我們。
我們都是軍人。
同一個份。
墨上筠倒是沒察覺出異常,抬就往坡上走,而頗為心虛的傅哲則是隨在后。
可是,他們沒有兩步,就聽到這叢林里突兀的聲音,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空中炸開。
刺耳,鮮明,嘹亮。
那是信號彈的聲音。
------題外話------
都說過四千字保底了,最近都是兩章合并一章啊,更新量跟平時沒啥區別。
463、考核落幕【08】墨墨發火
猜你喜歡
-
完結2307 章

獨家蜜婚:陸少的心尖寵妻
第一次相親,就被他拐進民政局連夜扯了證,婚後才發現他竟然是堂堂的陸家長孫,全國數一數二的陸氏集團的首席總裁。她隻想找個平凡男人過平凡日子,冇想要嫁個身世駭人的大總裁啊!“夫人,既然已經上了賊船,那就冇法再下去了,還是老老實實跟我一起努力造人吧。”麵對她的懊喪,他笑著將她摟入懷中,深深吻住。她情不自禁地淪陷在他的柔情中。原以為婚姻不過是一場豪賭,卻不料這場豪賭如此暖人心脾,讓她甘之如飴。
407.3萬字8 673126 -
連載52 章

超甜!墨爺的小祖宗又美又颯
【馬甲+團寵+微玄幻+古武+異世】夏煙重活一世,不想努力了,只想做個寵老公,愛老公,天天在老公懷里嚶嚶嚶的小嬌嬌。但在所有人眼里,夏煙不學無術,一無事成。廢柴?草包?網上罵聲一片,“墨爺有錢有顏配你,簡直是暴殄天物。”當即,夏煙甩出她的重重…
9.4萬字8.18 8213 -
完結213 章
生崽痛哭:豪門老男人低聲輕哄
【年齡差11歲+霸總+孤女+甜寵+無底線的疼愛+越寵越作的小可愛】 外界傳言,華都第一豪門世家蘇墨卿喜歡男人,只因他三十歲不曾有過一段感情,連身邊的助理秘書都是男的。 直到某天蘇墨卿堂而皇之的抱著一個女孩來到了公司。從此以后,蘇墨卿墮落凡塵。可以蹲下為她穿鞋,可以抱著她喂她吃飯,就連睡覺也要給她催眠曲。 白遲遲在酒吧誤喝了一杯酒,稀里糊涂找了個順眼的男人一夜春宵。 一個月以后—— 醫生:你懷孕了。 白遲遲:風太大,你說什麼沒有聽見。 醫生:你懷孕了! 蘇墨卿損友發現最近好友怎麼都叫不出家門了,他們氣勢洶洶的找上門質問。 “蘇墨卿,你丫的躲家里干嘛呢?” 老男人蘇墨卿一手拿著切好的蘋果,一手拿著甜滋滋的車厘子追在白遲遲身后大喊,“祖宗!別跑,小心孩子!” 【19歲孩子氣濃郁的白遲遲×30歲爹系老公蘇墨卿】 注意事項:1.女主生完孩子會回去讀書。 2.不合理的安排為劇情服務。 3.絕對不虐,女主哭一聲,讓霸總出來打作者一頓。 4.無底線的寵愛,女主要什麼給什麼。 5.男主一見鐘情,感情加速發展。 無腦甜文,不甜砍我!
39.3萬字8 14199 -
完結803 章

煙視媚行
早知道邢錚是披著衣冠的禽獸,林湄一定不會自不量力去敲他的房門。那夜之後,她便落入他精心設計的陷阱中,被他啃得骨頭渣都不剩。
143.9萬字8.18 5961 -
連載810 章

禁止相親!薄總夜夜跪地求名分
【假斯文真敗類VS人間尤物黑蓮花,雙潔,甜寵,1V1,HE】應如願跟著媽媽進入薄家,成了最透明又最引人注意的應小姐。她沒有身份,上不得臺麵,是最物美價廉的聯姻工具。她太美貌,太弱勢,老老少少都如狼似虎地盯著她,用盡手段想占有她。為求自保,她主動招惹了群狼之首薄聿珩,喊了一夜的“聿哥”,天亮後以為錢貨兩訖,他能保她平安離開薄家。萬萬沒想到,男人夜夜進入她房間,拉開領帶捆住她:“妹妹,酬勞是日結。”
94.7萬字8.18 6962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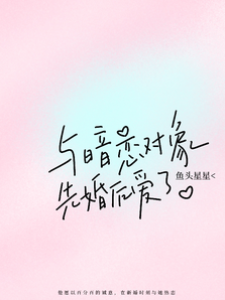
與暗戀對象先婚后愛了
【清冷美人×桀驁貴公子】江疏月性子寡淡,不喜歡與人打交道,就連父母也對她的淡漠感到無奈,時常指責。 對此她一直清楚,父母指責只是單純不喜歡她,喜歡的是那個在江家長大的養女,而不是她這個半路被接回來的親生女兒。 二十五歲那年,她和父母做了場交易——答應聯姻,條件是:永遠不要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 _ 聯姻對象是圈內赫赫有名的貴公子商寂,傳聞他性子桀驁,眼高于頂,是個看我不服就滾的主兒。 他與她是兩個世界的人,江疏月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討喜,這段婚姻,她接受相敬如賓。 兩人一拍即合,只談婚姻,不談感情。 要求只有一個:以后吵架再怎麼生氣,也不能提離婚。 _ 本以為是互不干擾領過證的同居床友。 只是后來一次吵架,素來冷淡的江疏月被氣得眼眶通紅,忍住情緒沒提離婚,只是一晚上沒理他。 深夜,江疏月背對著,離他遠遠的。 商寂主動湊過去,抱著她柔聲輕哄,給她抹眼淚,嗓音帶著懊悔:“別哭了,祖宗。” _ 他一直以為自己與妻子是家族聯姻的幸運兒,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書中找到一封情書,字跡娟秀,赫然寫著—— 【致不可能的你,今年是決定不喜歡你的第五年。】 立意:以經營婚姻之名好好相愛 【先婚后愛×雙潔×日久生情】
26.1萬字8 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