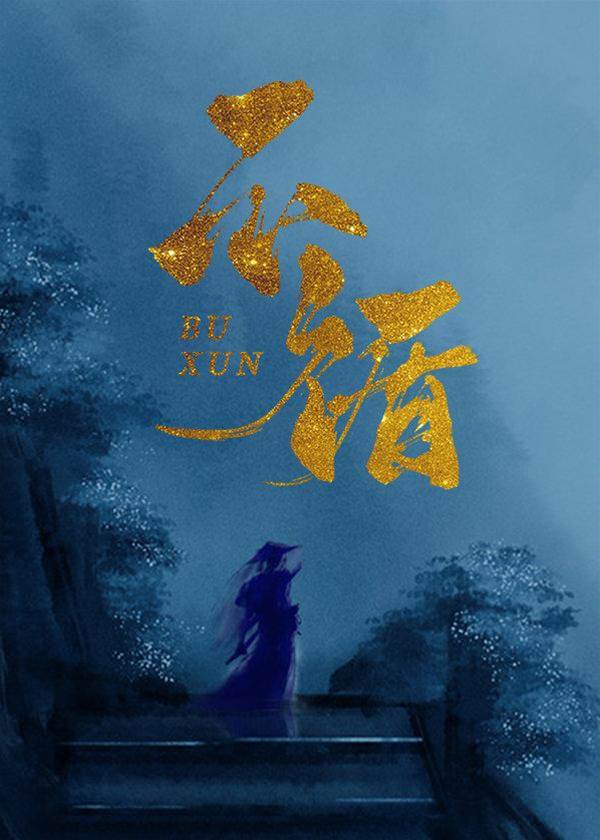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第80章 亦真亦幻
阿娘地倒下來, 蘇毓連忙跑過去,跪在邊,推推的;“阿娘, 阿娘……”
爹爹牽著他的玉驄馬站在不遠,手里拿著一把彎刀,刀在月下閃著冰涼的, 什麼東西順著刀淌下來,滴滴答答落在草叢里。
他推了好一會兒,阿娘不理他, 他仰起頭:“爹爹,阿娘睡著了麼?”
爹爹背對著月亮, 臉藏在黑暗中,看不真切。
他不說話, 從馬背上取下一個布囊,打開, 里面有兩樣東西, 一個小小的皮水囊,還有一塊掌大的生, 連著皮,在皎潔的月下, 像緞一樣,比月還白,比月還亮。
蘇毓約想到那是什麼,退后了一步:“這是什麼?”
爹爹蹲下, 像平時那樣輕輕地他的頂發:“這是阿銀的和,給你吃的。”
“那阿銀呢?阿銀在哪里?”蘇毓向四周張。
爹爹道:“傻孩子,阿銀殺了給你吃,自然沒了。”
蘇毓抿住,眼淚在眼眶里打轉:“我不吃,我不吃阿銀的。”
爹爹把和水囊仍舊包起來,搭在他肩上,然后握著他的肩膀,讓他轉過,指指前方黑黢黢的林:“穿過這片林子有個山坳,到了那里才有人家,可以給你東西吃,若是你不吃阿銀的,不喝它的,你就會死死。”
蘇毓眨了眨眼,一滴淚珠落了下來:“爹爹,我要回家。”
“你沒有家了。”男人道。
“叔伯嬸嬸,堂兄堂姐他們呢?”蘇毓忽閃了一下長睫,大眼睛里淚盈盈。
一片云飄過來,遮去了月亮,這下更看不清爹爹的臉了。
“那我……”蘇毓想了想道,“阿娘和我去外祖家……”
Advertisement
男人淡淡地一笑:“你外祖家也沒人了。”
怎麼會呢?蘇毓到困,阿娘說外祖父是什麼侯,他隨阿娘回過一次城,外祖家的宅子特別大,走也走不完,人比他家還多,有許多舅舅和舅母,還有許多表兄和表姐,怎麼會沒人呢?
男人聲道:“若是不信,你就去城看一看吧。”
他覺得爹爹今晚很古怪,心里越來越不安:“爹爹,我是在做夢麼?”
男人笑而不答,彎下腰了他的臉頰:“要探求大道,先要斷絕塵緣,你是應天命而生之人,長大后也會走上這條路,到時便懂了。”
他說完拉起他的手,把滿是污的彎刀塞進他手里,拍拍他的頭,直起,抱起他阿娘放到馬背上,阿娘歪倒下來,在玉驄馬雪白的皮上拖出長長一條深的印子。
爹爹把娘扶好,翻上馬,讓靠在自己懷里,一踢馬腹,便轉走了。
蘇毓趕忙追上去:“阿娘,爹爹,別扔下我……”
一邊跑,一邊用手背抹眼淚,阿娘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是他顧不得了,玉驄馬撒開四蹄疾奔,不一會兒便消失在了彎彎的山道上。
他追了很久,終于追不了,沿著原路走回去,坐在那塊林間空地上哭起來,不知哭了多久,困意慢慢籠罩上來,他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再次醒來,便又是在奔馳的馬車中,阿娘地摟著他。
周而復始,反反復復。
……
小頂在王老六的攤位上從清早蹲到黃昏,作伴的魚蝦陸陸續續被人買去了,還在。
駐足詢價的人倒是不,還有人把拿在手上掂了掂,但一聽要二十塊上品靈石,便把放回原,順便將王老六挖苦一番。
Advertisement
第二日,王老六學了個乖,讓兒子守著攤兒,自己揣著香爐去專賣古玩的鋪子,向店家兜售。
倒是有幾個店主人興趣,一問價錢,便即搖頭:“你這玩意兒,大小是個香爐,形制卻是煉丹爐的形制,不倫不類的,收進來也要融了重鑄,就值這幾斤的銅價,你賣二十塊上品靈石,但凡眼睛沒瞎都不會要的。五塊頂了天了。”
還有這個嫌太扁,那個挑太圓,這個說制式太老,那個又說不夠涵古,連耳朵上的小青鳥都被嫌棄長得像只,總之從頭到腳都是病。
王老六一家一家挨個兒問過去,果然沒人愿意出二十塊上品靈石,最后磨破了皮子,以八塊上品靈石的價賣給了一家賣香燭紙錢冥的鋪子。
一天下來,小頂已經沒了脾氣,擺正了自己的位置,雖然是青冥仙君親手鍛造的煉丹爐,第二任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連山君,但沒人認得,就是一只價值八塊靈石,長得像煉丹爐的香爐。
環顧了一下四周,在心中嘆了口氣,和香燭紙錢作伴,總好過埋在一堆魚蝦中間供人圍觀。
已經走丟好幾日了,也不知道師父有沒有音信。連那麼憊懶的五師兄和六師兄都找到魔域來了,師伯、師姐和師兄他們肯定急壞了,碧茶和李圓他們一定也很擔心。
更擔心暗中幫丁一對付的人,會對師父和其他同門不利。
一想到都是因為,便難得想哭。
要是在修煉上多上點心就好了,丁一修為比低了幾個境界,可對上他毫無招架之力,都是不夠勤勉的緣故。
師父總說怠惰,仗著會煉丹煉投機取巧,還真是說對了。
Advertisement
不過事已至此,再怎麼懊悔焦急都無濟于事,現在不能說話也不能,靈不能離開原,就和在九重天上第一次“醒來”的時候一模一樣。
那時候不會修煉,不懂心法,稀里糊涂過了很久,忽然有一天就能離開原,也能說話了。
仙君說這是修靈。
既然那時候能修出來,沒準現在也一樣。
眼下可是正經拜了師、修過仙的爐子,總比無點墨的時候強吧?
定了定神,開始回想先前學的門派心法。
多虧了師父每晚雷打不的傳音課,小頂最近背了十七八卷元嬰期適用的心法。
一邊默誦,一邊凝神定。現在是只爐子,自然沒了經脈,只能憑空存想,假裝從日月天地中汲取靈氣,引不存在的經脈,在其中運轉二十八個小周天,再運轉二十八個大周天。
不知是否是的錯覺,運完功后,的神思似乎清明了一些,視也比先前清晰了。
此時當是夜半,店主人已經將門扇闔了起來,店堂里空無一人,只有幾縷月從門板的隙里進來。
但卻能清楚地看見對面靠架子立著的一排紙人,其中有一個還只扎了一半,勾著紅,彎著眉眼,似在朝微笑。
小頂“后背”上莫名有些發涼,旋即想起自己是只爐子,不啞然失笑,怎麼也害怕起這些來了?
做了半年的活人,倒是越活越像人了。
小頂在心里嘆了口氣,不由自主地懷念起做人的覺來,雖不如當爐子省心,有許多苦惱,但生著,能到跑,能說能笑,有師長有朋友……
想到師長,不免又想起師父來,定睛一瞧,對面有個男紙人的眉與師父有幾分相似,隔壁那個下頦有點像,還有那個額頭差不多有師父那麼寬……
想著想著,有些犯困,慢慢沉了夢鄉。
半夢半醒之間,忽然覺得自己像是被一細線牽引著飛出了鋪子外。
越飛越快,月下的山河在眼底一閃而過,轉瞬之間似乎已飛了幾千幾萬里。
接著牽著的那線忽然猛地一拽,子一重,眼前一黑,便跌落了下來。
小頂丈二和尚不著頭腦,睜開眼睛一看,看見一些模糊而搖曳的火,耳邊有嘈雜的聲響,似乎有個人在哭哭啼啼。
就在這時,猛然發覺自己又有眼睛、手腳和了。
抬手了眼睛,忽覺哪里不對勁,借著火看了看手,發現眼前的分明是只孩的手。
胳膊、、、腦袋……整個人都了小孩,被人裝在一個藤編的背簍里背在背上,那人上有一悉的氣息,不由自主地口而出:“爹爹。”一出口聲音也是生生的。
男人腳步一頓:“醒了啊?再睡會兒,還沒到地方。”
“這是去哪兒啊?”小頂一邊問,一邊打量四周,只見他們在荒山野嶺中,又圓又大的月亮掛在山尖上。
他們一行人總有二三十個,都是村夫野佬的打扮,幾個人舉著火把,還有幾個人挑著酒壇子和竹飯籃。
米酒和燒的香氣飄過來,讓食指大——自從沒了人,已經幾天沒吃過東西了。
不遠,一個人發出一聲嗚咽,小頂不用人告訴,立即想起那是娘。
了一聲阿娘,又問了一遍去哪兒。
阿娘用袖子抹了把臉,噎噎的說不出話來。
旁邊有個持火把的年輕人笑道:“帶你上山耍呢,頂丫頭。”
娘一聽這話,突然慟哭起來,去扯他爹肩上竹簍的帶子:“不去了,我們不去了,錢還給族老,把小頂還給我!”
爹爹低了聲音,煩躁道:“發什麼瘋!回去!”
旁邊有兩個婦人一邊拽娘一邊勸:“嫂子,回去吧。”
阿娘瘦瘦一個人,不知哪里來的力氣,掙了他們,撲向男人,一邊捶打一邊罵:“你這沒心肝的,為了八塊靈石賣自己骨去嫁山神,才四歲呀!你這……”
“啪”的一聲脆響,阿娘的聲音戛然而止。
人捂著臉,慢慢蹲下來。
“我不是為了大郎?你不舍得,不舍得兒子怎麼辦?一輩子困在這山里?”爹嘶啞著嗓子道,“走!”
阿娘不再吭聲,一不地蹲在山道旁。
小頂從背簍里探出頭,蓋子一下下地打在頭上,阿娘越來越小,漸漸看不見了。
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里,為什麼自然而然地知道這是爹娘,什麼都不知道,但心口還是一一地痛,兩行眼淚滾落下來。
爹爹不再說話,只是背著默默走著,時而上坡,時而下坡,不知走了多久,他們終于停了下來。
眾人忙活起來,在地上鋪了席子,擺上香案,將香爐、紅燭、酒、燒豬頭、燒、瓜果等都擺好。
接著爹爹打開背簍,把小頂抱起來放在香案旁,了的發鬟:“小頂乖,爹爹和叔叔伯伯們有事走開一會兒,你坐在此地乖乖等爹爹回來。”
小頂一看這架勢便知他們在做什麼,但只是點點頭。
不一會兒,人走了,黑黢黢的林子里,只剩下一個人。
他們一離開,立即站起來,下外衫,把糕點、燒和瓜果抱起來挎著,拿起一個燭臺,憑著記憶往林子外走。
他們來時故意在林子里繞來繞去,生怕找到路回去,但現在的小頂不是四歲稚,這法子對不管用。
雖不知道這一晚會發生什麼,但明白,林子里一定有危險的東西,必須快點離開。
約莫走了一炷香的功夫,紅燭暈的邊緣,似乎趴伏著一團東西。
小心翼翼地走近幾步,舉起蠟燭一照,卻是個和差不多大的男,生得雕玉琢,雖閉著眼,也看得出他眼睛很長,眼梢微微上挑,又長又翹的睫覆在眼上,像兩把小扇子。
不知怎的,這孩子看著有幾分面善。
這孩子穿著一織錦裳,一看就是富貴人家的孩子,不知怎麼也孤一人跑到林子里來。
最詭異的是,他邊放著一把寒閃閃的彎刀,刀上還有跡。
小頂悄悄拿起彎刀放到旁邊,然后輕輕推了推他:“小孩,你醒醒。”
……
蘇毓又在做同一個夢。
顛簸的馬車里,阿娘摟著他。馬忽然長嘶一聲停下來,阿娘抱著他跳下車不停地跑。
他們藏在草叢里,阿娘讓他別出聲,他記住了,可是爹爹一喚他,他又忍不住答應。
阿娘倒下了,爹爹將他拋在林子里,騎著馬帶走了阿娘。
這夢不知做了幾千幾萬遍,就在他又一次蜷著子躺在林中空地上快要睡著的時候,忽然有人推了推他:“小孩,你醒醒。”
是個小姑娘甜甜的聲音,甜得像是歲除夜里吃的膠牙糖。
他睜開眼睛,發現眼前燭影搖曳。
他一個激靈坐起,卻見邊蹲著個小,穿一紅布裳,梳著雙鬟髻,圓圓的小臉在燭中像珍珠一樣微微發著,一雙微圓的大眼睛忽閃忽閃。
蘇毓微微一怔,隨即警覺地往旁邊挪了幾寸。
不等他發問,那先道:“你是誰?怎麼會在這里?”
“我是阿毓……”
“阿毓?是哪個毓?”又道。
蘇毓覺得問得古怪,不過還是彬彬有禮地答道:“家父說過,是鐘靈毓秀的毓。”
“啊!”吃驚道,“那你姓什麼?”
“蘇。”
“師……”咽了口口水,“你怎麼變這樣了?”
蘇毓皺起小小的眉頭:“什麼樣?”
“我是小頂,”指指自己翹翹的小鼻子,“你記得我嗎?”
蘇毓搖了搖頭。
小頂又問:“你生辰八字記得麼?”
蘇毓戒備地皺起眉:“你為何問我生辰八字?”莫非這小其實是妖怪?
小頂道:“那你就說六個字吧。”
蘇毓遲疑了一下,還是說了。
小頂張了張,半晌道:“你記得自己幾歲麼?”
蘇毓聲氣道:“五歲。”
猜你喜歡
-
完結48 章

心上撒野
1. 林瓷嫁給陸時溫兩年,夫妻同框次數寥寥無幾,淪為南城名媛圈的笑柄,然而她本人并不以為意,活得風生水起,這月飛巴黎,下月飛紐約,潮流奢侈品全部一網打盡,成為頂尖時尚買手。 外界流傳林瓷是以此掩蓋內心的痛楚,私下的她肯定天天以淚洗面,眾人皆猜測他們夫妻關系早已破裂,離婚是遲早的事兒。 好友問林瓷對此有什麼看法,她輕輕搖晃著酒杯,紅唇溢出一抹嫵媚的笑: “有個只管刷他的卡,還不用經常履行夫妻義務的工具人老公,我笑都來不及。” “離婚?隨便啊,小鮮肉弟弟難道不香嗎?” 陸時溫的財產哪怕分她十分之一,也足夠她紙醉金迷了,誰不渴望富婆的生活?可比現在自由開心多了。 2. 在陸時溫面前當了兩年多的無腦白蓮花,林瓷受夠了,主動將離婚協議甩給陸時溫,想搶占先機。 誰知,陸時溫將離婚協議書撕得粉碎,神情凜冽地看著她,一個字都沒有說。 后來,媒體曝出一則重磅緋聞,陸時溫在午夜將一神秘女子按在車上強吻,與林瓷的婚姻岌岌可危。 名媛圈都笑話林瓷綠得發光,哪知陸時溫親自出面澄清了緋聞—— “不過是我和夫人偶爾的小趣味罷了,讓大家見笑了。” 【高冷一時爽,事后火葬場】
15.9萬字8 19962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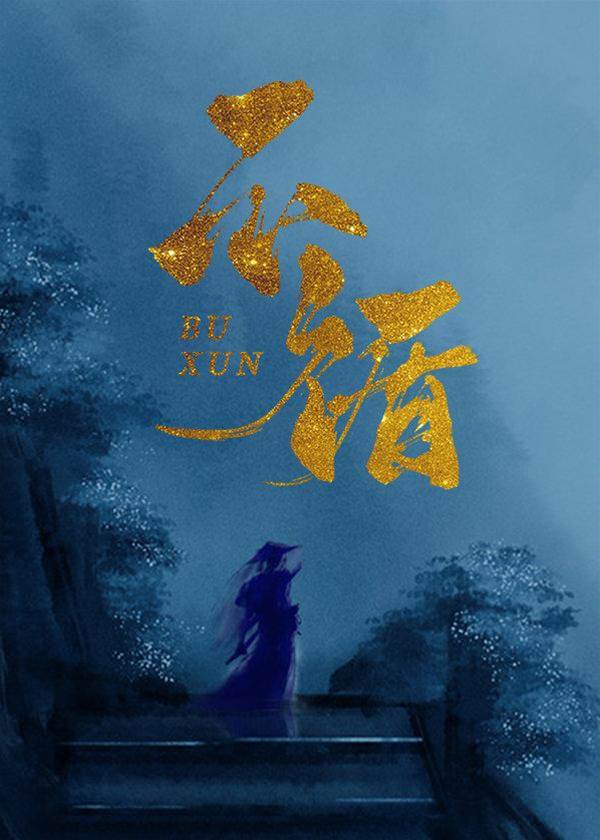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269 章

侯門夫妻重生后
白明霽及笄那年,晏家派媒人上門替世子晏長凌提親,同是武將之後,也算門當戶對,父母一口答應,她也滿意。 十七歲白明霽嫁入晏家,新婚當夜剛被掀開蓋頭,邊關便來了急報,晏長凌作爲少將,奉命出征。 一年後,傳回了死訊。 對於自己前世那位只曾見過一面,便慘死在邊關的夫君,白明霽對他的評價是:空有一身拳腳,白長了一顆腦袋。 重生歸來,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白明霽打算幫他一把,把陷害他的那位友人先解決了。 至於害死自己一家的姨母,她不急,她要鈍dao子割肉,她萬般籌謀,等啊等啊,卻等到了姨母跌入山崖屍骨無存的消息。 白明霽雙目躥火,“哪個混賬東西動的手?!” — 晏長凌十六歲時,便上了戰場,手中長矛飲血無數,二十歲又娶了名動京城的白大姑娘,人生美滿,從未想過自己會英年早逝。 枉死不甘,靈魂飄回到了府中,親眼看到自己的結髮妻子被人活活毒si。 重生歸來,他打算先履行身爲丈夫的責任,替她解決了姨母。 而自己的仇,他要慢慢來,查出當年真相,揪出那位出賣他的‘摯友’他一番運籌,還未行動,那人竟然先死了。 晏長凌眼冒金星,“誰sha的?” — 得知真相,兩人沉默相對,各自暗罵完對方後,雙雙失去了鬥志。 晏長凌:重生的意義在哪兒? 白明霽:重生的意義到底在哪兒? 既然都回來了,總不能再下去,晏長凌先建議,“要不先留個後?” 白明霽同意。 小劇場: 本以爲今生再也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他,直到半夜突然被踢下床,“你閨女哭了,去哄一下。” “你那好大兒,又把先生氣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二寫的一手好字,連他自己都不認識了,爲人父,你總得管管。” 晏長陵:曾經有一段清閒人生擺在面前,我沒珍惜...... “晏長陵!” “來啦——”
39.9萬字8.18 13511 -
完結74 章

嬌妾惹人
攝政王儲司寒權勢滔天,卻是個奸臣,不良於行,聽說他的府邸,用鮮血澆灌出了一片曼珠沙華。 宋知枝現在被人送給了儲司寒做禮物。 可她是個鈍的,不知道這個大魔王有多可怕。 【小劇場一】 侍寢第一天,宋知枝在被子裏拱成小小一團,甜甜喊,“夫君,快上床。” 然後從枕頭下拿出一本小人書塞進宋知枝手中,自己捧着臉,雙眸星亮,“今晚給我講三打白骨精行嗎?” 儲司寒:“……” 【小劇場二】 宮宴上,宋知枝喝了三杯米酒,衆目睽睽之下,抱着儲司寒的膀子不撒手,嘴巴一暼,“相公揹我,不揹我就賴在這了……” 儲司寒:“……” 【小劇場三】 新春冰嬉比賽,儲司寒沉着臉呵斥,“不許去,在觀衆席上觀看即可。” “我真的很想去玩,”宋知枝跑的像鳥一塊輕快,“晚上回來隨夫君罰。” 留下這句話,裙襬飛揚,輕盈的向一隻鳥雀飛走。 儲司寒:“……” 世人以爲儲司寒暴虐,宋知枝過的日子定然生不如死,宋知枝卻清楚,他也會給她講小人書,也會給她買零嘴。 會死死摁住棉被蓋住腿,背過去的臉眼眶微紅,“……別看” 會頂着寒風,騎一整夜的馬,鬢邊沾滿塵土,拽着她的衣袖哄,“別生我的氣……”
23.6萬字8 3682 -
完結111 章

春閨令
京城第一公子謝凌,出身名門,儀容儒雅,是朝中最年輕的宰輔。 昭寧三年,遵守祖輩婚約,迎娶江南第一世族秦家大小姐爲妻。 新婚當夜,看着妻子嬌若芙蓉,難掩姝色的容貌,謝凌心尖顫了顫。 婚後,二人舉案齊眉。 ** 秦謝兩家婚約乃是祖輩婚約,奈何長姐心裏早已有心上人。 百般權衡之下,妹妹秦若硬着頭皮嫁了過去。 謝家每一個人都對她很好,包括她那位權勢滔天,矜貴自持的“夫君”。 一朝身份被揭穿,秦若自知無顏見人,寫下一封和離書便走了。 和離書被呈到謝凌面前,男人氣笑了。 不久,他在江南水鄉找到那個將他耍得團團轉的姑娘,啞着聲音問:“若若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這是打算帶着我的孩子去哪兒?” #明媒正娶的夫人要跟我和離,怎麼辦# #先婚後愛,世族公子爲愛折腰#
46.8萬字8 1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