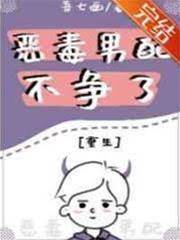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第44章
監察的人在反腐活開展之后,就將利州的況先一步稟明給了顧元白。
顧元白看完之后直接然大怒。
利州的知州今年決了一個貪污吏,這貪據說為非作歹、強搶民、貪污,利州知州查都沒查就將此人給押了大牢。此案件后經過大理寺審查,發現有疑云,便讓利州知州重新決斷,但利州知州一意孤行,直接將這名員給斬了。
監察的人查到,被死的員雖有些貪污行為,但罪不至死,更沒有為非作歹、強搶民的惡行,完全是他人造謠誣陷。如果只是這樣,那只能判知州一個判案有誤、是非不分的罪名,但監察一查,查出了一件好玩的事。
補上這位被誤判死的職的地方,竟然是京城“雙學派”的人。
細細一番調查之后,監察的人發現知州也是雙學派的人。
結黨營私,帝王生平大忌。
顧元白看著監察送回來的信,圣上的怒火讓殿中的人瑟瑟發抖地跪倒在地,他冷笑兩聲,“好,好得很。”
他才清洗了前朝廷,員之中的黨派不敢結,就拿著學派開始結黨營私了?
顧元白將信紙放在桌上,還是怒火燒心,他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冷道:“讓國子學掌教召來。”
第二日一早的早朝結束,眾位大臣不及退下,就被圣上以視察學子的名頭帶到了國子學。
國子學中的學子們讀書郎朗,清脆而悅耳。掌教帶著眾位講師早已等在國子學之前,恭迎圣上駕到。
一眾臣子跟在圣上后,只以為圣上是心來,便也笑著隨侍在側,見識了一番國子學的大好俊才。
等看完了這些學子之后,眾位大臣以為這就結束了,卻沒有想到掌教面嚴肅地請他們進了一學堂。
Advertisement
學堂之中已經放置了數把椅子,大臣們面面相覷,掌教已經走向了前方,沉聲道:“請圣上、大人們坐下吧。”
工部尚書看向最前面的位置:“圣上,您坐?”
顧元白卻向著眾人后走去,道:“朕坐在最后。”
“那如何使得?”戶部尚書驚慌道,“圣上怎能坐在我等之后?”
但顧元白已經坐了下來,他面淡淡,“坐吧。”
眾人疑不解,紛紛坐了下來。
平日里職高的在前面,因為這會兒圣上在最后坐著,所以那些職高的也變了坐在后面。
等眾位員全都落座以后,掌教開了口,他的第一句話就驚得滿屋臣子心中驟停,“下要給各位大人講一講先帝時的牛高之爭。”
牛高之爭,是先帝在世時的一場黨之爭,以朝中重臣牛大人一派為首,與另一派以高大人為首的黨羽腥風雨的政斗。
先帝喜佛,格說的好聽點是仁善好聽諫言,說的難聽點就是耳子。那時牛高之爭禍朝政,先帝也只是各打三十大板,讓他們各自收斂一些。牛高二黨見先帝手段如此弱,便更加囂張地同對方爭奪起了朝廷地位和權力,他們仗著的正是“法不責眾”四個字。
直到如今的圣上出生后,先帝才打算起來為自己的子清除黨,那場禍害朝政八九年的牛高之爭的黨羽,這才相繼落馬。
這一件事,也為人人不敢提起的事,了不可言說的言。
而現在,國子學的掌教就當著眾位朝廷命和圣上的面,直接說起了這事。
政治敏銳度高的員已經察覺出了不尋常,離圣上越近的人,越是直了繃著聽著掌教說出的每一字。
Advertisement
“結黨營私,是歷朝歷代都有的弊端,”掌教高聲道,“先帝在時的牛高之爭只是其一,而這牛高之爭,便是兩派以朝中重臣為首的爭端。這場爭端的戰場不止在京城,也是在地方……”
已經有人頭上泌出了細汗,微微低著頭,不敢接著再聽。
這時,圣上的聲音就從后傳了出來,不咸不淡道:“給朕抬起頭,認認真真的聽。”
于是臣子們被迫抬起了頭,不敢錯過一瞬。而隨著越聽,他們心就是越沉。
掌教已經說到了兩派地方員因為黨爭而互相誣陷廝殺的事,這些事跡被淋淋的揭出來,每一句話都足以讓人膽戰心驚。
圣上就坐在最后,無數人的背影就會被圣上看盡眼底,有的員余一瞥,就看到守衛在講堂外側的腰配大刀的侍衛們,瞬時之間,后背就被汗水浸了。
終于,不知道過了多久,這場艱難的黨羽之爭總算是講完了。掌教從前頭走下來到圣上邊的時候,坐在前頭的員們大半部分都齊齊松了一口氣。他們頭腦得到了半分的輕松,開始細想圣上為何今日帶他們來國子學,而又帶他們來聽這一趟話的目的了。
掌教恭敬道:“圣上,臣已經講完了。”
顧元白端坐在雕花木倚之上,聞言微微頷首,手指敲著扶手,表看不出喜怒,道:“那就重頭再講一遍。”
掌教額角有汗珠落,他不敢有片刻耽誤,大步又朝著前方走去。
這一遍又一遍的,整個屋中的氣氛極度繃,顧元白放眼去,眼可見的,一些人已經坐立不安了。
田福生給顧元白送上了茶,顧元白慢慢喝著,心底中原本的怒火已經沉了下去。
以高為首的黨派,和以學派、地方出為首的黨派,有什麼區別?
Advertisement
全是想占有顧元白的土地、權利和資源,用顧元白的東西去收攏顧元白的員,徹徹底底的慷他人之慨。
但皇帝之慨,哪有這麼好慷的?
顧元白解了就將茶杯放下,他對著站在后門筆的薛遠勾勾手,薛遠角勾起笑,走了過去,低聲道:“圣上有何吩咐?”
心口砰砰,這真的是君臣之心?
薛遠余瞥著顧元白,想看見他笑,不想看到他如此氣憤。氣壞了怎麼辦?這大概真的就是忠君之心了。
顧元白道:“你去將太傅李保請來,他當年親經歷過牛高之爭,講起來總是要比掌教有所慨。”
薛遠站起,影打下一片,干凈利落地應了一聲是,轉就大步朝外走去。
顧元白被影遮了一下眼,下意識朝著薛遠背后看了一眼,這乍一看,他竟然發現薛遠好像又長高了些。
顧元白皺眉問:“薛九遙今年年歲幾何?”
田福生想了想,不確定道:“應當已有二十有四了。”
二十四歲還能長個子?顧元白看著前頭各個神繃的員,漫不經心地想,那朕才二十一,怎麼沒見長?
前頭的員們祈禱著希掌教能說的快些。等這一遍終于說完了,掌教還不敢下去,圣上邊的小太監過來道:“掌教大人,快請下吧。您今日辛苦了,外頭炎熱,您可先回去歇息一番。”
眾人見掌教走了下來,俱都以為這已經結束了,心頭陡然一松,面上都出了放松的神。但后的圣上沒人說話,也就沒人敢出聲。
長達一刻鐘有余的寂靜后,門旁又響起了腳步聲。眾人抬頭一看,就見名滿天下的大儒李保拄著拐杖走了進來,一步一步挪到了前頭,見到底下眾位員盯的目后,深吸一口氣,鏗鏘有力地道:“今日老夫就在這,給眾位大人講一講先帝當年禍朝政的牛高黨之爭!”
眾位臣子頭暈目眩,心臟又猛得提了起來。這一松一,嚇得人簡直兩戰戰。
外頭的日頭雖大但是不烈,屋里的人卻像是七月盛夏一樣,熱得都要不過來氣。
等李保講完被人送出去后,這會再也沒有人敢放松了。
顧元白等了一會,才悠悠問道:“諸位大人可有何想法?”
不敢,不敢有。
六部尚書和各府重臣拿著余看著彼此,樞使趙大人眼觀鼻鼻觀心,政事堂的參知政事也是如此,此兩府可沒有什麼結黨營私的爛事。
過了一會兒,終于有人站了出來,道:“黨羽之只會禍朝綱,一旦發現必須嚴懲不貸!”
“刑部尚書說的對,”圣上道,“那這嚴懲,應該又如何嚴懲呢?”
刑部尚書道:“視其程度,分級追究。”
顧元白頷首,聲音溫和了起來,“刑部尚書說得對,朕也是這麼想的。”
各位大臣聽出了圣上語氣中的緩和,繃的神微松。
刑部尚書卻不敢胡思想,他直覺圣上的話還沒說話,而這話,必定就是今個兒這一出的主要容。
果然,圣上語氣不變,又問道:“那若是黨派中的地方高用手中私權,鏟除了另一黨派罪不至死的員,在其空缺上安自己黨派的人,這該當何罪?”
刑部尚書力陡然一大,他慎之又慎,思之又思,“當以徇私枉法、結黨營私、德行不佳以做罰。”
圣上沒說好與不好,只是轉而道:“吏部尚書,你說該如何?”
眾人不明白圣上為何突然起吏部尚書,轉頭朝吏部尚書一看,吏部尚書也滿頭霧水,但還是恭恭敬敬地道:“臣認為刑部尚書說的對。”
圣上親手把持朝政到如今也有一年半的功夫了,大家伙也研究出來了一個細節。圣上要是心好,那就是喚臣子為某卿某卿,若是心不好,或者哪個員犯了他的忌諱,那就是會口氣淡淡的全了職,就如同此時吏部尚書一樣。
“朕也認為刑部尚書說的對,”顧元白笑了起來,“如今正好也發生了一件朕所說的事,既然吏部尚書認為理應如此,那便去同大理寺一同理好吧。”
吏部尚書不負責理這些,他眼睛一跳,心中升起不妙的覺:“是。”
顧元白終于起,在宮侍的陪侍下往外走去,剛走了兩步才想起來,轉過頭道:“吏部尚書,此案中的員涉及到的派別,正是‘雙學派’了。”
朝中是雙學派中的人猛然驚醒。
圣上笑了一下,然后聲音驟冷:“朕希你不要也犯了徇私枉法的錯。”
“朝廷重,應以國以民為重,”顧元白的目在眾位臣子的上一一掃視,道:“朕也眾卿應知,今日你們所聽的三堂課,到底講了些什麼。”
本就是各派代表人的朝中眾人冷汗已出,沉沉躬:“是。”
顧元白走出了講堂,還站在講堂中的諸位臣子卻腳僵。正當眾位大人到后怕之事,突聽一道聲音響起:“諸位大人,還請走吧,各衙門的事務都耽擱不起片刻。”
埋在眾位臣子之中的薛將軍覺得這聲音太耳了,抬頭一看,可不就是自己的兒子。
薛遠彬彬有禮地笑著,瞧起來氣度很是不凡。
眾位臣子驚醒,開始三三兩兩地出了門。薛將軍往邊上走去,走到薛遠跟前,低聲道:“圣上今日是怎麼了?雙學派出了什麼大案?”
薛遠低頭瞥了一眼薛將軍,懶洋洋道:“薛將軍這是要打聽圣意?”
薛將軍氣得臉一板,大步走了出去。
等人都走完了,薛遠才將腰間的佩刀正了正,快步追著圣上的方向而去。
他走到國子學門外時,皇上的馬車已經走遠了。薛遠失笑,往周圍一看,上前將薛將軍從馬上拽下來,翻上了馬,韁繩一揚,“駕!”朝著顧元白的方向追去。
薛將軍氣得在原地跳腳,“逆子、逆子——!”
不過一會,薛遠就追上了大部隊,他策馬趕到顧元白的馬車一旁,清清嗓子,“圣上,您若是心不好,也可拿臣出出氣。”
剛說了兩個字就忍不住發笑。
前幾天圣上罵他畜生東西都能把他罵了,還是算了吧。薛遠最近覺得自己火氣太大,要是又被罵了,嚇著人怎麼辦。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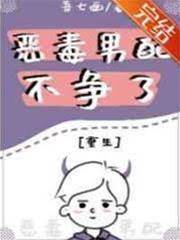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