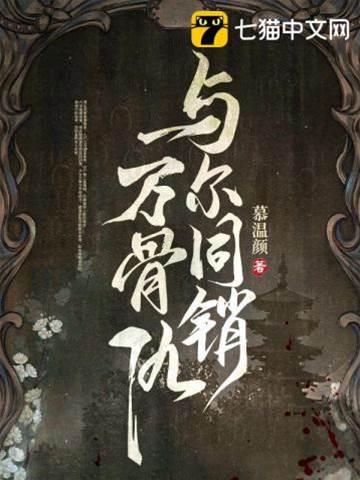《嬌嬌(重生)》 第47章
他說著關心的話,眼神卻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骨節分明的手兀自留在的袍帶上,指尖的熱力過薄薄的袍,傳敏的腰眼,令忍不住微微栗。
他明明沒有到的任一,卻仿佛被他錮住,無法彈。
不行,不能這麼下去。
“睿舅舅……”半晌,終于回過神來,輕呼著想要后退。剛退一步,他剛剛系好的袍帶便在他手中扯,眼看就要散開。頓時嚇得止住作,僵直子,氣惱道,“您放開我。”
他神不解:“我抓住你了?”
瑟瑟著他端肅平靜的凜然面容,不由牙:裝什麼裝?你分明就是故意的。經歷了上輩子,我還不知道你嗎?表面看著道貌岸然,實際上就是個胚,混蛋,一肚子的男盜娼。
瑟瑟想到當初他迫著承的那些花樣就又氣又恨。越是抗拒他,他就越惡劣,不知從哪里學來的齷齪手段,擺弄的,挑逗的極致,每每要弄得瀕臨崩潰,哀泣求饒才罷休。偏偏那些文武百還總覺得他們的君王不好,英明神武,將留下,完全是使出百般手段,狐主。
,他個頭啊!不他都已被他折騰得上天無路,地無門,哪還敢火上澆油?
蕭思睿見杏眼圓睜,敢怒不敢言的模樣,眼中出一笑意。他忽地手將攬懷中,聲音低沉下來:“別惱了,嗯?”
他的作實在太過自然,自然到瑟瑟慢半拍才反應過來不妥。手抵住他堅實的,正要推開他,他輕飄飄地扔下一句:“今日在林中,我忘了告訴你,我之前已經請求喬太夫人做主,為我們持婚事了。”
Advertisement
瑟瑟石化了。半晌,才發出聲音:“您,你怎麼這麼快……”憑喬太夫人的本事,這樁婚事只怕真有希。
“你的事,我怎能不上心?”他別有深意地道,“所以,瑟瑟,你必須盡快過這個坎,習慣我不再是你的長輩。”
瑟瑟快瘋了:這可真是前門拒狼,后門進虎。崩潰道:“可您不是一直把我當外甥,您就不別扭?”這一世,不是一直好好的嗎,他怎麼忽然就對又起了念頭?
忽然就想到他剛剛看到足時的眼神,懊惱之極:明知道他對的一對玉足有著格外的喜與執著,還這麼大意,讓他看到了。只怕就是那一刻,他重新對燃起了/念。
蕭思睿哪能不知的想法,低頭看,聲音帶上了一笑意,眼中卻無半分笑意:“兒,長輩可不會這麼抱著你。”他敏銳地察覺到,聽到那個悉的稱呼,懷中的軀控制不住地抖起來,卻很快強行止住。
他的眼底不由飄過一霾。
瑟瑟沒有發現,如困般暴躁地找著出路:“可娘親是最重規矩的人,我喊了您這些時候的舅舅,必定不會同意。”
蕭思睿道:“這個瑟瑟就不用擔心了,喬太夫人自有辦法。”
瑟瑟沒轍了,從不懷疑喬太夫人的能耐,愁容滿面地道:“您,您就不能和喬太夫人說說?”沒等他回答,自己頹然住了口。他婚事不順,喬太夫人早就懸心已久,聽到他要娶妻,想必該高興極了,就算他想反悔,喬太夫人也不會同意。何況,他兒沒有反悔的意思。
蕭思睿著懷中花容慘淡的佳人,只覺仿佛有一無形的線在反復絞著心臟,疼得幾乎失去了知覺,銳利的眸中漸漸生出戾氣:視他如洪水猛,連掩飾都不掩飾了。呵,他早該知道,甚至寧愿嫁給蔣讓那種無能之輩,也不愿意嫁給他!
Advertisement
可這輩子,休想他再放過!欠他一條命,合該以自己來還。
屋外忽然傳來了“啪啪”的石子聲。蕭思睿問道:“什麼事?”歸箭的聲音在窗外小聲響起:“大人,常先生有急信,趙安禮的口供問出來了。”
常先生,他說的是那個刑訊高手常祿,從趙安禮口中問出話了?瑟瑟霍地扭頭看向窗外。
蕭思睿看神,松開,吩咐道:“把信拿進來。” 瑟瑟忙退后一步,和他拉開距離。
歸箭輕巧地從窗外跳了進來,眼觀鼻、鼻觀心,將一封信恭敬地高舉呈上。
蕭思睿接過掃了一眼,遞給了瑟瑟。
瑟瑟飛快地看完,頓時驚怒不已,果然,趙安禮所做的一切都是被人慫恿的,那人不是旁人,正是上一世和趙安禮恩恩,雖是妾室,卻過得比姐姐那個正室還要風的盧娘。有人買通了盧娘,勾搭趙安禮,并想借著燕晴晴拿燕家。
常祿只問出了這些,更多的趙安禮也不知道了,只有去問盧娘。盧娘卻在知道趙安禮事敗后,便收拾包袱逃跑了。
瑟瑟想不通:燕家不過是個普通人家,連仇家都沒結過的,究竟是誰,要如此苦心孤詣,煞費周張地對付他們燕家?
著蕭思睿,微,卻終究什麼也沒說。
蕭思睿看了一眼,吩咐歸箭道:“繼續找那個盧氏。”
瑟瑟激道:“多謝您。”剛剛才拒絕他,原本沒臉開這個口,沒想到他竟會主幫忙。
他淡淡道:“謝倒是不必。瑟瑟只需付報酬便行。”
瑟瑟一愣,不由問道:“您需要我付什麼報酬?”
他目晦暗,忽地向近一步,察覺不對,想要后退,他長臂一撈,已再次將攬懷中。瑟瑟又又窘:“歸箭……”“還在呢”三個字還未來得及說出口,歸箭已“咻”的一下跳出窗,溜得比兔子還快。
Advertisement
瑟瑟:“……”
他著呆若木的模樣,眼神暗了暗,忽然低下頭,輕輕親了親的發頂。
那一吻,輕如蜻蜓點水,春風拂柳,瑟瑟卻覺得仿佛有一電流躥過,瞬間流遍四肢百骸,差點沒跳起來:“您,您……”
他掐住腰,一眨不眨地看著,目如有實質,一寸寸掠過的全。
那是悉又痛恨的強勢掠奪的目。
瑟瑟不由又氣又恨,子卻在他在腰間某輕輕一后,面泛紅,不爭氣地在了他的臂彎。
這個人,在三年的孜孜探索中幾乎悉了的每一,知道的每個肋,能輕易地掌控的。就知道,他平時再裝得如何嚴肅冷,卻委實不是什麼好東西,骨子里,依舊是那個喜歡失控,哭泣求饒的大混蛋。
他著懷中眼睛都紅了的,心中發疼,面上卻出了微微的笑,手,撈起一縷緞般的長發,送到邊輕輕一吻:“瑟瑟,能娶汝為妻,吾之幸也。”
瑟瑟愣住了。
抱月指揮兩個使宮人抬著熱水過來時,發現瑟瑟長發披散,只松松地披著一件外袍,坐在角落里發呆。也不知在想什麼,白生生的小臉上紅暈布,杏眼水汪汪,霧蒙蒙的,如有波漾。
饒是抱月見慣了的貌,一見之下,也不由臉紅心跳,疑叢生:二娘子這是怎麼了,怎麼忽然變得如此,如此……抱月想不出合適的詞來,如果一定要形容,那就是態橫生,勾人心弦。
抱月的心知不由怦怦跳起來,心想幸虧這副模樣沒有被男子看到,否則,否則只怕無人能把持得住。
指揮著宮人將熱水倒耳房中的浴桶,這才過來請瑟瑟道:“二娘子,可以沐浴了。”
瑟瑟猛地回過神來,手握住了發燙的臉頰。
抱月忍了又忍,還是忍不住問:“二娘子,你怎麼了?”
瑟瑟搖搖頭:“沒什麼。”也不要抱月服侍,自己獨自進了耳房。解開外袍,除去羅時,不期然又想起他剛剛幫穿上時的景。
明明他是在幫穿戴整齊,可他看著的眼神,為什麼總讓有一種在他面前無寸縷的錯覺?
瑟瑟想到他的模樣就是一個激靈,搖搖頭,努力甩心中異樣的覺,將自己深深地埋水中。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辦?
晚上,長安公主在行宮正殿集芳殿宴請他們。
集芳殿位于山腰,由無數高達數丈、有數圍的原木筑,涂以清漆,不加雕飾,頗有返璞歸真之趣。殿中以十二巨柱撐起穹頂,殿宇高曠,暑熱不侵,正是夏日設宴勝地。
顧于晚了傷,不能出席,大皇子沒有留下,連夜回了自己的府邸,余下只剩長安公主、陳括、蕭以嫻和瑟瑟,再加上不請自來的蕭思睿五人,一人一席,男左右而設。
瑟瑟沐浴耽擱了時間,等到到集芳殿時人已到得差不多,一走進去,所有人的目都落到了上。
換了一石青鑲斕邊輕羅褙子,銀白間挑線子,披一條輕紗披帛,烏黑如緞的秀發松松挽了個髻,只斜了一支珠花,在兩耳各垂下一縷發。
似乎沒有上妝,大殿中輝煌的燈火打在面上,剛剛沐浴過的呈現出水潤的白,出淡淡的紅暈,邊的梨渦甜而人;彎彎的柳眉下,那對含笑的杏眼映著燈火,流盼生輝,瀲滟多。
一時間,殿中竟是靜了片刻。
瑟瑟含笑向長安公主告罪:“我來遲了,公主恕罪。”
長安公主這才回過神來,目灼灼地看著笑道:“宴席還未開始,蕭大人也還未到,燕姐姐并不遲。”
瑟瑟笑著謝過,這才依次向其他人行禮。陳括一見便出笑容,問道:“可住得習慣?宮人可有失禮之?”
瑟瑟自然搖頭。
長安公主在一邊笑陳括:“七皇兄,你怎麼忽然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怎麼沒見你這麼關心我啊。”
陳括臉微紅,有些窘迫,蕭以嫻幫他解圍道:“燕家妹妹第一次來屏山苑,七殿下多關照些也是應該的。”
陳括激地看了蕭以嫻一眼。
瑟瑟在一邊保持微笑:蕭以嫻一直如此,溫,事事妥當,活另一個蕭后。記憶中,自己似乎從來沒見到過對方失態的樣子。
可正因為如此,從來都不喜歡蕭以嫻。一個人從來不失態,從來不表真實的緒,原本就是一件可怕的事。
長安公主也是個有口無心的,說過就放到了一邊,笑著指了旁邊的席位對瑟瑟道:“你坐這里,離我近些。”
瑟瑟微微一愣:宴席的席位可不比其它,大有講究。像們這些沒有誥命的小娘子,誰上座,誰次座,全要看父兄的位,這個位置怎麼看都該是蕭以嫻坐的。
推辭道:“還是讓蕭小娘子坐那里。”
長安公主不高興了:“我已經跟蕭家姐姐說過了,都同意了。”
瑟瑟哭笑不得:你開了口,蕭以嫻哪能拒絕?可自己卻不能不知好歹。正要堅辭,外面又有了靜,侍尖利的聲音響起:“蕭大人到。”
眾人向殿外看去,就見蕭思睿披一件玄繡銀大氅,不不慢地走進大殿,向陳括和長安公主行過禮后,他的目落到瑟瑟上。
瑟瑟實在有些怕他看的眼神,總讓有一種無可逃的可怕覺。深吸一口氣,才若無其事地向他行禮:“見過睿……呃,蕭大人。”
蕭以嫻也向蕭思睿行禮,隨即在一邊掩莞爾:“我聽說九叔認了燕妹妹為外甥,還帶著燕妹妹去見了祖母,怎麼這會兒見外起來了?”
長安公主還不知道這事,聞言意外道:“還有這事?”
瑟瑟赧然不語。蕭思睿自己做的孽,倒要看看他打算怎麼說。
蕭思睿淡淡道:“我與有緣,恰好母親亦姓蕭,便認了為外甥,卻不想出了點岔子。”
長安公主好奇道:“什麼岔子?”
蕭思睿道:“我帶了去見太夫人,太夫人慎重,特意去建業蕭氏對了族譜,哪知……”他出苦笑之。
這下子,不是長安公主,別人也好奇起來。
瑟瑟心中驀地起了不妙的預。
蕭以嫻催道:“哪知什麼?您就別賣關子了。”
蕭思睿道:“從建業蕭氏的族譜推下來,母親原比我長了一輩,我倒是平白無故地占了便宜,讓了好幾日舅舅。”
蕭以嫻一怔:“這麼說,燕妹妹,呃,燕小娘子與九叔您是一輩的?”那豈不是要對方表姑?呃,皇后姑姑與九叔也是一輩的,如此說來,七皇子豈不是也比小了一輩?
蕭以嫻不由看了陳括一眼,果然見到對方的臉也是十分微妙。
瑟瑟目瞪口呆:還,還能這麼作?
作者有話要說: 太夫人:為了把我家九郎這個滯銷貨推銷出去,這個鍋我背了!
昨天那些沒良心要看我哭的,別走!我要拿小本本記下來!
謝以下小天使,(づ ̄3 ̄)づ╭
林亦槿今天也是世最可扔了1個地雷,沉沉扔了1個地雷~
灌溉營養:“卑微小媛在線流淚!”+3,“是是是是是我啊”+1,“憨憨”+10,“碧”+3,“DL”+5,“被吃掉的小橘子”+1,“千南”+6,“彭阿笪”+5~
猜你喜歡
-
完結642 章

退婚后我成了皇城團寵
一朝穿越,楚寧成了鎮國將軍府無才無德的草包嫡女。 當眾退婚,她更是成了一眾皇城貴女之間的笑話。 可就在眾人以為,楚寧再也無顏露面之時。 游園會上,她紅衣驚艷,一舞傾城。 皇宮壽宴,她腳踹前任,還得了個救命之恩。 入軍營,解決瘟疫危機,歸皇城,生意做的風生水起。 荷包和名聲雙雙蒸蒸日上,求親者更是踏破門檻。 就在楚寧被糾纏不過,隨意應下了一樁相看時,那位驚才絕艷的太子殿下卻連夜趕到了將軍府: “想嫁給別人?那你也不必再給孤解毒了,孤現在就死給你看!”
112.9萬字8 2071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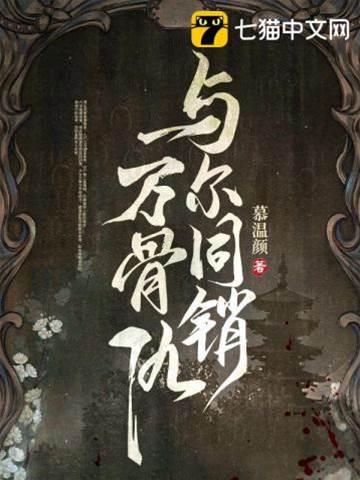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746 -
完結182 章

夫君他清冷又黏人
姜初妤爲了逃婚回到京都,正好在城門口遇上少年將軍顧景淮班師回朝。 他高坐馬上,衆星捧月,矜貴無雙。 是她從前的婚約對象。 正巧,皇帝忌憚顧家勢力,把她這個落魄貴女依婚約賜婚給了他。 新婚夜裏,顧景淮態度冷淡,不與她圓房,還在榻中央放了塊長橫木相隔。 知他不喜自己,姜初妤除了醉酒時抱着他喊“茂行哥哥”,唯一的越界,便只有以爲他身死時落下的那一吻。 可誰知,顧景淮“復活”後,竟對她說: “我也親過你一回,扯平了。” “?!” 她的夫君不對勁。 再後來,顧景淮某夜歸來,毫無徵兆地把橫木撤下,摟她入懷。 姜初妤十分驚訝:“夫君,這不妥吧?” 沒想到素來冷麪的他竟一臉傷心:“夫人怎與我生分了?” 姜初妤:? 翌日她才知道,他不慎傷到了腦袋,對她的記憶變成了一起長大、感情甚濃的小青梅。 他一聲聲皎皎喚她,亂吃飛醋,姜初妤無比篤定這個記憶錯亂的他喜歡自己,卻捉摸不透原來的他是怎麼想的,不敢與他太過親近。 可某日她忍不住了,踮腳在他脣上親了一口。 顧景淮霎時僵住,耳廓爆紅,不敢看她。 姜初妤頓覺不妙,臉色也由紅變白:“你是不是恢復記憶了?” 顧景淮捂着下半張臉,可疑的紅從耳根蔓延到了脖頸。 看來將錯就錯這步棋,下得有些險了。
27.3萬字8 54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