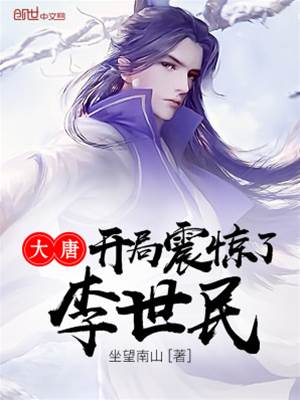《世子兇猛》 第一千二百二十二章 用心良苦
秦老大開始裝了,上鄂卻滿面詫異。
“殿下竟也知福州天子號良田居多?”
秦玄回道:“是,書院中有文庫,孤是從文庫中所得知的。”
“文庫。”上鄂不解。
“地理山川、民生風俗、無所不包,早在堂兄他去東海前就定了搜集文庫資料一事,這兩年來,書院都會派人搜集這些資料。”
“用來教授學子?”
“是,堂兄說,既然行不了萬里路,那就要讀萬卷書,萬卷書,萬里路,總要選一樣的。”
上鄂沉默了。
人們總是說上無辦事不牢,并不是因為年紀,而是因為年紀輕經歷的,懂的。
之所以經歷的,就是因為走的路。
萬卷書,千里路,人,總要選一樣的,這話,一點都不假。
秦老大沒好氣的說道:“大道理,他比誰知曉的都多,做的時候,什麼道理都忘掉了。”
盧通打趣道:“大道理,小道理,都是道理,自己不做,教于別人做,有何不可,殿下是山長,不是學子,能教授就可。”
秦老大側目不已。
他發現最近盧通總是幫秦游說好話,有些反常。
秦玄倒是沒想那麼多,笑著說道:“萬里路,萬卷書,都是學識,湖城知州曹琥大人,沒有讀過萬卷書,來了夏京,立功封爵,最大的愿,卻是回湖城,將他這萬里路上所見所聞,說給他的族人聽,大家探討這些個所見所聞,要如何改變湖城與湖部族,而書院的學子們,恰恰相反,堂兄教導他們,曹琥大人行了萬里路,是為了回到湖城,而學子們在書院讀了萬卷書,是為了離開書院,在書院,讀萬卷書,是要將學識揮灑出去,帶給所有人,行萬里路,是得到學識回到故鄉,改變自己族人的命運。”
Advertisement
秦老大神微變:“書院的學子,不留在京中?”
“是。”
“這混賬東西!”秦老大這怒意說來就來:“那麼多大儒,整日耳提面命教導學子,離了書
院不來朝堂之上為君分憂,卻要離開夏京,何統。”
秦玄哪能想到自己隨便一句話就給秦游拉了仇恨,連忙解釋道:“父皇,非是如此,堂兄尊重每一位學子的選擇,朝堂之上,夏京之中,百行百業,各道之,堂兄與廖師傅從未強求過任何學子,是學子們自己選擇的。”
“都是些孩子,哪里有什麼選擇與否,還不是平日書院教導的,若沒有這風氣,學子們哪會想要離京。”
從秦老大的怨念中可以看出來,上雖然不說,但是他極為重視書院中的學子的。
不只是他,包括極為朝堂大佬也是如此。
他們太改變朝堂上的風氣了,書院的學子,就是一清新的風,可沒想到這風并不是吹響朝堂的,而是吹向了京城之外。
沒了秦游的庇護,不在夏京,這些學子,當真能一展中抱負嗎?
“罷了。”秦老大頗為無奈的說道:“秦游與廖師傅既然如此打算,朕還能說什麼,那些學子,皆是良才玉,雕琢一番未嘗不可。”
興致缺缺的秦老大繼續看向奏折,只是心煩意之下,死活都無法集中注意力。
一來氣,自然是找出氣筒了,將奏折扔到秦玄懷里,秦老大哼聲道:“報館推廣覆蓋圖,又是書院的奏請,云里霧里。”
秦玄低頭看了眼,樂了:“覆蓋圖而已。”
“朕問的就是這覆蓋圖是何意。”
“就是覆蓋圖啊。”秦玄指著奏折解釋道:“上面用紅線標注了各州府報館輻的區域,白線代表無法看不到報紙的區…”
Advertisement
秦老大打斷道:“你都能看懂?”
“兒臣自然是能看懂的。”
“好,那你與朕和諸位卿說說,三言兩語便可說清楚的事,為何要畫出這所謂的覆蓋圖,難道朕還不知報館的重要嗎,推廣便推廣,故弄玄虛作甚。”
“父皇此言差矣,如圖所示,四水之地,六縣,多山多水,水路難通,山路難行,政令更是不達,所以將
此地標記出,雖要辦三家報館,卻不是要告之政令,而是拼音普學之策,上面已有標注,去年科考,四水之地連一個考生都沒有,有此可以證明,此地督學員就是飯桶,識字率不高,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可若是報館辦起來,就需讓當地府教授拼音之法,白線就是此意,下有注釋。”
秦老大恍然大悟:“原來如此,這般辦,可比辦了學館輕省了不。”
“堂兄早就說過,報紙,雖可盈利,卻也有大用之,朝廷用的好,對行之政令大有益。”
秦老大倒是明白這個道理,不過他更興趣的是秦玄,秦玄竟然能夠很輕易的看懂這些“晦難懂”的奏折。
心生考校之心的秦老大又出了一本奏折,扔給秦玄:“廣尋縣商勾結一事,騎司奏上來的,沒有證據,只有一份看不懂的圖表,什麼差距收全國之最,何意?”
秦玄打眼一掃,沒看奏折容,只是看了圖表,眉頭就皺了起來。
思考了片刻,秦玄臉上帶著幾分怒意:“廣尋盛產石料,王家石行的商隊遍布境,每季獲利五千余貫,可謂豪商巨賈,可該縣賦稅卻連年欠收,每年欠稅額,又與王家獲利有所關聯…”
盧通聞言,不由開口道:“殿下是說,這王家區區商賈,敢貪墨了朝廷稅銀?”
Advertisement
“不,與當地民生經濟有關。”
秦玄放下奏折,思索了片刻,這才說道:“廣尋每季車隊出七百二十馬,開采的山石數量可想而知,而廣尋縣是下縣,只有千余戶,這也就是說,要滿足王家售往各地的石料,這千余戶,至要有六人開山,可王家獲利巨大,而當地縣民連稅都不起,造冊的新生兒更是的令人發指,加之廣尋沒有太多商賈,那麼有此可以判定,此百姓極為窮困。”
盧通沒有聽懂:“老臣還是未明白騎司為何要說當地商勾結。”
“盧大人不是有報館的份子嗎,那孤便拿此來舉例,假如報館每月獲利一千貫,可
報館中整日務工的長工卻只領到了十文錢,難以度日。”
“殿下是說,廣尋縣的百姓,都在開山采石,了王家的長工,到了手中的工錢,卻之又?”
“不錯,正是因為如此,廣尋無商賈,因商賈去了,百姓手中無錢,商賈無利可圖,新生兒,也能表明百姓們度日艱難。”
“既然工錢,為何廣尋縣的百姓不去別的地方做工,三百里外就是…”
盧通說不下去了,秦老大和其他幾位臣子也面劇變,想通了關節。
各地的百姓并不是說你想去哪就去哪,想要離開本縣,需要開憑證的,去府開憑證,無論是串親戚閑溜達或者經商,有正當理由,本地府核實后才能給憑證,去的地方越遠,辦起來也就越麻煩。
如果地方府不給這個憑證的話,百姓就沒辦法離開,可不離開總要養家糊口啊,只能去給王家開山采石,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也正是因為如此,王家才將工錢定的特別低,這才有騎司所謂的“商勾結”之說。
秦老大目已帶著幾分怒火了,掃了一眼聞人泰,后者趕主說道:“臣一會離了宮就回刑部派遣快馬前往廣尋縣查明。”
上鄂對這些到不是很在乎,看向秦玄問道:“這些,都是書院中教授的?”
秦玄應了聲是。
秦老大興趣更濃,又遞過去一奏折,是遞,不是像剛才那般扔了。
“給朕看一看,農司的奏請,要戶部調撥八百貫,用于什麼種糧察錄,朕知杜子先生不是夸夸其談之輩,可卻想不通,是幾個箱子罷了,為何要八百貫之巨。”
其實錢不多,就是盧通很好奇,秦老大也很好奇,按照他們的理解,農司要買幾個箱子,可幾個破木箱子,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秦玄看了眼奏請,再次笑了:“鏡箱,就如同千里目那般,此箱非彼箱,可過鏡子,看到農在土下的生長過程,奏折所說,杜先生想了個法子,讓墨家人用品質極佳
明鏡子裝箱子,其中裝土,埋種,放置后,每一日,在不同的鏡箱中埋下一顆種子,如此便可讓農司與學子們記錄農糧生長的況,其目的,就是觀察使用不同的化后,產量差別如何,最終找到提高農產量的法子。”
“大善。”盧通一拍大:“批。”
其他老臣也聽懂了,連連點頭附和,秦老大則是目沉思之,沒有吭聲,而是又將一本奏折遞給了秦玄。
“三日前,贛州道番蠻械斗一事,你如何看。”
這本奏折并不是書院的人奏請的,而是地方府,秦玄先是一目十行看了下去,接著一字一句的去讀,足足過了半晌,支支吾吾說不出什麼見解。
倒不是沒看明白,而是奏折已經被秦老大批復過了,要他理,還不如秦老大想的周全。
秦老大微微點頭,揮了揮手:“朕還要與幾位大臣商議些事,你去吧。”
秦玄站起,施了一禮,退下了。
太子這一走,秦老大看向幾位老臣:“諸位卿以為,這書院別出心裁的奏請,以及他們所稱行之有效的法子,當真是可行的?”
上鄂率先表態:“老臣以為可行,化繁為簡。”
其他臣子也是點頭同意。
秦老大表莫名:“難怪每隔一段時間,秦游就要太子去書院待上些時日,這些奏請,朕與你們,看的是難之又難,可太子,卻轉瞬間便能看出其中關鍵,朕這侄兒,倒是用心良苦了。”
盧通若有所思:“陛下您是說,這些奏請,實際上,本就是給太子看的?”
“是也不是,若是朕與你等可看懂,愿學,愿懂,再好不過,可若是朝堂上的大臣,既不學,也不愿懂,那太子便能確保這些奏請不會被束之高閣,待他習慣了如此批復這種奏折,他日監國,朝堂的臣子,也必須要如此奏請,可想要效仿,就要去學,而這要學的學識,就太多太多了,到了那時,朝堂上的臣子們怕是再難引經據典的夸夸其談,只能談論實務。”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978 章
重生三國之天朝威武
金三角的一位將軍轉世來到了東漢末年。 在這風起雲湧的時代,他要建立一支天朝鐵騎,他要恢復泱泱大國的風範,要讓萬國來拜。 人才他收,文的武的通通不拉,多多益善。 美女他要,享盡齊人之福展男人風采。 殺一人是罪,屠萬人是雄。 一個斬新的三國就此展開,一個亙古未有的大國疆域就此重新的劃分。
268.8萬字8 55127 -
完結1647 章
大明屠皇
崇禎十六年,軍醫朱劍穿越到了朱慈烺的身上,成為了大明朝的倒黴太子。肆虐的鼠疫,糜爛得朝政,席捲天下得李自成,肆虐西南的張獻忠,白山黑水還有磨刀霍霍隨時可能殺入中原得女真鐵騎,偏偏還攤上一個爛泥扶不上牆的便宜老爹。朱慈烺將屠刀一次次的舉起,不光是對準戰場上的敵人,同時也對準了朝堂上的敵人,對準了民間的敵人!殺貪官!除晉商!剿闖逆!滅獻賊!在不斷地血腥殺戮中興大明,成就一代屠皇!各位書友要是覺得《大明屠皇》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臉書和推特裡的朋友推薦哦!
299.2萬字8 16553 -
連載7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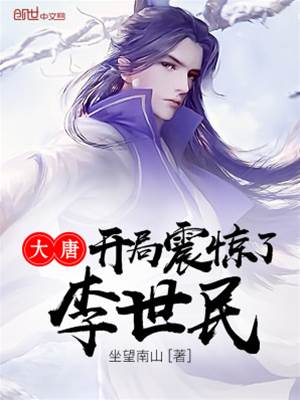
大唐開局震驚了李世民
穿越大唐,王子安只想當個閑散的富貴閑人,賺點小錢,弄點小菜,喝點小酒,吹個小牛,交一二……個紅顏知己…… 你們這一個個瞎震驚啥呢? 你們這一個個瞎湊乎啥呢? 我真不想娶…… 額——長樂公主? …… 那也不是不行…… 哎,我真是太難!
179.6萬字8.18 9633 -
完結1754 章

大唐:開局誤把李二當成災民
穿越大唐。 蘇辰原本只想做個混吃等死的咸魚。 所以帶人將莊子打造成了個世外桃源。 但貞觀三年冬,大雪肆虐,天下受災,民不聊生。 有兩個自稱商賈的人,因為怒罵他撒鹽掃雪,而被家丁抓了起來。 一個自稱姓李一個姓房。 對莊子一切都充滿了好奇。 每天更是追問蘇塵各種天下大事。 “你覺得當今圣上如何,他是否該對這次雪災下罪己詔?” “突厥犯邊,大軍壓境,你覺得如何才能退敵?” 蘇辰煩不勝煩,但偶爾也會指點幾句。 直到這天,姓李的家伙忽然說。 “攤牌了,我不裝了,其實我是李世民!”
316.3萬字8.18 788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