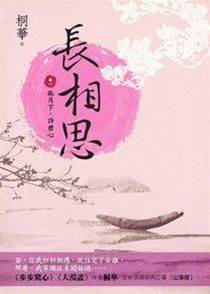《嫁病嬌后我咸魚了》 第88章 第 88 章
衛澧臉耳子更紅了, 別過頭擺弄手指,不去看。
當時兩個人吵架,他是個要臉的人, 怎麼可能低頭, 說是給過生日才來的, 那顯得他一點兒骨氣都沒有,像是求和似的。
他當時還不知道要不要喜歡趙羲姮,自然不能低頭。
六月一日, 是趙羲姮執著鞭子,在山出現,將他帶出來的日子, 自那一天開始, 衛澧才真正有了生命,作為人活在世上。
十一月三十日, 趙羲姮的生日,他明明說著討厭趙羲姮,恨恨到骨頭兒都疼,但還是默默去收集一切關于的消息。
他臉一紅,趙羲姮就知道自己猜對了, 佯裝憤怒道,“給我過生日怎麼才只拿一點酒來, 你心里是不是沒我?”
“閉吧,我能記著就不錯了。”衛澧惱怒, 直接去捂住趙羲姮的, “不對, 誰說是給你過生日的, 別自作多了。”
“那你是怎麼知道我生日的?”趙羲姮把他的手從上下來, 窮追不舍地問道。
“知道就知道了,你問這麼多干什麼?”衛澧坐立難安,干脆站起來,像是逃避什麼似的快步走出去了,“我還有事兒,先去理了。”
趙羲姮看著他近乎落荒而逃的背影,噗嗤一聲笑出來。
似是想到了什麼,自己尚且平坦的小腹,這個小家伙就是在生日那天來的。
大周年輕人并不崇尚過生辰,一般只有年過六十的老者,才會每年大肆慶祝,因而趙羲姮倒也不生氣衛澧只給帶了酒。
衛澧路上遇見了一隊侍,們嘻嘻哈哈的往廚房方向去,見著衛澧連忙收斂笑容。
“笑什麼笑?很好笑嗎?都滾去掃地!”他眉眼間滿是煩躁,甩袖走了。
Advertisement
地上跪著的侍們面面相覷,不知道主公又發什麼瘋,分明這幾個月與夫人琴瑟和鳴,神仙眷,已經修養了啊?
四月拜謁述職,三月下旬的時候,各地太守就已經陸陸續續帶著家眷到來了,尤其是那些個年終匯總被打回去,又罰了俸的,他們惴惴不安,生怕來的晚了再惹衛澧發怒。
還有新收并的原幽州郡城的六位太守,也早早來到了,畢竟比起平州其他太守,他們算是外來戶,還沒準新主子的脾,又與新主子沒半點兒誼,謹慎小心討好是應該的。
人一多,難免吵吵嚷嚷的,尤其對衛澧這種討厭鬧騰的人來說,他這幾日脾氣都很暴躁。
吃過晚飯后,西院的熱鬧幾乎掀翻了鍋,傳到東院的時候細聽還能聽著點兒諸如蚊子嗡鳴般的聲響。
衛澧氣依舊沒消,踢了踢椅子,隨手指了個侍,“他的,去!告訴西院,讓他們給爺老實點兒!別特麼出聲!一天天都要煩死了。再吵都滾出去!”
侍戰戰兢兢走了。
趙羲姮將目定在他腳邊兒的凳子上,然后目又幽幽落回他的臉。
衛澧順著的目看向凳子。
……
凳子是趙羲姮妝奩臺的凳子,現在被他踢倒了。
他連忙彎腰,將凳子扶起來,里甩鍋似的碎碎念,“啊,怎麼倒了,還好我給扶起來了。”
趙羲姮的臉還沒好,他又輕咳兩聲,用袖子了凳子上兒沒有的灰。
然后湊過去,跟趙羲姮轉移話題,“怎麼這麼糟糟的,他們有病吧?來了帶那麼多人,你不覺得吵嗎?把他們都趕出去吧,省得耽誤你養胎。”
“趕出去睡大街?”趙羲姮雖然也覺得他們帶的家眷實在太多了,但人家家人丁興旺,一家和樂還不讓?
Advertisement
“睡大街就睡大街,反正又不是我睡。”衛澧解下腰帶,把外隨手一扔,作利落瀟灑。
趙羲姮跟他說話了,那就是不介意他將凳子踢倒這件事了,他站在火炕上,一雪白的里,打開手臂,對著趙羲姮道,“來,抱一個。”
“不抱!”稚死了,多大的人了還親親抱抱,“你沒洗澡。”
衛澧下意識聞了聞自己上,一點兒異味都沒有啊,然后又湊過去,“我上不臭,你聞聞。”
“不要。”趙羲姮滾進被褥里,蒙著臉不見他。
衛澧一邊往隔壁室的溫泉里去,一邊威脅趙羲姮,“趙羲姮,你好好給我等著點兒的,等我出來揍你,現在還敢嫌棄我了。”
趙羲姮蓬松的被子里探出頭,“我就等著了,你能把我怎麼著?”
衛澧臉一沉,他是不能怎麼著,趙羲姮現在就是個小祖宗,他現在十分懷念之前那個每天糯糯的小姑娘了,他怎麼都不會反抗他。
他一咬牙,鉆進去洗漱。
沒多一會兒,他帶著滿的水汽出來,站在炕下頭,迫不及待地出手,“我洗完了,來抱抱。”
趙羲姮滿臉都寫著抗拒。
“抱!”衛澧執拗的朝出手,“來,你過來我掂掂你多沉。”
這次不待趙羲姮拒絕,他長一,踩上來,攬著趙羲姮的腰和背把人帶下來。
趙羲姮嚇得護住肚子,驚呼一聲,待反應過來,低頭狠狠咬了他的脖子。
衛澧疼的悶哼一聲但始終不愿意撒手,“你不給我抱打算給誰抱?”
自打歇晌起來那次,他有些沒分寸,鬧了將近一個時辰,趙羲姮就好久都不讓他,小手指都不讓,更不要提抱抱了。
Advertisement
他沒別的心思,就是想抱一下。
輕輕照著多的地方拍了一下,“你怎麼這麼兇?”
趙羲姮憤的臉都紅了,換了個地方又咬了一口。
但是剛才那口咬的牙都酸了,這次咬人更像是小貓舐人,的。
衛澧收起心猿意馬,單手摟著,下意識了自己發熱的耳垂。
“趙羲姮,你高了。”他上下打量一番,忽然道。
高一直是趙羲姮的執念,以前想長到衛澧的下,但后來發現長衛澧也長,這個愿有些難以實現,于是就改了,改長到衛澧肩頭那兒就。
“你是不是糊弄我的?”松了口,雖是這麼說,但語氣中帶著些許期待。
“真的。”衛澧將放下來,與自己著,用上次量高的法子來給比量了一番,的的確確是長高了,這次已經到衛澧的肩膀了。
趙羲姮驚喜地他,照著這樣長下去,說不定真的會到衛澧的下呢。
衛澧順勢的腰,“怎麼高了也沒見沉?肚子里還有孩子呢,腰怎麼也沒變?”
“怎麼沒變的?”趙羲姮忙不迭辯駁,拉著他的手往自己肚子上放,“這個月大了好多,不信你。”小家伙現在已經四個月多一點兒了,怎麼可能沒變化。
急于解釋,忽略了衛澧角那一抹謀得逞的笑。
“你都快一個月不讓我了,我上哪兒去?我哪知道長沒長大?”衛澧話這樣說著,手掌卻輕輕在了的小腹上,上下了,小心翼翼從上下擺鉆進去,滾燙的掌心著小腹的皮。
趙羲姮一,“。”
衛澧攬住,與額頭相抵,溫道,“我就一小會兒。”
“嗯,就一會兒。”趙羲姮做出了一點點讓步,畢竟小家伙也是他的。
“咚”
四周是寂靜的,這一聲是衛澧腦袋一弦兒崩斷的聲音。
他腦海里,現下不亞于山崩海嘯,巨浪滔天。
繼而嗡的一聲,神志全都喪失了,眼前白陣陣,渾抖起來,眼眶不自覺紅了。
許久,他才找回自己的聲音,“趙羲姮……”
衛澧聲音帶著哭腔,他不想這樣的,但他止不住。
趙羲姮也呆住了,一時間不知道怎麼辦好,上自己的小腹,“衛澧,了。”
醫師說小家伙四個月的時候,就已經會胎了,只是不明顯,若是不仔細,很容易忽略。
這是第一次在,小家伙很懂事,知道要讓爹爹娘娘都到。
衛澧與趙羲姮一直期盼著這個孩子降生,他們知道這個小寶貝正安安靜靜在趙羲姮肚子里逐漸長大,但卻是第一次,他們真切到小家伙是個會活,會鬧騰的生命。
這種覺,讓即將為父母的兩個人激又心悸,幾乎不上氣來。
趙羲姮去看衛澧,卻發現他眼睛紅的像個兔子,睫都巍巍沾了淚珠,死死咬住下,好像一副強迫自己的不哭出來的樣子。
“你是不是高興得都要哭了。”趙羲姮牽牽他的手。
衛澧沒敢說話,他怕自己一松口就哭出來,只能搖搖頭,倔強的將下抬高,表示自己才不會哭。
但真實反應是騙不了人的。
趙羲姮將臉埋在他口,環抱住他的腰,“我不看你,就抱抱你。”
衛澧沒有親人,連父母是誰都不知道,這個小家伙是和他唯一一個脈相連的人,知道他激,想哭就哭,又不會嘲笑他。
衛澧這才將回抱住,下搭在的肩頭,松懈下來,眼淚大滴大滴往下掉,怕自己哭出聲,死死咬住拳頭。
他會好好努力的,趙羲姮和孩子都要好好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64 章

誘上夫君——囧妃桃花多
蘇小荷是個低調的懶人,除非誰觸碰了她的底線,那麼她會給你看看她那顆變態的小心肝。 一朝穿越,變成了南宮世家的大小姐,不愁吃不愁穿,太符合她的理想人生了。 什麼,成親?她才18歲,是不是太早了點? 未婚夫好像不錯,好吧,反正都能衣食無憂,懶得逃了。 可為什麼新婚前一晚,她會中媚藥? 尼瑪,跳進荷花池怎麼會冇用? 哎呀,好可愛的小男人,對不起了,先幫姐姐泄個火! 名節已壞,未婚夫娶了親妹妹,算了,反正她也不想嫁,繼續低調。 什麼?自己強的居然是北溟世家的小少爺,人家要報仇...
116.6萬字8 23562 -
完結480 章
首輔家的美食小辣妻
現代女強人,21世紀頂級廚神,一朝穿越成了軟弱無能受盡欺負的農婦,肚子裡還揣了一個崽崽? 外有白蓮花對她丈夫虎視眈眈,內有妯娌一心想謀她財產? 來一個打一個,來一雙打一雙,蘇糯勢要農婦翻身把家當。 順便搖身一變成了當國首富,大將軍的親妹妹,無人敢動。 但是某個被和離的首鋪大人卻總糾纏著她...... 寶寶:娘親娘親,那個總追著我們的流浪漢是誰呀? 蘇糯:哦,那是你爹。 眾侍衛們:...... 首鋪大人,你這是何必啊!
90.3萬字7.73 79420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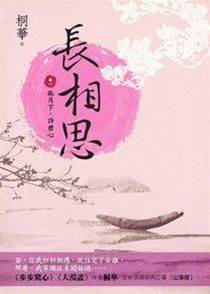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連載617 章

一別兩寬,將軍自重,妾身想獨美
蘇明妝雪膚花貌、香嬌玉嫩、美艷動人,長出了令所有男人垂涎欲滴的模樣,然,卻被父母生生慣壞,成了眾人避之不及的刁蠻任性、無法無天的惡女。一次偶然,她被年輕俊美的安國公救下,便死活要嫁給對方,甚至不惜編排自己被輕薄,令潔身自好的安國公名聲掃地,一番撕破臉、甚至驚動皇上的鬧劇后,終于如愿出嫁。 但新婚那日,她做了個夢,夢見出嫁三年,安國公沒碰她一下。 為了報復安國公,給他戴綠帽子,認識了貌美的錦王…做盡荒唐事。東窗事發后,安國公提出和離。 和離后,她聲名狼藉,被京城官家夫人們排擠,而她為了報復這些女人,她勾引他們夫君……做了更多荒唐事,最后得花柳病而死。 可謂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爛。 反觀安國公,則是與英姿颯爽的將門女子顧姑娘興趣相投、惺惺相惜,兩人還共同出征,成婚后也是婦唱夫隨,羨煞眾人。 顧姑娘的名聲有多好,她的名聲就有多臭。 顧姑娘和安國公的婚姻多美滿,她與安國公的婚姻便多諷刺。 她如夢初醒,發誓自己人生絕不能那麼荒誕,不能把好牌打爛。 但睜開眼,發現自己在大婚夜……錯誤已釀成。 安國公連蓋頭都沒掀,便棄她而去。 蘇明妝心想:一切還來得及,萬不要作妖,做好自己,靜靜等待和離……
110.7萬字8 203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