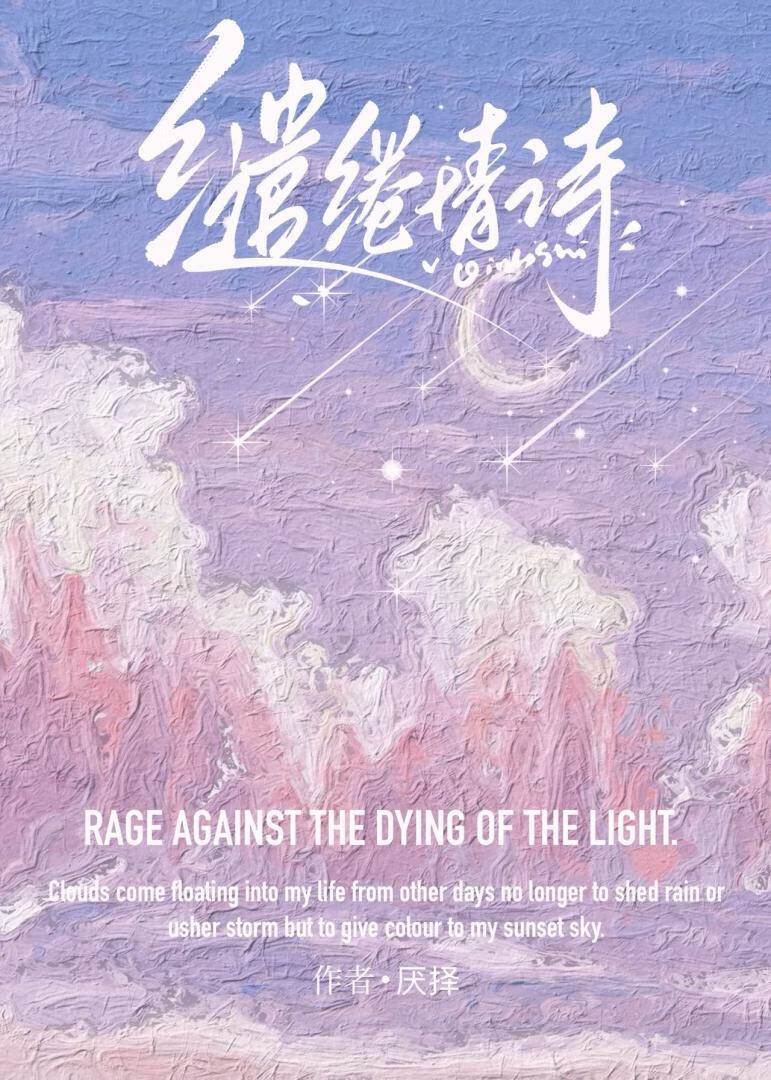《不斷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 第100章
這番言論話糙理不糙,白曄猛地往里灌了口水,又補充道:“退一萬步講,就算我真的慘了那人,到死都在打,可算什麼?只不過是生活里可有可無的調劑品啊!沒了它,我照樣可以步步高升、家財萬貫、飽萬人敬仰——誒嘿,滋滋兒。”
簡而言之,他不覺得謝逾對周倚眉的歉疚能造出如此龐大的幻境,現實不是全員腦的話本子。
孟訣沒反駁,順著他的意思接話:“不知依白道友所看,這浮屠境的因是何緣由?”
“我覺得吧,謝逾肯定恨死周倚眉了。”
白曄眼底盡是勝券在握的神采,語速越說越快:“你們想啊,他雖然年與相,可那畢竟是很久之前的事。這時間一年一年地過,無論多麼濃烈的,都難免被磨得只剩下一個薄殼——那兩人僅僅是這樣的,而周倚眉非但想要殺他,還將謝逾關進暗無天日的煉妖塔,你們說,這執念夠不夠重?”
寧寧笑了:“所以你覺得,謝逾想要殺掉周倚眉報仇。”
“對啊!”
白曄應得毫不猶豫:“這不是符合他格嗎?睚眥必報的小人。”
“但如果謝逾真想殺,在這浮屠境里,他曾有很多手機會,不必非得等到報仇的這一刻。”
裴寂沉聲開口,眼底是化不開的暗:“他至今沒周倚眉,說明心中尚有溫存。”
這兩方各有各的理由,也各有各的不合理之,房屋一時陷沉默,忽然響起寧寧清脆的嗓音:“哇,你們快看!周小姐出發了!”
于是在場幾人紛紛側過頭。
寧寧在百花深的姑娘手里得到過一份視靈,不久前與周倚眉談話時,順手將它放在了周小姐肩頭。
Advertisement
仙魔大戰之時,這玩意兒尚未被研發。因此就算周倚眉察覺到不對勁,也不會對它多麼上心,頂多覺得路過了不知名蚊蟲,與報仇比起來不值得注意。
“既然咱們討論不出個所以然,”寧寧指了指面前的圓鏡,“不如先看看劇走向?”
說罷半垂眼睫,凝神看向鏡面上的影子。
形纖瘦的白子立于門前,仰頭向狂浪翻涌的天際。
疊的烏云恍如變幻無常的鬼面,疾風像饕餮吞吃的聲音。
的確是個好天氣。
周倚眉沒做任何準備,不過是將稍顯凌的發重新束起,匆匆洗了把臉,便頭也不回地出了門。
=====
顧昭昭在整理帶去鸞城的行李時,忽然聽見門外的腳步聲。
以為那是侍奉于側的丫鬟,低著頭繼續整理:“何事?”
只要熬過今天。
今日一過,待與謝逾一道前往鸞城,徹底擺崇嶺這是非之地,顧昭昭,就能飛上枝頭變凰。
魔君之妻。
一想到這四個字,就止不住角上揚。
其實打從一開始,從沒想過謝逾能有這麼大出息,之所以暗自借了小姐的功勞,只因為他生有一張漂亮的臉。
哪怕遍鱗傷、瘦骨嶙峋,年的眉眼也能在剎那之間令面紅心跳。
只可惜謝逾對高不可攀的周大小姐深種,對從未生出毫興趣。
充斥整個心口的嫉妒,應該就是自那時而起。
周倚眉擁有人們的一切,絕容貌、出骨、無懈可擊的家世,以及為數眾多對死心塌地的男人。
顧昭昭不甘心。
即便謝逾不喜歡,有的是法子他上鉤。
于是開始日復一日地編織謊言。
Advertisement
周倚眉心疼謝逾,礙于周家眼線,只能托付邊的侍為那小奴隸捎去傷藥和糕點。
顧昭昭拿著籃子悄悄跑去見他,紅著臉告訴滿臉戒備的年:“你別怕,這是我特意為你準備的藥膏……你的傷還痛嗎?”
一天又一天,一遍又一遍。
謝逾看的眼神越來越和,偶爾會向喃喃提起,為何周小姐總是對他不冷不熱,從未來看他一眼。
后來謝逾向周倚眉提出私奔,顧昭昭毫不猶豫告了。
周大小姐被囚,謝逾被打得半死不活。
而走到年邊,出一滴眼淚:“你真傻,周小姐那樣的人,怎會心甘愿同你離開?就在今早,還向我嘲諷過你的無能無知……把一切都告訴老爺,今夜注定不會來了。”
謝逾的兩只眼睛都是紅,一眨不眨地著。
顧昭昭繼續告訴他:“你走吧,若是來日還記得我,便回來崇嶺看看我。”
在那一瞬間,年眼底的冷漠土崩瓦解,彌漫開淺淺水霧。
知道,自己功了。
誰能想到,謝逾竟會為魔君呢。
眼看曾經無比驕傲的周倚眉從云端跌落云底,而一步登天,為了陪伴在魔君旁的人,那些滋生多年的妒忌終于煙消云散,顧昭昭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活。
只有一點。
謝逾似乎仍對周倚眉舊未了,哪怕口中說得多麼厭惡,可眼睛騙不了人。
等到去往鸞城,就可以與周大小姐永遠說再見了。
顧昭昭心頭歡喜,本打算繼續收整行李,卻覺得不大對勁。
方才進屋的那人沒說一句話,只是靜靜站在門口,不知是否正在看。
口一跳,倉惶抬頭。
映眼簾的,是一張再悉不過的臉。
Advertisement
周倚眉。
顧昭昭覺不太妙,往后瑟一下。
居然連說話的勇氣都不復存在,磕磕好一會兒,才破了音地驚呼出聲:“你、你想干什麼?”
沒有忘記,周倚眉曾經是個骨卓絕的劍修。
只可惜在的慫恿之下,那只拿劍的右手被謝逾生生折斷。
“你別想打什麼歪主意!若是傷了我,謝逾定然饒不了你——侍衛呢?丫鬟呢?都去哪兒了!”
周倚眉沒理會的大喊大,手中白一現,出現一把鋒利長劍。
孟訣緩聲道:“以氣化劍,這位小姐修為不低。”
再看窗外,雖然還未到傍晚,天空卻已經全暗了。
烏云聚龐大的漩渦,沉沉倒掛在天幕上,仿佛要將所有亮吞噬殆盡,空留沉悶且單調的黑。
也因此,當月般的雪白劍意凜然涌,如洶洶雪瀑映亮子側臉時,勾勒出的殺氣才會像方才這般冷冽而瑰麗。
這人一定是瘋了。
竟是……以左手拿著劍的,
顧昭昭被嚇得瑟瑟發抖,周倚眉則自始至終面無表,向時不像在看活。
像在看一塊惡心至極的垃圾。
劍氣嗡鳴,白修上前一步。
顧昭昭還想求饒,小腹卻猝不及防被劍氣猛地一撞,渾劇痛之下,噗地從口中吐出鮮。
周倚眉懶得同多話,語氣極淡:“安靜。”
不想聽見這人的聲音。
顧昭昭哭了淚人,想道歉求饒卻不敢,只能一邊發抖一邊掉眼淚。
而那提著劍的瘋人一把提起領口,不由分說將顧昭昭往屋外拽。
哪敢反抗,只能跟著周倚眉一步步往前。
府邸里的侍從丫鬟皆昏昏倒地、沒了意識,顧昭昭看得心頭大駭,開始盤算如何能盡早讓謝逾發覺此等慘狀,只有他能治治這瘋——
不對。
兀地瞪大眼睛。
周倚眉拽著去的方向并非別,正是謝逾的臥房。
約有了預,自己接下來會遭遇什麼。
“不……求求你,不要!是我錯了……!”
下意識想要求饒,瞥見對方淡漠的臉孔后狠狠一咬牙,啞聲道:“你真以為他會信你的鬼話?待會兒謝逾見我傷,準會立馬殺了你!”
周倚眉沉靜如死水的臉上,終于出現了一抹笑。
充滿了嘲笑、不屑與懷疑的笑,冰冷如刀,仿佛在一字一頓地問:“你確定?”
顧昭昭不確定。
知道謝逾對周倚眉懷有特殊的,恨織,最是人癲狂。
隨即便是破門而的砰響,當還在為那道眼神心驚跳之時,周倚眉已經踹開了謝逾的房門。
而正如所料,房屋里的男人微微一怔,并沒有立刻出手。
謝逾終究還是對周倚眉心存不忍。
“阿逾,救我!”
顧昭昭來不及細想其它,涕泗橫流地扯著嗓子喊:“瘋了,周倚眉——”
話音未盡,小腹之上又是一陣劇痛,花跟旋轉花灑似的噴出來。
——周倚眉竟然敢當著謝逾的面傷!
謝逾對顧昭昭好歹有幾分,見狀蹙眉怒起,然而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被周倚眉冷聲打斷:“上前一步,我會殺。”
沒說謊,長劍架在顧昭昭脖子上,劍修殺人不過轉瞬之間。
兩張對峙,場面陷僵局。
“說。”
周倚眉面無表:“當年為他準備傷藥的是誰?”
就知道瘋人會來這一出!
顧昭昭目眥裂,用抖不已的聲線大聲喊:“我……是我!阿逾救我——啊!”
一縷劍氣毫不留穿過右手手掌,劇痛難忍。
“最后一次機會。”
周倚眉的語氣依舊沒有起伏:“當年為他準備傷藥的是誰?”
顧昭昭一邊流眼淚一邊干嘔,快哭吐了:“我、我說!求你別殺我嗚嗚嗚……我全都說!是小姐,是小姐準備好一切,托我去送的!”
謝逾渾猛地一震。
周倚眉微微抬起下,仿佛在討論某件再普通不過的小事,口吻里甚至帶了幾分慵懶意味:“繼續。”
謝逾那廢男人就靠不住!
顧昭昭氣得牙,迫于威脅只能繼續往下說:“所有東西……都是小姐準備的,我、我撒了謊……我愿意做牛做馬來贖罪!小姐饒了我吧!”
脖子上的長劍更靠近了一些,惹來生生的疼。
周倚眉:“繼續。”
“私奔……私奔也是我告的!對不起對不起,都是我的錯!”
顧昭昭不敢看謝逾的眼神,低頭死死盯著地板,即便如此,還是到一陣覆蓋而下的濃郁殺氣。
屬于魔族的殺氣。
周倚眉對的聲淚俱下與謝逾的驚駭皆是置若罔聞,淡聲道:“你還有什麼話想說麼?”
沒有殺!
顧昭昭的眼瞳瞬間亮起來:“小姐,求你饒了我吧!我愿意用這一輩子來補償,你不要殺我,好不好?”
周倚眉:“哦。”
周倚眉:“忘了說,這是你的言。”
顧昭昭的臉本來就糟糕頂,聽聞此言,立馬變得比吃了蒼蠅更惡心。
本來是想破口大罵的。
然而橫在脖頸的長劍白倏然,疼得渾發麻,大腦停滯,什麼也記不起來。
顧昭昭頹然倒在了地上。
周倚眉抬眸瞥向不遠的男人,拭去劍上跡斑斑:“清楚了麼?”
天邊的亮已然盡數消散,在鋪天蓋地的幽寂里,謝逾面如死灰。
而跟前眉目清絕的白修仍在自顧自繼續說:“藥是我送的,功法我給的,請是我求的——你難道就不曾懷疑過,一個侍,哪有那樣大的能耐?”
他怎會未曾懷疑,顧昭昭的話里有太多含混不清的貓膩。
可一旦順著那個思路想去,背后的真相讓他畏而卻步,不敢深思。
——他究竟做了些什麼?
俊無儔的青年渾抖著后退一步,雙目猩紅。
他在心底一遍遍問自己:謝逾,你究竟做了些什麼?
謝逾自出生起,就注定沒有未來。
一個份低微的奴隸,打罵盡是家常便飯,沒有人愿意施舍善意的眼神。
周家的爺小姐們猶如遠在天邊的月亮,想要見上一面都難,以他的份,更不可能有毫接的機會。
想來他與周倚眉的相識極為俗套,外出賞花的小姐將玉佩落在路旁,奴隸年將它拾起,懷揣著跳不已的心臟朝靠近。
猜你喜歡
-
完結24 章

偏執替身
一場車禍,令蒙雨喬完全不記得過去的事,醒來被告知有一個帥到讓她屏息、臉紅心跳的舞蹈家老公。和陌生的“老公”重新戀愛是什麽感覺?壁咚親吻擁抱,為什麽她覺得老公好像有一點冷淡欸,她要好好學習怎麽撩他。在相冊裏意外看到了兩人少年時的照片,什麽,那個和老公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居然不是他?事實讓蒙雨喬震驚,她是個壞女人嗎?她才知道,原來她根本不愛他,嫁給他隻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替身,對著他的臉永遠懷念她逝去的戀人。但現在她的心好像已經……就在她想對他表白時,明明已經死去的戀人卻又忽然重新站在了她麵前?過去和現在,她該如何選擇?
12.7萬字8.18 1075 -
完結66 章

貴妃二嫁
國公府嫡女韓千君,從小養尊處優一身榮華富貴,十六歲時更是一步青雲,進宮成了貴妃,開掛的人生羨煞了旁人,但老天爺自來公平,一年後,皇宮裏的一頂大轎原封不動地將其送回國公府,從此成了無人問津的棄婦。 韓家主母愁白了頭,以陪嫁爲誘替其物色下家,長安城裏續絃的,納妾的紛紛上門。 韓千君走投無路之下,相了個教書先生。 沒錢沒關係。 前夫給了她一筆可觀的安置費,她養得起。 所有人都以爲韓千君這輩子完了,直到見到了那位教書先生的真容,昔日等着看她被天爺公平相待的衆人:老天爺從未公平過。 長安城首富辛澤淵,前太傅辛家的大公子,生得玉樹臨風,還是京城有名的才子,奈何一雙眼睛長在了頭頂上,誰也入不了眼。 誰曾想竟找了個二婚。 家中姐妹都道韓千君使了見不得人的手段才攀上了辛家,只有她自己知道這門親事來得尤其容易。 那日她拿着自己的嫁妝前去扶貧,“先生不要多想,我並非那等威逼利誘之人,對先生絕無所圖。” “你可以圖。” 韓千君盯着他英俊的臉,在他極爲鼓舞的目光下,終於鼓起了勇氣,“那先生能娶我嗎?” “可以。” 文案:國公府嫡女韓千君,從小養尊處優一身榮華富貴,十六歲時更是一步青雲,進宮成了貴妃,開掛的人生羨煞了旁人,但老天爺自來公平,一年後,皇宮裏的一頂大轎原封不動地將其送回國公府,從此成了無人問津的棄婦。韓家主母愁白了頭,以陪嫁為誘替其物色下家,長安城裏續弦的,納妾的紛紛上門。韓千君走投無路之下,相了個教書先生。沒錢沒關系。前夫給了她一筆可觀的安置費,她養得起。所有人都以為韓千君這輩子完了,直到見到了那位教書先生的真容,昔日等著看她被天爺公平相待的衆人:老天爺從未公平過。長安城首富辛澤淵,前太傅辛家的大公子,生得玉樹臨風,還是京城有名的才子,奈何一雙眼睛長在了頭頂上,誰也入不了眼。誰曾想竟找了個二婚。家中姐妹都道韓千君使了見不得人的手段才攀上了辛家,只有她自己知道這門親事來得尤其容易。那日她拿著自己的嫁妝前去扶貧,“先生不要多想,我并非那等威逼利誘之人,對先生絕無所圖。”“你可以圖。”韓千君盯著他英俊的臉,在他極為鼓舞的目光下,終于鼓起了勇氣,“那先生能娶我嗎?”“可以。”1、自認為很聰明的顏控小白兔VS看起來很人畜無害的大灰狼。2、雙c2、古風後宅感情流。接檔文求預收:《非富即貴》錢銅,人如其名,揚州第一首富千金。滿月酒宴上,算命的替她批了一命。——此女將來非富即貴。錢銅不信。俗話道:富不過三代,窮不過五服。錢家到她這,正好第三代。得知家中打算以金山為嫁,將她許給知州小兒子後,錢銅果斷拒絕,自己去碼頭,物色了一位周身上下最寒酸的公子爺,套上麻袋。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她打算犧牲自己,嫁給一個窮小子,以此拉低外界仇富之心。—當朝長公主的獨子,謝元縝,三歲背得三字經,十歲能吟詩作詞,十六歲通曉四書五經。文武雙全,少年成名,自認為達到了人生巔峰。在替皇帝日夜賣命四年後,他又得來了一個任務。揚州富商猖狂,令他微服徹查。前腳剛到揚州,後腳便被一條麻袋套在了頭上。再見天日,一位小娘子從金光中探出頭來,瞇眼沖他笑,“公子,我許你一輩子榮華,怎麽樣?”初見錢銅,謝元縝心中冷笑,“查的就是你!”再見錢銅:“奢靡無度,無奸不商,嚴查!”一月後:逐漸懷疑人生。半年後:“錢銅,我的腰帶呢......”新婚當夜,謝元縝在一堆金山裏坐到了半夜,終于提筆,給皇帝寫了一封信:局勢複雜,欲求真相,故外甥在此安家,暫不回朝了。文案寫于2024/09/12,謝絕借鑒,必究。內容標簽:情有獨鐘天作之合爽文輕松韓千君辛澤淵接檔文《非富即貴》求預收呀~一句話簡介:(正文完)先生我威逼利你誘成嗎立意:相信未來,人生處處有驚喜。
29萬字8 2428 -
完結156 章

男友雇京圈太子親我,怎麼后悔了
【豪門世家+男二追妻火葬場+爽甜+反轉+男主又爭又搶】阮梨想告訴未婚夫,她臉盲痊愈的消息。 卻聽到他和兄弟們打賭: “誰能假扮我睡了阮梨,攪黃這門婚事,我的跑車就送誰。放心,她臉盲。” 阮梨:還有這好事? 當晚,她睡了清貧校草時郁。 可每當她要和未婚夫攤牌、索要跑車時,身后總有一道陰濕的視線,似要將她生吞活剝,拆骨入腹。 * 時郁出身于京圈傅家,克己復禮。 直到阮梨的出現。 她頻繁把他錯認成未婚夫,親了又親。 人美,聲甜,腰軟。 就是眼神不好,愛上了室友江肆言那個浪蕩子。 每次盯著他們的相處,數著他們說話的次數,時郁嫉妒得眼睛發紅。 后來,他開始假扮江肆言,只為留在她身邊。 * 江肆言拜托室友時郁: “好兄弟,阮梨太黏人,你扮成我,應付一下她。放心,她臉盲。” 室友做得很好。 即便他們二人同時出現,阮梨也以為時郁才是她的男朋友。 安靜乖巧地跟在時郁身邊,不再黏著他。 他很滿意。 直到那夜,雷雨大作,攪動春水。 他提前回到寢室。 卻見室友聲音低啞,把阮梨按在了腿上,輕哄磨吻: “寶寶,叫我的名字。” “時郁……” “老婆,今天你和他說了九句話,所以還有八次。” . ◆雙潔,1V1 ◆“玫瑰不必長高,戀者自會彎腰”
25.8萬字8 50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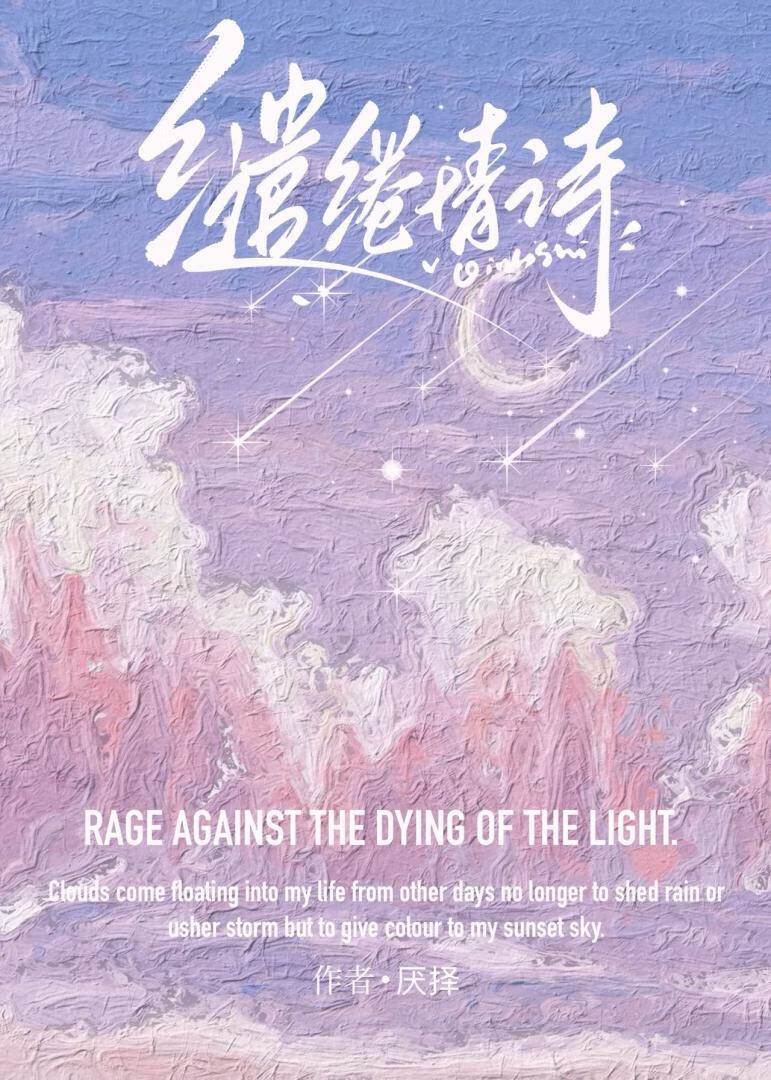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