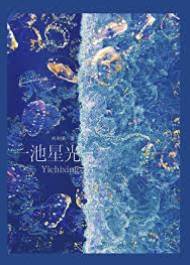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深愛刻骨:賀先生,請簽字》 第一百二十章 我沒打算變性
向晚不了萌妹子撒,最後被磨泡,還是答應了。
三人一起往病房走,任小雅整個人幾乎掛在向晚上,一直嘰嘰喳喳沒停。
鍾宇軒往兩人上瞥了好幾眼,臉越來越難看,最後他黑著臉走過來,生生把任小雅從向晚上拽下去了。
“你幹嘛呀?”任小雅瞪。
鍾宇軒推了推金邊眼鏡,一本真經回答,“你太胖了,都快把向小姐倒了。”
“!!!”任小雅眼鏡猛地瞪大,張兮兮地問向晚,“是真的嗎?”
向晚看了眼一臉敵意的男人,若有似無地歎了口氣,點了下頭。
元氣任小雅見此,瞬間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一步三歎氣地跟在兩人後,倒是沒再整個人掛在向晚上。
三人進了病房,寬敞明亮的病房瞬間多了幾分人氣。
賀寒川坐在病床上,目越過鍾宇軒落在向晚上,閃了閃,隨後神態自然地收了回去,“你怎麽來了?”
“代表廣大群眾來看看你死了沒有。”鍾宇軒走向桌子,在保溫桶那兒嗅了嗅,“從哪兒買的湯,聞著還不錯。”
碗裏的湯沒,還熱著,他端起來喝了兩口,“喝起來也不錯。”
賀寒川睨了他一眼,“狗鼻子都未必比你靈。”
Advertisement
“多謝誇讚,這是你嫉妒不來的。”鍾宇軒說話的功夫,又喝了兩口,“我怎麽聽夢蘭說差點紮到脈,你對自己下手也這麽狠啊?”
賀寒川沒出聲,隻是掀起眸子,看向向晚。
向晚恍若未覺,低垂著眸子避開了他的目。
將兩人的小作收在眼底,鍾宇軒嘖嘖兩聲,放下手中的碗,有幾分不懷好意地說道:“其實紮大沒有紮你老二管用,你怎麽……”
賀寒川的目太有迫,他咳了一聲,沒繼續說下去。
一直在向晚後的任小雅突然出頭,語不驚人死不休:“對啊,男人的睪丸痛比其他地方都要強烈,不用紮,你自己擰一下,應該就……唔唔唔!”
鍾宇軒鐵青著臉走到跟前,捂住了的,“你給我閉!”
向晚安安靜靜站在一旁,沒有參與幾人的對話。
“我沒打算變。”賀寒川涼涼瞥了鍾宇軒一眼,“你要是想變,我很樂意提供手資金。”
鍾宇軒,“……”
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賀寒川的“好意”。
這個話題揭過去,任小雅又慫地到了向晚的後,小聲跟抱怨,“每次大冰山笑得時候我覺得沒好事,他不笑的時候,我也覺得沒好事。”
向晚漫不經心地嗯了一聲,專心看著地麵。
Advertisement
任小雅誇張地全打了個哆嗦,雙手環,碎碎念,“其實大冰山也不合適,他還是笑的,雖然笑得假的吧……哎呀,他在看我!!!他是不是聽到我說他了?!!”
一蹦三尺高,直接蹲在地上,整個人在向晚後。
向晚被這麽一折騰,下意識抬頭看向賀寒川,正好撞進他漆黑的眸子中。恍惚了一下,很快回過神,垂著眸子看地麵。
被他扔出來後,已經打算破罐子破摔了,但縱然語言行為比平時稍微放肆了些,心裏終究還是……怕他。
那種怕是深深刻在骨子裏,又經過七百多個午夜噩夢堆積而來的,恐怕這輩子都難以泯滅。
賀寒川收回視線,看向鍾宇軒,“你的眼不敢恭維。”
“嗬!”鍾宇軒冷嗤,維護徒弟兼未來朋友,“你眼瞎。”
賀寒川輕笑了一聲,淡淡道:“我眼瞎,所以找了你這麽一個兄弟。”
鍾宇軒,“……”
“師父,我們什麽時候走啊?”任小雅坐立不安,十分稽地蹲著走向鍾宇軒,聲撒,“要不你留在這兒陪大冰山,我跟向晚先去吃飯吧?”
眨眨眼睛,還時不時張兮兮瞄賀寒川一眼。
鍾宇軒被的慫樣氣樂了,“想先走?”
Advertisement
任小雅小啄米似的點頭。
“不行!”鍾宇軒壞笑著在丸子頭上狠狠了一下,欣賞著的表變化。
任小雅滿是憧憬的臉在聽到‘不行’兩個字時瞬間一片愁雲慘淡,站起,唉聲歎氣地走向向晚。
“你是不是不隻打斷了向晚的,還打斷了小雅的?怎麽這麽怕你?”鍾宇軒看著自家徒弟的樣子,又氣又樂。
聽此,向晚垂放在兩側的手一點點攥,那些刻意忘的場景不控製地在腦中回放,衝得口一陣陣發悶。
什麽也沒說,扭頭往外走。
任小雅從後麵拽住,時刻警惕著逃跑,“你去幹嘛呀?”
“我出去打個電話。”向晚了發疼的眉心,敷衍得找了個借口。
任小雅瞄了眼賀寒川,湊到耳邊悄聲道:“我也跟你一起出去,我保證,我出去後離你遠遠的,絕對不聽你打電話。”
向晚低低嗯了一聲,走了出去,任小雅小尾似的亦步亦趨跟在後。
等們出去後,鍾宇軒過去關上門,這才問道:“這次到底怎麽回事啊?說向晚勾引你,說向晚找你複仇,說你潛規則向晚……說什麽的都有,你怎麽還把自己紮進醫院了?”
“向宇在我喝的酒裏麵下了安眠藥和春藥。”賀寒川眉心皺了皺,很快鬆開,簡潔回答道。
“?”鍾宇軒既困又覺得好笑,還有些吃驚,“這麽不流的手段,你居然中招了?”
賀寒川撥弄著病服上的褶皺,抬頭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低下,“沒想到他會耍招,沒防備。”
向宇這人最討厭那些不流的小手段,看誰不順眼、要整誰從來都是正麵剛,從不玩的。
鍾、向兩家長輩好,但鍾宇軒跟向宇一向不對付,兩人互看不順眼。
“向宇一直腸子,中間連個小彎都沒有,你不設防也正常。”鍾宇軒推了下金邊眼鏡,笑道:“這二貨最近也不知道吃錯了什麽藥,跑到向氏集團混了個職位,還學人出去談生意,結果連合同都不會看,還被人騙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00 章

陌路婚途
結婚四年,老公卻從來不碰她。 她酒後,卻是一個不小心上了個了不得的人物。 隻是這個男人,居然說要幫她征服她的老公? excuse me? 先生你冷靜一點,我是有夫之婦! “沒事,先睡了再說。”
89.4萬字8 73159 -
完結2312 章

有孕出逃:千億總裁追妻成狂
夏時是個不被豪門接受的弱聽聾女,出生便被母親拋棄。結婚三年,她的丈夫從來沒有承認過她這個陸太太。他的朋友叫她“小聾子”,人人都可以嘲笑、侮辱;他的母親說:“你一個殘障的女人,就該好好待在家裏。”直到那一天他的白月光回國,當著她的麵宣誓主權:“南沉有說過愛你嗎?以前他經常對我說,可我總嫌棄他幼稚。我這次回來,就是為了追回他。”夏時默默地聽著,回想著自己這三年和陸南沉在一起的日子,才驚覺發現,她錯了!結婚三年,夏時愛了陸南沉十二年,結果卻深情錯付。種種一切,讓夏時不堪重負。“陸先生,這些年,耽誤你了。”“我們離婚吧。”可他卻把她關在家裏。“你想走,除非我死!”
207.6萬字8.33 330489 -
完結380 章

插翅難逃之督軍請自重
她,是為姐姐替罪的女犯。他,是殺伐果決、令人生畏的督軍。相遇的那一刻起,兩人命運便交織在了一起。顧崇錦從來沒想過,一個女人竟然成為了他最大的弱點。而偏偏那個女人,卻一心隻想逃離他。宋沐笙也沒有料到,一心隻想保護姐姐的她,早已成為了男人的獵物。他近乎瘋狂,讓她痛苦不堪。為了留住她,他不顧一切,甚至故意讓她懷上了他的孩子,可誰知她居然帶著孩子一起失蹤......她以為她是恨他的,可見到他一身軍裝被血染紅時,她的心幾乎要痛到無法跳動。那一刻她意識到,她已經陷阱這個男人精心為她編織的網裏,再也出不來......
64.9萬字8.18 8586 -
完結8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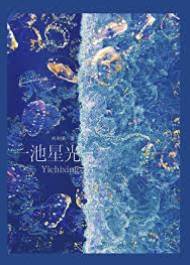
一池星光
夏星曉給閨蜜發微信,刪刪減減躊躇好久,終於眼一閉按下發送鍵。 食人星星【不小心和前任睡了,需要負責嗎?】 閨蜜秒回【時硯池???那我是不是要叫你總裁夫人了?看了那個熱搜,我就知道你們兩個有貓膩】 原因無它,著名財經主播夏星曉一臉疏淡地準備結束採訪時,被MUSE總裁點了名。 時硯池儀態翩然地攔住攝像小哥關機的動作,扶了扶金絲鏡框道,“哦?夏記者問我情感狀況?” 夏星曉:…… 時硯池坦蕩轉向直播鏡頭,嘴角微翹:“已經有女朋友了,和女朋友感情穩定。” MUSE總裁時硯池回國第一天,就霸佔了財經和娛樂兩榜的頭條。 【網友1】嗚嗚嗚時總有女朋友了,我失戀了。 【網友2】我猜這倆人肯定有貓膩,我還從沒見過夏主播這種表情。 【網友3】知情人匿名爆料,倆人高中就在一起過。 不扒不知道,越扒越精彩。 海城高中的那年往事,斷斷續續被拼湊出一段無疾而終的初戀。 夏星曉懶得理會紛擾八卦,把手機擲回包裏,冷眼看面前矜貴高傲的男人:“有女朋友的人,還要來這裏報道嗎” 時硯池眸底深沉,從身後緊緊地箍住了她,埋在她的肩膀輕聲呢喃。 “女朋友睡了我,還不給我名分,我只能再賣賣力氣。” 夏星曉一時臉熱,彷彿時間輪轉回幾年前。 玉蘭花下,時硯池一雙桃花眼似笑非笑,滿臉怨懟。 “我條件這麼好,還沒有女朋友,像話嗎?”
29.5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