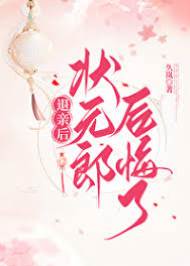《愛誰誰》 第70章 試法
當趙家遭逢大難時,朝堂也正麵臨一次巨震。聖元帝命太常卿草擬文案,意圖製甚至瓜分相權,而九黎貴族亦不甘心實權被漢人攬去,聯合幾位親王提出劃分人口等級的政略。
若在往昔,聖元帝或許會認真考慮,然而現在,他找到了切實有效的辦法製相權,也更明白民心向背的威力,又怎會倒行逆施,了國本?他當著滿朝文武的麵將奏折扔回去,隻問了諸位親王六個問題:一,此是不是中原腹地?二,此漢人幾何,九黎人幾何?三,漢人軍隊幾何,九黎族軍隊幾何?四,漢人將領幾何,九黎族將領幾何?五,漢人文臣幾何,九黎族文臣幾何?六,以勝多的戰役,這輩子你們打過幾場?妄圖以萬人碾億萬萬人,你們哪兒來的底氣?
諸位親王被問得啞口無言,狼狽敗走,漢人臣子卻對皇上更為敬服。
劃分熱的子平息後,聖元帝提出“二府三司製”,明麵上是為更有效快捷的理朝政,實際上卻將丞相的權力再三拆分,自是遭到丞相一係的激烈反對。然而他也不急,隻把太常卿草擬的章程分發給文武百,讓他們各自回去閱覽,慢慢斟酌利弊。
因丞相總攬軍政事務,以往武在朝堂上隻是擺設,目下見皇上竟要單獨設立樞院,讓他們把控軍務,自是求之不得,當就全站出來附議。又有丞相一係的員雖未表態,拿到章程後回家看了又看,再三思量,覺得這是一個出頭的大好機會,心裏也慢慢產生搖。
聖元帝毫也不著急,每日朝會必將此議案提出,命朝臣商討表決,第一日隻有武和帝師一係熱烈響應;第二日中立員站出來幾個;第三日又增多一些;第四日……漸漸的,不斷有人提出附議,或者主呈奏折,完善細枝末節,熬了一個多月,王丞相已是獨木難支,眾叛親離,不得不順應眾意,通過了“二府三司製”。
Advertisement
從此以後,丞相再不能獨攬朝政,淩駕於皇權,世家巨族與皇帝共治下的局麵慢慢破碎,終至消弭。聖元帝再拋出改革稅法與土地製度的議案時,反對聲浪果然消減很多,更有朝臣提出切實的方案供他施行,首要一點就是查人口,完善戶籍,再行分攤田地。
然而世家巨族到底有幾分底蘊,在嚴重犯他們利益的前提下不可能毫不反擊,竟放出流言,那些遊走鄉裏的胥吏非為查人口,卻為抓捕壯丁,送去修造類似於長城那般的建築,或者衝殺前線,擔當炮灰。聖元帝意效仿暴秦,施嚴刑峻法,行病民害民之策,又將戶稅改為丁稅,或二稅並行,大大加重了百姓負擔,隻為搜刮民脂民膏供自己樂雲雲。
聖元帝頒布的每一條法令,每一個政略,均被曲解得麵目全非,又以最快的速度傳播開來,引得民怨沸騰,象橫生,更有幾飽苛政盤剝的鄉縣揭竿而起,衝擊州府,意圖推翻皇權。
不過一夕之間,戰火就星星點點地燃起來,而聖元帝若是派出軍隊腥鎮,也就更應驗了那些流言,了濫殺百姓的暴君,或致全境崩塌。殺也殺不得,招安又招不來,聖元帝眉心的壑都增添幾條,當真是一籌莫展。
帝師與太常已分派儒生下去,每到一個鄉縣就唱念修法的好,民眾卻並不采信,反倒以為朝廷在糊弄他們,越發生了怨氣。
況越來越糟,若放任自流,魏國必然分崩離析;若強勢碾,百姓必然遭苦難,怎樣才能既快速又風平浪靜地解決這場危機了聖元帝的一塊心病。他總想找個人話,拿個主意,放眼四顧卻發現未央宮裏隻有穿堂冷風與昏暗燈燭,並無人能為他解憂。
Advertisement
“陛下您別喝了,明日還要早朝,睡晚了怕頭疼。您若是心裏不痛快,可去後宮排遣排遣,想必眾位娘娘很樂意伴您左右。”白福戰戰兢兢地勸。
聖元帝冷笑一聲,“排遣?們除了爭風吃醋,勾心鬥角,還懂什麽?朕的解語花不在此。”話落眸子一亮,急道,“快拿文房四寶來,朕要寫信。”
白福不敢耽誤,忙取來文房四寶,一一鋪開。
----
因民四起,朝堂巨震,葉全勇一案已擱置待查,趙陸離亦被無限期關押,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歸返。除了關素,趙家上下都有些焦躁,寫了信向趙瑾瑜求救,卻久久未能收到回音,隻能茫然坐等。
這日,關素正在書房裏作畫,忽然收到鎮西侯府送來的一封信,上書“夫人親啟”四字,下角落了忽納爾的款。眉梢微挑,興趣漸濃,拆開後一目十行地看完,想也不想就寫下答案,命人送返。
聖元帝本以為夫人要考慮許久才能回信,已做好等待幾日,甚至數十日的準備,卻沒料隻過了半個時辰,急足就匆忙宮,跪在前複命。他拆開信封,取出清香撲鼻的夾宣,卻見其上隻寫了七個行雲流水的大字兒——子當以試法。
以試法?怎麽個以試法?聖元帝兀自沉,苦苦思索,最終掌大讚,“妙啊,夫人果然是朕的解語花,賢助!來人,朕要親自去鄉裏探查民,不喬裝改扮,不白龍魚服,怎麽張揚怎麽來,必要鬧得人盡皆知才好。”
白福幾個連忙苦勸,直得口舌發幹也沒讓陛下改變主意,隻好傳令下去,準備攆與儀仗。
這一日,全燕京的人都知道皇上親自去近郊鄉縣安民眾,卻在途中驚了馬,翻了車架,倒一大片剛栽種的農田。為鼓勵農耕,保證糧產以供應軍隊,聖元帝曾頒布過一條律令,嚴任何人踩踏已種了秧苗的田地,違者杖十,罰銀五兩。
Advertisement
這回他自己犯錯,哪怕耕種田地的農夫一再表示無需賠償,卻還是命屬下在自己背部打了十杖,並親自將五兩銀子遞過去。當地員早就安排了十裏八鄉的百姓前來跪迎聖駕,將這一幕看得真真切牽
這場刑並非作假,當皇帝轉過時,竟有斑斑跡從布料裏出來,染紅了龍袍。然而他毫也不在意,語重心長地道,“修法當以護民民為本,民貴君輕,不但民眾要遵守律法,皇族更該以作則。在修法之初朕便過,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又豈能自食其言?近來種種謠傳,非為朕之本意,查人口,完善戶籍,不為抓捕壯丁,暴征財稅,隻為攤分田地,鼓勵開荒,供養百姓。朕想給大家一條活路,某些人卻為私鼓民,令無辜者枉死。人口戶籍排清楚,家中隻獨子一人可減輕賦稅徭役,更可免去征丁打仗;家中隻孤寡老人,不但無需繳納賦稅,還可獲得府周濟;家中人丁興旺,攤分的田地也就更多。你們隻看見戶稅改丁稅,卻沒看見占田改均田,以往隻能為世家巨族耕種田地,以獲得得可憐的口糧,現在卻能自己擁有田地,靠勤勞肯幹養活一家人。你們孰優孰劣?”
到此,他慨然長歎,語氣悵惘,“朕一心為民,實不願你們枉送一條命,枉流一滴鮮,故遲遲未派重兵碾全境。也希你們能開霧睹,破陳立新,共創一個太平盛世。”
俗話得好,寧當太平犬,莫為世人。人活於世,誰不願安安穩穩、太太平平?誰不願安居樂業,足食?沒被到絕境,誰又會拿命去拚?此前也有人走鄉串戶,大力宣揚修法的好,卻都及不上皇帝的以作則與真意切的自述。
莫飽讀詩書的文人已淚灑滿襟,拜服於地,就是那些大字不識的平頭百姓亦深,山呼萬·歲,直讚皇上謀世雄主,千古明君。
今日種種以最快的速度傳揚開來,□□的民眾冷靜了,開始打聽此前頒布的律法都有哪些,所謂的“均田”又是何意。帝師與太常親自遊走鄉裏,為民解,於是戰火一一熄滅,拿起刀槍落草為寇的壯丁紛紛跑回家,生怕慢上一步就沒能登記戶籍,導致家裏得幾畝田地。
不過半月功夫,這場有可能分裂魏國,顛覆朝堂的災難就這樣消弭於無形。聖元帝沒耗費一兵一卒,隻了些許皮之苦,但對一名驍勇善戰的將軍而言,這本算不得什麽。
與此同時,關素收到了忽納爾送來的謝師禮,一箱典籍與一張地契。早已聽陛下以試法之事,卻不以為怪,隻當忽納爾把自己的信呈給鎮西侯,鎮西侯又報予皇上,這才有了後續。
回禮很貴重,是價值連城也不為過,卻之坦然,著地契笑道,“皇上雖然出草莽,作風有些土豪之氣,然納諫如流,勇於擔當,稍加時日,必名副其實,堪為聖君。”
金子一麵附和,一麵將這番話默默記在心裏。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1051 章
將軍彆急:神醫娘子來沖喜
一朝穿越,竟成了丞相府的痴傻大小姐,被毁容不说,还被打包送给了一个中毒不醒的大将军冲喜。 好吧,那就顺手解个毒!只是…… 某神医:将军,解毒只要脱衣服就行,你脱什么裤子? 某将军:娘子,这天气炎热,为夫只是想凉快一下。 某神医:那将军脱我的衣服干什么? 某将军:娘子,这天气这般炎热,为夫是怕娘子热坏了!
120.7萬字8.18 75971 -
完結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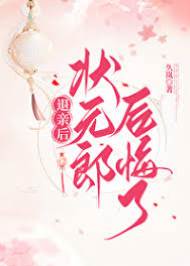
退親後狀元郎後悔了
沈棠的未婚夫是武威郡王府的二公子岑晏,狀元郎有才有貌,這門親事人人羨慕,但沈棠卻做了一個決定:退親。 兩家結親全是因爲岑家欠了沈家人情,實際上岑晏並不喜歡沈棠,他有他自己擇妻的標準。 沈棠就跟岑晏商量:“我可以讓兩家順利解除婚約,但你必須保證我未來的人身安全,另外,還需給我補償。” 正中下懷,岑晏一口答應。 後來,等沈棠找到解除婚約的辦法,正準備享受有錢有閒還有靠山的逍遙日子時,岑晏反悔了。 他說:“你要的安全,補償,嫁給我也一樣有,甚至還會得到更多。” 沈棠:……能不能有點契約精神啊?
14.7萬字8 8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