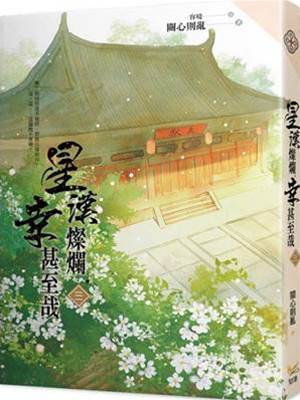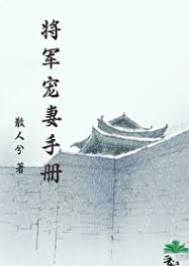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閨寧》 第112章 懲戒
是夜,三房的壽安堂一片寂靜,長房梅花塢的西次間里卻是燈火喧囂。
長房老太太的子仍不見起,如今瞧著模樣只像是茍延殘,也不知究竟還有幾日可活。因而這一回的事,誰也不敢去擾了,只請了長房老太爺來商量事。
這事目前尚算瞞得嚴實,知道真相的人除了三老太太跟陳氏外,也就只有大太太跟宋氏。所以能瞞著就繼續瞞著,鬧開了總沒有好。府里可還有那麼些個姑娘正在待嫁呢。
所以今夜,在座的只有謝大爺、謝元茂夫婦,並個謝二爺而已。
長房老太爺坐在上首,手掌攤開在炕幾上,掌心裡臥著兩顆玉球,手指一,就滴溜溜轉悠起來。
在場的知者只有大太太同宋氏,長房老太爺輕咳了兩聲,出聲詢問:「究竟出了何事,一從寺里回來就要商討?」
大太太先不接話,看向宋氏,宋氏卻只低著頭,似乎長房老太爺並沒有在問一般。大太太看著,不在心裡罵起宋氏來,平日里不顯山不水的,真到了時候,原也是個再狡猾不過的人。
原本,雖一道將人給召集了起來,但是可是準備讓宋氏站出來開口的。
可誰知,這會皮球落在了懷裡,竟是不得不接話了。
謝元茂幾個也都是不知的,這會都牢牢盯著呢。
大太太無法,皺皺眉,嚴肅地道:「昨兒夜裡,寺里出了件了不得的大事。」
「了不得的大事?」謝二爺人一樣的角,一聽這幾個字再看大太太面上的神,便覺得有不詳的預約約浮現出來。
大太太重重嘆了聲,角翕,卻沒有出聲,似十分難以啟齒。
長房老太爺急躁起來,將手中玉球往炕幾上一磕,肅然追問:「吞吞吐吐的做什麼,直截了當地將事說了!」
Advertisement
「是……」大太太這才一副勉為其難的模樣笑了笑,開口道,「我跟六弟妹,在三嬸房中發現了一個男.人。」
「什麼?」屋子裡幾個原本不知的人皆大驚失,長房老太爺手裡的玉球更是直接了手,飛快滾落於地,發出「嘭」的重重一聲響。謝元茂為三老太太名義上的兒子,驚駭得面如土,一把從椅上站起來,急急道:「大嫂莫不是瞧差了?」
大太太為難地看著他,「我一人瞧差也就是了,難道六弟妹也同我一道眼花了不?」
謝元茂就去抓宋氏的胳膊,焦慮地同尋求否定:「福,你也瞧見了?」
「那麼大一個活人,誰瞧不見?」宋氏沒有直接回答,輕輕反問了句。
謝元茂聞言,頹然鬆開手,子往後一栽,倒了下去。
這消息可真真是晴天霹靂,能瞬間將人給劈焦炭。
謝元茂驚得子都抖起來,剩下的幾人也沒好到哪裡去。
謝二爺最先回過神來,連聲問道:「那人如今在何?」
「已經鎖起來了。」大太太道,「假扮和尚進的寺,只怕是從外頭帶進去的人……」
此言一出,眾人更驚。
長房老太爺覺得面上發熱,想不通怎會出了這樣的事,自己那九泉之下的弟弟若知道的,豈不是要氣得從地下爬上來?死了這麼多年,竟還被戴了綠帽子,真是死也死不安生!
「那人留不得!」他略一想,便立即發話。
謝二爺卻遲疑了下,問道:「需不需拷打一番?」
究竟是何時同三老太太勾搭上的,可曾從謝家拿過什麼好,這一切的一切,才是謝二爺關心的要點。
但長房老太爺這會氣上心頭,哪裡有這心思,斷然否決道:「何須拷打!總歸是失了婦德,了家風,不嚴懲如何能行?」
Advertisement
言下之意,不管這是第一回還是第幾回,做了便是做了,絕沒有轉圜的餘地。
謝二爺聽明白了,自然不再問。
長房老太爺自己說完,卻又有些不甘心起來,問道:「這事會不會另有?」
「父親……」大太太紅著臉,「媳婦進去時,牀上的兩人可都還著子呢。」
長房老太爺瞪著眼,罵道:「***!」
大太太聽得臉更紅,又道:「阿蠻那丫頭子敦厚,臨行前要為三嬸點長明燈,可三嬸的那盞燈卻百點不著,只怕是驚擾了菩薩,菩薩也看不過眼了。」
「佛門清凈,做出這等傷風敗俗的事,菩薩沒當場要了的命去,便已是大慈悲了!老二你去,這便去,立刻將那人置了!」長房老太爺氣得頭疼,著額角,嘟嘟囔囔,「老三自個兒就是死在上的短命鬼,而今媳婦竟也是個差不多的貨……」
謝元茂在地上聽見了,忙撲過去,「老太太那邊要怎麼置?」
與人私通,乃是大罪。
長房老太爺惱得厲害,擲地有聲地道:「難道還有臉活著?」
半老徐娘,風韻猶存,又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紀,有一便會有二!這一回若放過了,難保何時就會出第二回,到那時,謝家難道要一齊葬送在手裡不?
長房老太爺焉會讓這樣的事發生,他冷下了聲音,趕謝二爺隨大太太下去將那漢子置了,轉頭又吩咐起了宋氏來:「老六媳婦,你且回去將壽安堂封了,對外只說老太太在寺里染了風寒,病了不宜吹風見人。」
眼下這時節不好立即就讓暴斃,那就暫且先擱幾日。長房老太爺又看向了謝大爺,瞇著眼睛道:「老大下去準備著,壽材壽,都先備妥當再說。」
Advertisement
「老六你也別孬了,同老六媳婦一道回去,謹慎些!」
謝元茂癡癡地從地上爬起來,面煞白,一副已經見了鬼的模樣。
宋氏頭一回見他的慫樣,心裡頭莫名煩躁起來,在長房老太爺面前勉強裝作相敬如賓的模樣,上前去扶住謝元茂,兩人一道往外走。
人散了,梅花塢里的燈卻一夜未滅。
謝姝寧從玉紫裡得知消息時后,很是鬆了一口氣。
以對長房幾位的了解,三老太太這一回怕是死定了。
可饒是如此,卻依舊覺得不解氣,反倒是越想越覺得氣憤,這些招數,原本可就都是三老太太自己想出來,準備用在母親上的。一想到那人醜陋又無恥的臉就恨得冷笑,不要臉的東西,竟還妄想從這要銀子,且等著吧!
大被蒙頭,裡喃喃喊著:「都死了也就是了,落得清凈……」
……
那廂大太太裡也就念叨著這樣的話,「死了也好,清凈。」
走在旁的謝二爺聽見了,悄悄問道:「大嫂,這事會不會有什麼蹊蹺?」
他素來謹慎,不敢輕易下定論。但這回,老爺子也並沒有說錯,不管怎麼樣,錯事做下便是做下了,哪怕是被人陷害,三老太太也休想。他心裡清楚得,可仍想再往深里探究一番。
偏生大太太一問三不知,聞言竟反問他,「二弟覺得裡頭有蹊蹺?難道還會有人特地尋個漢子來送到三嬸牀上去不?」
「這也並非全無可能。」謝二爺訕訕然道。
大太太蹙眉,語重心長地道:「場上的事我這做嫂嫂的自然不懂,可是二弟,這一回定然是你想多了。當時,三嬸可連一句辯解的話都沒有呢。」
「是嗎?」聽到三老太太被抓.后,竟是一句為自己辯解的話也無,謝二爺不有些發懵。
大太太頷首,走了幾步卻忽然道:「說起這個,我倒想起一事來,當日三嬸沒為自己辯解,反倒是指著六弟妹的鼻子罵了好一通難聽至極的話。」
夜風拂面,謝二爺長長吐出一口濁氣,有些話想說,卻不好就這麼說。
他這個做兄長的,總不好就這麼在沒有證據的況下懷疑弟妹。
但這事的確可疑。
他大步邁開步子,走到鎖了假和尚的屋子門前。
正要讓人開門,他忽然聽到後大太太輕聲問了句,「二弟,你近些日子可曾帶過小廝二門?」
府里誰都知道,他邊小廝最多,年紀大大小小,皆有。
他形微頓,笑了起來:「大嫂說笑了,好端端的怎會帶二門來。」
大太太也跟著笑了起來,「二弟莫怪,原是我多心了。」
兩人就都沒有再說話,一前一後走進了屋。
假和尚的仍舊堵得嚴嚴實實的,上被繩子捆得,手腳亦是。
謝二爺看一眼,鄙夷地移開視線,「罷了,留著也是禍患。」
這話一出,倒在地上的假和尚就急切地「嗚嗚」喚起來。
可惜他裡堵著東西,口中的話支離破碎,人聽不明白。
謝二爺正要喚人進來,卻忽然在他的話里聽到了幾個約約的字——八。
八?
他皺眉在腦中過了一遍,卻沒有什麼線索,遂要上前去扯了假和尚的汗巾子,卻不防大太太快他一步,將人喊了進來。
罷了,問也無意,至多也就是后宅婦人間的小小戰爭罷了。
謝二爺把玩著手上的白玉扳指,後退下去。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糖寵
裴瓊很擅長甜言蜜語,哄得家里的祖母、爹娘和哥哥們都最疼她。 太子殿下最冷清的一個人,也被她花言巧語哄地五迷三道的,違抗父命也要娶她。 可傳聞里千嬌萬寵的太子妃,平日里連顆糖都要數著吃。裴瓊看著自己小盒子里寥寥無幾的幾塊糖,可憐巴巴地算這個月還剩幾天,她要怎麼吃才能撐到月底。 夜色幽深,鴛鴦交頸。汗光珠點點,發亂綠松松。 裴瓊眼睫上掛著淚珠兒,轉過身去不理人。 太子冷著一張臉哄:糖糖乖,不哭了,明日讓給做荔枝糖水吃好不好? 【食用指南】 1.互寵 2.真的甜,不甜不要錢 3.架空文,一切都是為了撒糖,請勿考據
24萬字8.18 8266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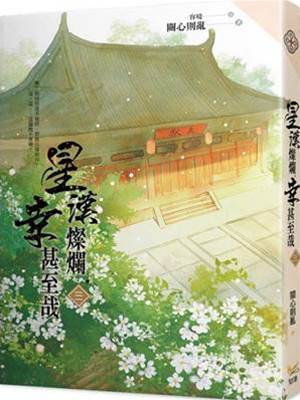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406 章

深宮劫:美婢難寵
沉默的承受著帝主給予的所有恩寵,她已無力去挽留清白,任由他在芙蓉帳下的狂妄。他是主,她是婢。從來只有他想的,沒有她能拒絕的。皇帝大婚,她卻要成為皇后新婢。
76.2萬字8 6169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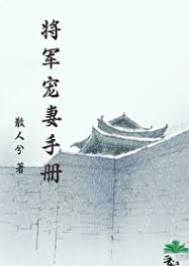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