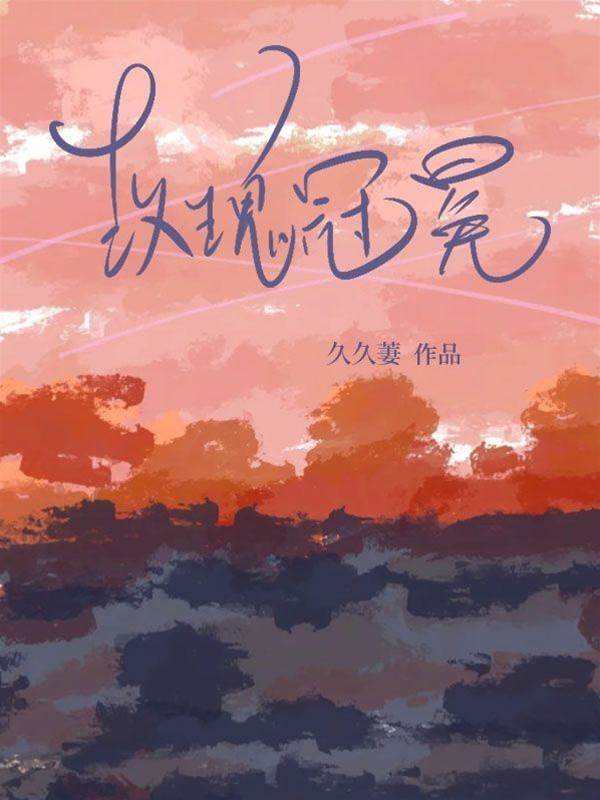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誰能不愛綠茶呢》 第49章 第49章
周聿注視著陳嫵輕的笑容。
不笑時,眼睛略有些圓,像是闖進叢林里的小鹿,左顧右盼,又堅定地朝著有的地方奔跑。
笑的時候,就像小鹿跳進溪水,溪水里漣漪瀲滟,倒映一彎月。
周聿結滾了滾,移開視線。
“裝修麻煩,許溯以前沒跟?”
陳嫵這才想起許溯來,肯定是太忙了,最近都沒記起他。
“裝修的時候他很忙。”
“沒記起許溯”這件事令陳嫵心底有種莫名的放松,故意給自己增加更多工作量,除了是為了學生,也有借著忙,借著時間忘掉許溯的意思。
原來也沒有那麼難。
“嗯,我不忙,有事隨時找我。”
“突突突突——”
裝修的聲音跟其后,周聿的那句話好像被沖擊鉆澆滅了,但又好像沒有,陳嫵應該是聽到了。
說是今天也會敲墻,但實際上時間已經到了。
再施工的話,噪音擾民。
裝修工時刻記得進度,想要再多敲一會兒,周聿點了點手表,和他們說明天再來。
裝修工看了看周聿的臉,嚨里嘆了一聲,“好,那明天我們早點來。”
陳嫵不用手,他就幫把裝修這種事捋了下來。
陳嫵記得上一次裝修,留下最多的印象就是難纏,哪像這一次,沒有拖泥帶水,六點一過,房間里就剩和周聿。
鎖好門,兩人先去樓下一層看了一看,儲柜里的禮盒沒有還留的,陳嫵還收到兩張紙,和三張明信片。
“歡迎新鄰居!”
“禮很好看,謝謝我們的新鄰居。”
陳嫵看著卡片,咧笑了一聲。
周聿凝著,不自地,也跟著彎起角。
突然陳嫵轉過了,周聿來不及收回笑意,稀奇,問他:“周聿,你在笑什麼?”
Advertisement
周聿著:“今天晚飯吃什麼?”
只要和周聿一起做飯,陳嫵瞬間連小工都當不上。
周聿說要回家一次,再過來的時候手里拎了一個袋子,陳嫵好奇,問是什麼,周聿笑了笑,沒說話。
他門路地套上圍,小兔子翹著絨絨的白小尾,左右晃。
周聿將食材清洗后,篤篤篤地切切片,陳嫵堅持自己一廚藝應該有用武之地,周聿隨手取下掛鉤上的鍋鏟地給,
“你來翻一下。”
曾經是大廚,現在可以做翻炒機。
周聿做菜時候潔癖現淋漓盡致,砧板切好蔬菜,要先刮洗一遍,換下一種蔬菜。綠油油的蔬菜在他手里可以被當做藝品。
陳嫵都能想到后期配聲:這雙白玉一般的手正在給青菜做馬殺,的菜葉在他的手中越發有了活力,撒上三兩顆晶瑩的鹽粒——
周聿接過手中的鍋鏟,大火放開,撲簌簌地炒出了菜香。
青菜不用炒太久,鍋里熱油滾三遍就能吃。
青翠滴,鹽味釋放出蔬菜清香。
陳嫵的手里被放上一小盤青菜,周聿低頭看:“去沙發坐會兒。”
陳嫵既“宜家宜室”之后又想到一個語,
“反客為主”。
廚房的香味越來越盛,陳嫵在等待間不爭氣地咽了咽口水,站在廚房門口,玻璃后邊,周聿正將一盤糖醋小排裝盤。
他垂眉,專注地將鍋里的湯淋在盤中最上頭的那一塊排骨上,隨后放下鍋,洗凈了手,用廚房紙巾干,抓了一把像是椒鹽又理論上覺不應該的調味料,三三兩兩地撒上。
周聿端起盤子,和玻璃門后的陳嫵對視。
陳嫵拉開廚門,周聿好似輕笑了一聲,沒有把裝滿了糖醋小排的盤子給,而是親自擺到客廳餐桌。
Advertisement
香味更濃郁了,周聿忽然轉,就見陳嫵正在一般地吸鼻子。
然后陳嫵就不了。
“陳嫵,我們沒有在玩木頭人。”
周聿從消毒柜拿了筷子,洗一遍,再熱水了,將碗一起遞給陳嫵,“了先吃,還有一個湯。”
陳嫵搖頭:“已經很麻煩你了,怎麼可以先吃。”
“趁熱嘗一嘗味道。”
周聿凝著,陳嫵只能筷子夾了一塊,咬了一口,像是沒回過味,又咬了一口,然后看向周聿:“比你們食堂的大廚做得還好吃。”
周聿:“我就當作是夸獎了。”
瘦相間的小排,悉的甘梅味。
陳嫵想應該是巧合:“周聿,你是問你們食堂大廚要了這道菜的菜譜嗎?”
“是我給他們的菜譜。”
“啊?”
周聿去了廚房,陳嫵愣了一下,跟了進去,周聿正在熬一小鍋番茄蛋湯,番茄多,蛋,吃起來肯定有點酸唧唧。
別人喜歡吃蛋花多的,陳嫵卻喜歡吃蛋花、番茄多的。
“我小時候經常吃這道。”周聿解釋,“長大了就自己做。”
陳嫵原本想問的心被了下去,周聿小時候,他們都知道他年時期過得不好,但小時候是怎麼樣的,他不說,他們怕讓他傷心,也從來不問。
陳嫵想要藏表的時候,親近的人都無法察覺開心還是不開心。
但直白的時候,又特別容易讓人一眼看出。
周聿瞧一眼,解釋:“不是我的親人給我做的,是一位好心人。初中家里出了點事,對方看我站在門口時間太長,給了我碗飯,后來一段時間,都會留我一碗。”
陳嫵沒想到是這樣的,見周聿神沒有不虞,
“這道菜是向好心人學的嗎?”
Advertisement
“嗯。”
“現在,你們還會見面嗎?”陳嫵想,如果有人在年的時候幫助,應該會在功名就之后回報對方。
但周聿卻只看著,他的眼眸漆黑而深邃,像是藏了睡前故事的湖泊。
陳嫵想,他可能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于是在周聿開口前,陳嫵善解人意地錯開視線,“湯要涼掉啦。”
周聿搬家之后,兄弟幾個說要來幫他暖房,他拒絕了。
周聿打開房間燈,冷清的房間布局哪怕裝了偏暖的白燈依然冷清。
客廳空空,沒有花植,除了生活必須的餐桌、沙發、電視,總而言比樣板房還要簡單。
26棟1601和1501的格局大部分一致,除了1601還多了一個閣樓,客廳有一道斜的樓梯,坡度不高,可以直上閣樓。
閣樓與loft不同,loft的閣樓很矮,人站不直。
公寓的閣樓就是整整一層,比樓下正常樓層的樓高還高一點。
周聿在頂樓按了一扇高閉、四四方方的窗,平時窗簾拉著。
天氣好的時候,能看見星空,周聿不怎麼看。
如果刮風下雨,打在窗玻璃上稀里嘩啦的,喜歡的人很喜歡,當做白噪音來催眠,不喜歡的人只覺吵。
周聿按窗的時候沒考慮自己,他想,也許呢。
等裝完了,他想,沒什麼也許。
他換下外,放進洗簍。
隨后走進書房。
書房是整個房間他最用心布置的地方,書架和桌子都是上好的紅木。書架上一半的位置擱每年最新出版的向書、專業書,另一半是整整齊齊的錄像帶,相冊還有畫冊。
他出一盤錄像帶,放進播放機里。
讀取的橫條慢悠悠地從左走到右,然后,一個灰的三角形出現在屏幕中央。
“跑不就慢慢走啦——”
陳嫵的臉出現在鏡頭里,正在好笑地著看不到臉的人的背,然后無奈地安對方:“有什麼好逞強的。”
大學時期的陳嫵束著馬尾,臉頰線條和,額頭白皙飽滿,臉小小的。
眼睛看過來,朝鏡頭笑了一下,眼睛像剛從春水里洗過的星星,“你看,周聿都要看你笑話!”
周聿挲著指節,也跟著笑。
“太熱了,想去海邊——”了一個懶腰,然后又很快自我拒絕,“不行,我要快點修完課程,考研究生。”
“你可以輕松一點。”
陳嫵想了想,笑起來,“不行哦。”
十五分鐘的錄像帶放完。
周聿在黑暗里微微坐了一會兒,然后,按了一個按鈕,錄像帶退出播放機,他把這一盤錄像帶放回盒子,盒子的側面記著錄像的日期。
周聿出一本信紙,這本信紙看上去已經撕了許多頁,整整齊齊地一整排撕開的痕跡。
拉開屜,取出一盒子彩鉛。
周聿下筆很慢,彩鉛在信紙上刮出沙沙的聲響。
在八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牽著他的手走進素描教室,溫地和素描老師說:“這孩子有一點畫畫天賦,我帶他來學學看素描。”
他學著老師教的樣子,跟著畫,等母親再來接時,老師夸他:“這孩子耐得下子,很聰明。”
展開畫紙,和他的父親說:“必須得學,你看小聿畫得多好呀。”
周聿紅了臉。
他那個后來賭錢、喝酒、最終折騰死自己的父親了后腦勺,重復著母親的話:“學,必須學!”
第二個屜放的是信封。
周聿折疊信紙,塞進信封。
他披上外,將信封放進兜里,經過30棟的時候往上了一,燈仍盈盈亮著。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263 章

偏執男主白月光我不當了
楚殷死後才知道自己是豪門文裡的白月光。 偏執男主年少時對她一見鍾情,執掌財閥大權後將她禁錮,佔有欲瘋魔。楚殷備受痛苦,淒涼早死。 再睜眼,她回到了轉學遇到陸縝的前一天。 “叮~學習系統已綁定!宿主可以通過學習改變垃圾劇本喲!”這輩子她不要再做短命的白月光,發奮學習,自立自強,這輩子逆天改命,最終揭開上輩子的謎團,拿穩幸福女主劇本。
37.9萬字8 10745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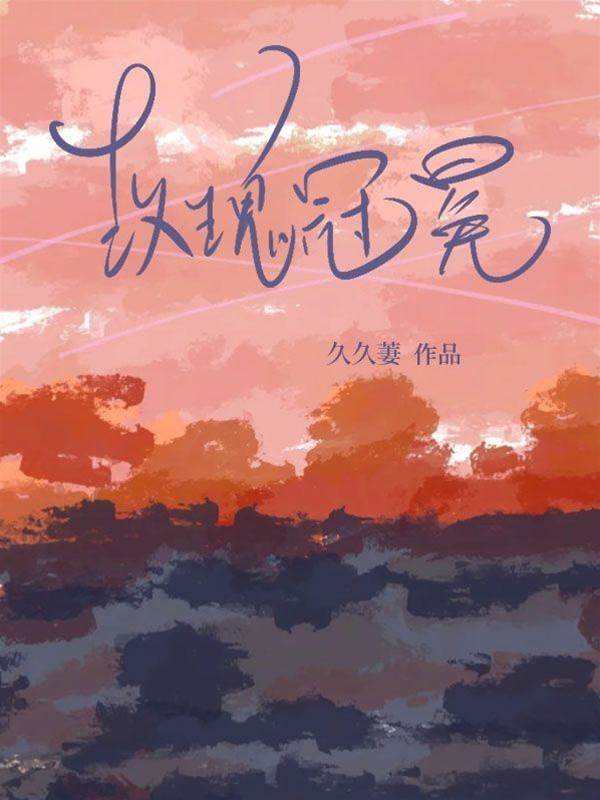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1063 章

四年后,前妻帶崽歸來虐翻渣爹
懷胎八月,他們第二次見面。 她以為他至少會關心關心孩子,卻沒想到他竟然要離婚,只因他們是商業聯姻,他對她毫無感情。 她希望他看在孩子的份上,至少等他們平安出生,可他卻無情的說:“你不要妄想我會接納他,他就不該來到這個是世上。” 四年后,她帶著天才兒子歸來,卻發現當年沒帶走的女兒,如今不但身患重病,還被渣男賤女一起虐待到自閉。 她憤怒的和他對峙,誓要搶回女兒。 他緊緊的抱住她,“老婆,我知道錯了!你別不要我……”
199.2萬字8 8573 -
完結261 章

驚呆!我親媽竟是帶球跑女配!
越蘇大學時見色起意,撿了一個男人。失憶,身材野,長得好。 后來,失憶的男人成了男朋友。 越蘇和他陷入熱戀,男人卻恢復了記憶,一朝成了京圈傅家太子爺。 他記得所有人,獨獨忘了她。 雪夜里,越蘇在樓下站了一晚,只為見他一面,卻等來了他的未婚妻。 越蘇心灰意冷,事業受阻,果斷退圈生娃。 四年后,她帶著孩子上綜藝,卻在節目與他重逢。 男人冷漠疏離,對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視若珍寶。 全網都在嗑他和當紅小花的CP,嘲笑越蘇不自量力。 卻在節目結束的某一天,狗仔拍到—— 那矜貴不可一世的傅家太子爺,將越蘇堵在角落。 低下頭顱,卑微乞求她的原諒。 * 要要做了個夢。 醒來驚呆,她媽媽竟是霸總文里的帶球跑女配! 她問小胖:“什麼是女配?” 小胖說:“白雪公主的惡毒后媽就是女配。” 要要:“女配的女兒呢?” 小胖:“那是小炮灰。” 要要不想成為小炮灰,督促媽媽努力賺錢,卻在綜藝偶遇便宜親爹。 便宜爹看著很有錢。 要要:“叔叔,等你死了,能把手表送給我嗎?” 傅西燼:“我不死也可以送你。” 要要:“還是等你死了再給我吧。” 傅西燼微笑,小棉襖還不算太漏風。 要要又問:“可以明天就送我嗎?” 傅西燼:“……”
50.2萬字8 147 -
完結143 章

透明的雪
盛衾從小性子溫和淡然,除了偷偷暗戀一個人多年以外。 做過最出格的事,莫過於在聖誕節的雪夜表白,將多年的喜歡宣之於口。 這次表白距離上次見宴槨歧已經有兩年多。 男人一頭烏黑的發變成了紅色,看上去更加玩世不恭。 他被一群人圍在中央,衆星捧月,人聲鼎沸中看向她,神色淡漠到似乎兩人並不相識,雪落在他的發頂格外惹眼。 等盛衾捧着那顆搖搖欲墜的心,用僅剩的勇氣把話講完。 四周幾乎靜謐無聲,唯獨剩下冷冽的空氣在她周身徘徊,雪花被風吹的搖晃,暖黃色的路燈下更顯淒涼狼狽。 宴槨歧懶散攜着倦意的聲音輕飄響起。 “抱歉,最近沒什麼興致。” 那一刻,盛衾希望雪是透明的,飛舞的雪花只是一場夢,她還沒有越線。 —— 再次重逢時,盛衾正在進行人生中第二件出格的事情。 作爲紀錄片調研員觀測龍捲風。 無人區裏,宴槨歧代表救援隊從天而降。 男人距離她上次表白失敗並無變化,依舊高高在上擁有上位者的姿態。 盛衾壓抑着心底不該有的念頭,儘量與其保持距離。 直到某次醉酒後的清晨。 她在二樓拐彎處撞見他,被逼到角落。 宴槨歧垂眸盯她,淺棕色眸底戲謔的笑意愈沉,漫不經心問。 “還喜歡我?” “?” “昨晚你一直纏着我。” 盛衾完全沒有這段記憶,呆滯地盯着他。 宴槨歧指節碰了下鼻子,眉梢輕挑,又說。“還趁我不備,親了我一下。” —— 雖不知真假,但經過上次醉酒後的教訓,盛衾怕某些人誤會她別有居心,癡心不改,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他卻步步緊逼。 有天被忽視後。 宴槨歧懶散地靠着車門,睨她:“看見了,不知道叫人?” “我覺得,我們不是可以隨便閒聊的關係。” 片刻後,盛衾聽見聲低笑,還有句不痛不癢的問話。 “那我們是什麼關係?” 盛衾屏着呼吸,裝作無事發生從他面前經過。 兩秒後,手腕毫無防備地被扯住。 某個混球勾着脣,吊兒郎當如同玩笑般說。 “之前算我不識好歹,再給個機會?”
33.8萬字8 1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