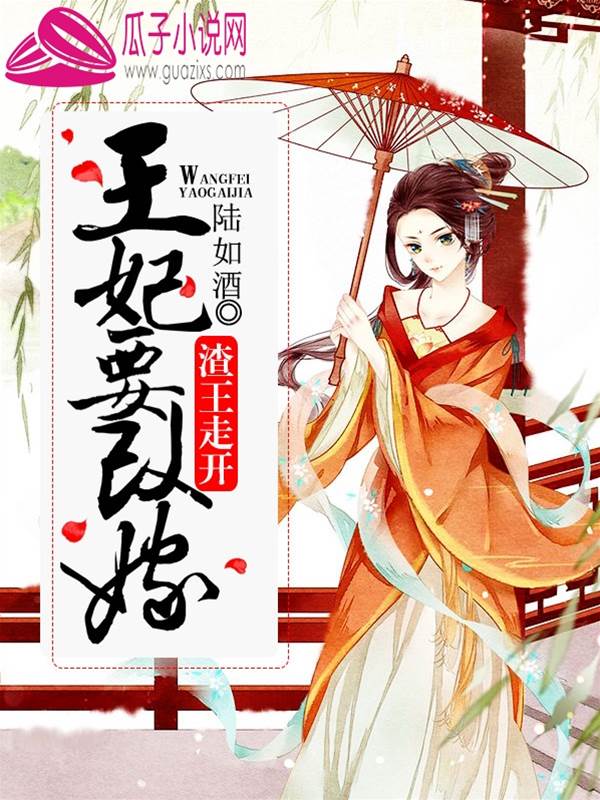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我是旺夫命》 第792章 可遇一心人,非死生,不可離
儀宮中,一常服的祁驍正圍著鐘璃打轉。
他叭叭說了半響,見鐘璃沒什麼高漲的熱,忍不住癟皺眉。
有些委屈的喊了一聲阿璃。
鐘璃聽見靜,再一看祁驍仿佛了莫大委屈的樣子,不住撲哧笑出了聲。
做了數十年的帝皇,時在祁驍的上留下了無數沉淀的痕跡。
他不說話站在那里,迎面而來的就是不怒自威的霸氣。
朝堂之上,無數人才倍出,俊才迭起。
卻始終無一人膽敢在祁驍面前放肆。
他用了十年,將大褚打造了自己設想中的樣子。
外攝非我之族,修清政嚴明。
十年前的戰痕跡在歲月的安下逐漸消散,整片大地重新煥發出了無限生機。
繁花盛世,就在眼前。
無數人口稱贊,百年盛世終得一見,縱然就是此刻赴死,也可安心含笑九泉,無愧列祖列宗之面。
然而在外霸氣十足的帝皇,在鐘璃面前,卻依然是多年前那個小傻子的德行。
輒就和孩子們置氣就罷了,還時不時的就跑來鐘璃跟前訴委屈,哼哼唧唧的,不像個傳說中無所不能的帝皇,倒像是個長不大的孩子。
鐘璃哭笑不得的嘆氣,語氣帶安。
“你說的好的,但是不現實啊。”
禪位給祁云宸自己帶著鐘璃出去玩兒,這想法未免也太離譜了。
祁驍聽了極為不滿。
“怎麼就不現實了?”
鐘璃好笑不已。
“宸兒才多大,你就想著撂挑子走人,若是他擔不起這擔子又該如何?你讓旁人怎麼看他?日后世人又怎麼評價你的過失?”
鐘璃膝下三子,大的兩個,不足十歲,就每日被祁驍拘著在勤政殿中旁聽。
先不說那麼大的孩子能聽懂多,總之,兩個小家伙是實實在在的在勤政殿中度過了不那麼愉快的年。
Advertisement
旁聽也就罷了,左右這擔子日后是要到孩子手上的,早些時候接也并非壞事兒。
可再早,也不能是這時候吧?
十四歲的孩子,在現代還在念初中,哪兒就能當皇帝了?
鐘璃覺得,祁驍異想天開了。
祁驍對此倒是不在意。
他漫不經心地說:“那小子慣會在阿璃面前賣弄癡憨,里卻是個實打實的油茬子,哪兒就真是什麼善茬?如今的場面他應付得來,阿璃不必擔心。”
祁驍花了十年時間將朝堂上下整頓一新,外也早就不復當年的婚論形。
只要祁云宸不是傻子,有這麼多人輔佐,他定然能撐起門戶。
話雖如此。
可鐘璃還是不贊同。
帝皇之尊聽著威風。
可實際上擔子也格外沉重。
祁驍都說辛苦的活兒,鐘璃暫時是真不忍心早早的就讓祁云宸接了過去。
左右祁驍是做慣了的,再多擔待幾年,讓孩子松泛松泛也無不可。
見不說話,祁驍忿忿不已,振振有詞。
“阿璃就是偏疼那臭小子。”
“我在這位置上磋磨著阿璃一言不發,讓那臭小子來試試滋味阿璃就舍不得了,這不是偏心是什麼?”
鐘璃無聲失笑,無奈道:“你都多大了?怎麼還跟孩子置氣?”
祁驍聽完更氣了,拉著鐘璃就不撒手。
“我怎麼就多大了?尋常人家十四五的人都快當爹了,他回家繼承家業怎地就了我這個當爹的不厚道?”
祁驍越說越來氣。
“我十四的時候已經上了好幾次戰場了,都說虎父無犬子,既是我的種,繼承個家業怎就不行了”
“他難不還能把這家底子給我敗了?”
聽他越說越胡攪蠻纏,鐘璃頭疼的了他的臉一下,嘆息道:“都說創業容易守業難,要是他真擔不起這擔子你又該如何?”
Advertisement
祁驍冷笑。
“我打斷他的!”
鐘璃無聲翻了個白眼。
“那我更不能同意了。”
祁驍不依不饒的纏著鐘璃說項,顯然是勸不鐘璃不打算改主意。
他想早早退位,就是想跟鐘璃出去玩兒。
鐘璃要是不去,他自己有什麼可玩兒的?
祁驍纏得鐘璃一個腦袋九個大,正想說點兒別的轉移祁驍注意力的時候,外邊有宮人來稟,說是三皇子回來了。
祁云玨哭喪著臉往里走,見著鐘璃嗷的一聲就喊了出來。
“娘親!啊啊啊啊啊!”
鐘璃被熊孩子一嗓子嗷出來嚇了一跳。
正怒火中燒的祁驍不滿皺眉。
“嗷嗷什麼?”
祁云玨委屈得不行,眨著一雙與鐘璃如出一轍的杏眼,嗷嗚嗷嗚的抹起了眼淚。
“大哥二哥扔下我,離家出走了!”
鐘璃眉梢往上狠狠一飛,有些啞然。
“什麼?”
祁驍愣了一下馬上嗷了起來。
“趕派人封鎖城門!去把那兩個不孝子給朕抓回來!立馬就去!”
祁驍下令已經很及時了。
但是一切還是沒來得及。
等他的人找到兩位離家出走的太子和二皇子蹤跡的時候,屋空無一人,桌上留了一封信。
大致意思就是,父皇年富力強,兒子自認學識疏,不敢貿然繼位,生怕辱沒了父皇一世英名,故而請求父皇寬限幾年,多容他們兄弟瀟灑些時日。
信中所寫字字誠摯,卻也不能抹滅連個小崽子搶在祁驍撂挑子之前,先溜一步的事實。
祁驍看完了信整整三天臉都是黑的。
鐘璃無奈之下更多的卻是好笑。
被兩位哥哥嫌累贅扔下的三皇子委屈了好幾日,日日在鐘璃的跟前打轉尋求安,慘白慘白的小臉上終于恢復了些許笑模樣。
Advertisement
祁驍的臉卻因此更黑得徹底。
這日,鐘璃親自下廚做了些桃花,祁云玨咬得里鼓鼓囊囊的,含糊不清地說:“母后,大哥說,母后告訴他,天高地遠,世間無限,只要有機會,一定要親眼去看看世界的模樣,若非如此,此生就當白白走過一遭,辜負無數風秀麗,當為生之大憾,這是什麼意思啊?”
鐘璃聞言眼中閃過一恍惚,半響后失聲輕笑。
瞇著眼睛看著天邊的流云,緩聲道:“意思就是,所有的路,都當自己走過的才算數。”
蒼云桑海,世間變數不盡。
若非自己親自走上一遭,又怎知活著是什麼滋味?
祁云玨茫茫然然的眨了眨眼,像是明白了,又像是不明白。
鐘璃正好笑的時候,抬頭就看見了朝著自己走過來的祁驍。
逆之下,步中年的男子英俊得不可思議。
他在下步步走來,眼中笑意悉數落在鐘璃臉上,像是用盡了一生的幸運前去求仰眼前之人。
目匯之時,鐘璃和祁驍都忍不住笑出了聲。
祁驍站定不,眉眼含笑的對著鐘璃出了手。
“起風了,我來了。”
我來接你回家。
鐘璃笑著將手放在他的掌心握住,語調微妙。
“你可知,我最慶幸的事兒是什麼?”
祁驍挑眉。
“愿聞其詳。”
鐘璃含笑而語。
“是當年在那個小村莊里,我撿到了個俊俏的小傻子。”
正巧小傻子還是的。
就把人撿回了家。
養著養著,就到了現在。
祁驍是在這異世當中,不可說的,最大幸運。
祁驍笑著勾起鐘璃的手,垂首在手背上落下一個輕吻,啞聲輕語。
“祁驍亦然。”
他橫無數海生死,負黑暗絕而去,滿暗都在那日晨中悄然而散。
鐘璃于他而言,是救贖。
是窮盡一生,也要的。
鐘璃笑了笑,微微仰用手指勾了勾祁驍的下。
“這是誰家小人兒?若無去,跟姐姐歸家可好?”
鐘璃眨了眨眼,眼中笑意漸濃。
“姐姐養你。”
祁驍微怔后啞然輕笑。
他俯將下放置于鐘璃掌心,抬頭著鐘璃淺瞳孔,一字一頓回答得極為認真。
“好啊,姐姐可要待我好才是。”
鐘璃樂不可支的了他的下一下,低聲道:“姐姐疼你。”
一輩子,都疼小傻子。
小傻子眼中亮狂綻,無聲笑了。
春正好,庭院中落英無數,花影紛飛之下,被忘在一旁的三皇子愣愣的看著宛若璧人的爹娘,眼中滿是恍惚。
“或許……這就是二哥說的,可遇一心人?”
可遇一心人。
白首不相離。
困守不相棄。
非死生,不可離。
(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成為白月光界的恥辱後
雲棠覺得,她是白月光界的恥辱。她跌落魔淵,九死一生爬回宗門後發現,愛她如珠似寶的師尊、師兄和爹孃給她找了個替身。結果,替身姑娘不簡單,她有嬌氣包一樣的身體,走幾步路都能把腳磨破皮。嬌氣姑娘拿走了雲棠所有法器、霸占雲棠房間,楚楚可憐地說:“雲姑娘,是我不好,我不該霸占屬於你的愛。”雲棠父母:棠棠,你不許欺負蘇姑娘。雲棠師尊:棠棠,因為你,蘇姑娘受了很多委屈,你若再這樣無禮,為師必定罰你。啥都冇做的雲棠:……因為嬌氣姑娘,雲棠過上了被三天一小罵五天一小罰的日子。她忍無可忍,乾脆躲開,每天到處瞎逛,某天,闖進一座山裡。黑髮冷眸的男子望著她,俊美冷漠的臉上刻著走火入魔的魔紋。*雲棠曾做了一個夢,夢裡她有爹孃寵愛、師尊疼惜,最後,師尊追求她,和她結為道侶,羨煞旁人。可現實是嬌氣姑娘練劍時手破了皮,爹孃師尊握著她的手,心疼得紅了眼。他們說,之前他們做錯了事,拿嬌氣姑娘當替身,嬌氣姑娘很可憐,他們必須彌補她。但冇人想到,雲棠一個人漂泊魔域,過得有多苦。爹孃師尊都圍著嬌氣姑娘轉,雲棠一不留神,就被那個黑髮大魔王拐著去耀武揚威。等爹孃回過神,發現怎麼親女兒和自己離了心,師尊發現自己所愛是誰時,雲棠已經被大魔王叼在嘴裡,摳都摳不下來。小劇場:大魔王燕霽冷聲:本座從不懂愛。雲棠恰好從他身邊走過去,緋紅衣裙翻飛,見燕霽看她,歪頭:“你叫我?”燕霽麵無表情、紅著耳朵移開視線,心底暗道:如果是她,那麼,再冇人比本座更知道愛是什麼。
55.8萬字8.18 10546 -
完結224 章
休夫後嫁給戰神王爺
“他娶你,不過是因為那句‘你嫁誰,誰就是太子。’” 這句話許多人對她說過,她就是不信。 然而現實打了臉,高門貴女被人算計,成了全家的恥辱。 大婚這日,她被鎖在洞房,同娶的側妃替她拜了堂。 即便如此,還一心想著扶人家登上皇位? 受儘屈辱的她含恨而終,被暴躁老姐穿越替代。 霸姐:什麼,我成了京城第一舔狗?不存在。 第一貴女就得有第一貴女的樣子,還想踩我上位?滾,打斷你的狗腿。 轉頭問傻王:“皇叔,皇位你坐嗎?我扶你。”
38.5萬字8 23033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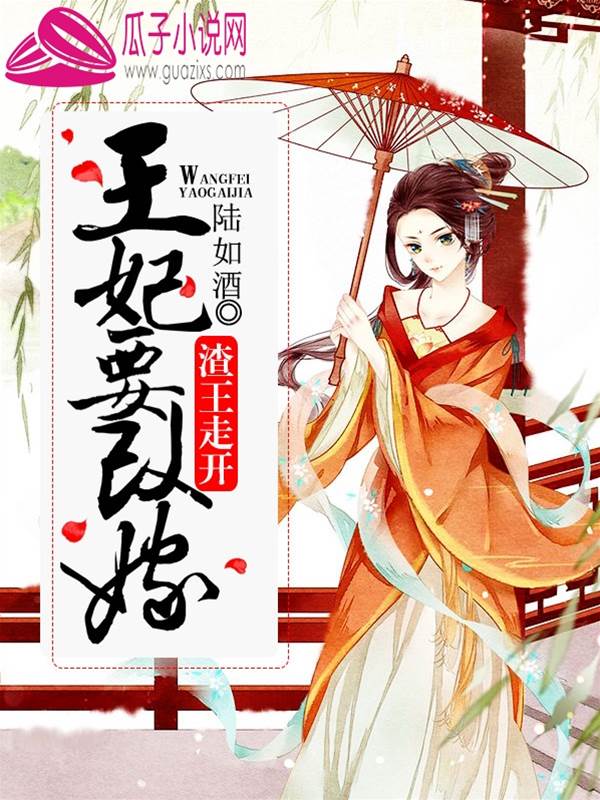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437 章
媚色難囚
一心復仇釣系心機美人vs禁欲清冷白切黑偏執大佬被心愛的夫君冷落兩年,最終趕出門去,沉尸河底。借尸還魂,重回夫家,她成了身懷秘密的遠房表小姐。媚眼如絲,顛倒眾生,她是令男人愛慕、女人嫉妒的存在。只有那清冷高貴的前夫,始終對她不屑一顧,眼神冰冷,一如既往。只是這次,她卻不再逆來順受,而是用媚色織就一張網,徐徐誘之,等著他心甘情愿的撲進來然后殺之而后快!裴璟珩紅了眼角嬈嬈,你依然是愛我的,對嗎?阮嬈嫵媚一笑你猜。(以下是不正經簡介)她逃,他追,她插翅……飛了!他摩挲著手中龍紋扳指,冷笑下令,“抓回來,囚了!”他囚了她的身,她卻囚了他的心。情欲與愛恨,走腎又走心。
86.5萬字8 4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