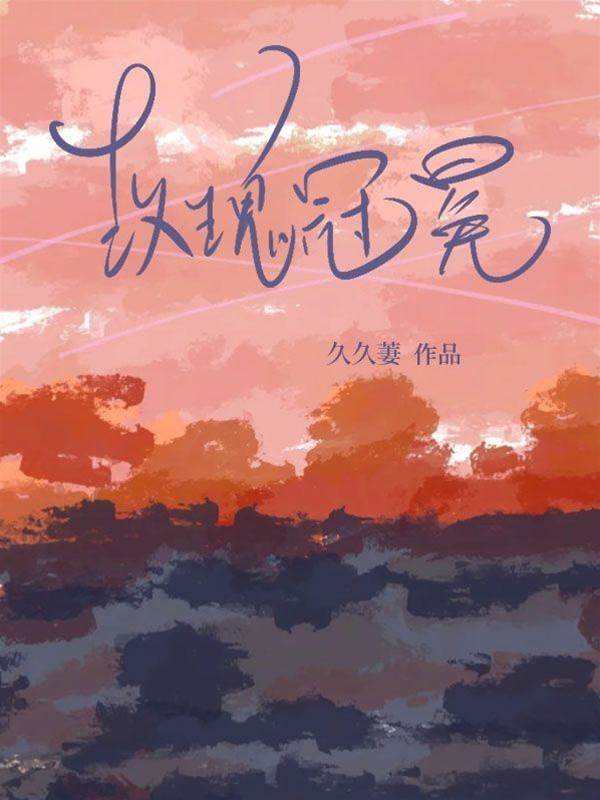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狼性大叔你好壞》 正文_第60章 你抱我
長長的睫上還沾著晶瑩的淚珠,撲閃撲閃就好像蝴蝶的翅膀沾染了珠,顧念愣愣的看著眼前的這一幕,半天都反應不過來。
雖然雲姨對的態度說的好聽點是恭敬,其實就是不冷不熱,但是還是經常會去廚房打下手,所以對於蕭家的廚房是一點兒都不陌生。
只是——
打翻的醬油瓶,摘過的菜葉,還有打碎了的碗碟……全都攤放在梳理臺上,眸轉再看到地面上也是一片油膩膩,在燈反下似乎在對著顧念張牙舞爪……
若不是之前來過,這哪裡看得出來是廚房的樣子,活像是垃圾填埋場的現場,只怕一不小心的話都能夠到。
顧念這些連那些傷痛都給全然忘記掉了,現在滿心好奇的就是,舒夏薇到底在廚房裡面做了什麼,怎麼做一頓飯就搞得整個廚房好像剛經歷過世界大戰被摧毀一般的覺。
難怪,蕭漠北會說舒夏薇的手不是用來做飯的,換是顧念的話,大概也會這麼說,但和蕭漠北的想法不一樣,不是疼惜,而是怕會連整個廚房都給燒起來。
顧念雖然在家的時候也沒做過這些,但是也不至於會弄這樣,看來這千金小姐和在貧民窟長大的孩不管怎麼說還是有著天差地別的。
自嘲的勾了勾脣角,挽起袖子,開始整理凌不堪的廚房。
客廳裡
舒夏薇將腦袋搭在了蕭漠北的肩頭,在看八點檔,因爲有蕭漠北陪著,就連再狗的劇也覺得特別的棒。
的眼神時而留在電視機明滅,但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盯著蕭漠北那張俊逸的臉龐看著,什麼電視劇都比不上邊的男人,憧憬了許久的這一刻總算是實現了,現在就差把蕭漠北完全的拿下,就不相信,蕭漠北會對無於衷……
Advertisement
舒夏薇有意無意的將自己傲人的前往蕭漠北的上蹭,蕭漠北忍著不悅,表現出一副很的樣子,但眼角的餘卻一直在注視著廚房那扇閉的門上。
“漠北!”舒夏薇纖細的手指覆在他的前:“我覺的客廳有點兒冷,我們回房間好不好?”
蕭漠北低謀,看著幾乎整個人都已經完全捲在他懷裡,說著冷卻眼如的人,他又怎麼會不知道舒夏薇的腦袋裡面在想什麼。
“等等吧,顧念不是還沒把廚房收拾好?”蕭漠北看似漫不經心的開口,眉心爲微不可見的蹙了蹙。
顧念顧念,又是顧念!明明這兩個人看起來都沒什麼集了,而顧念也被趕去廚房,怎麼還這麼的魂不散?
舒夏薇心裡越想就越是憤恨,長長的指甲將自己的都掐出了一道道的褶子,顧念就等著吧,絕對不會這麼輕易的就放過顧念的!
卻還是在蕭漠北的面前表現出一副很擔心的樣子:“漠北,你說顧念是不是因爲我讓去廚房的事而不高興了呢?”
不高興了,會嗎?
顧念進去廚房的時間有點兒長了,該不會真的像舒夏薇說的是在跟他置氣?蕭漠北的心裡面有點的擔心,但是轉念想到顧念之前在外部說的那些話,眸瞬間就冷下去。
“不管,你冷的話,先回房間吧!”轉眸溫對舒夏薇開口道。
“好,你抱我!”舒夏薇趁勢攀上蕭漠北的脖子,撒道。
“好!”
廚房裡的顧念兒不知道客廳裡面舒夏薇在心積慮的在蕭漠北的面前詆譭,好不容易將所有的雜和垃圾都清理乾淨,擰開水龍頭。
Advertisement
看著那些油膩到不行的盤子微微的蹙眉之後還是拿了起來,只是一到水,手立馬就收了回來。
是冷水!
顧念一邊在心裡面暗罵著自己心大意,一邊將開關旋轉到另一個方向——還是冷的!
這怎麼可能?蕭家的別墅在B市有名的富人區又不是貧民窟,一年四季都會有熱水供應,而且之前在廚房幫忙的時候,也都是有熱水的!
難道說是水管壞了,不會真的這麼湊巧吧!
還是說就活該沒有什麼好運氣,難得進一次廚房就沒有熱水,倒不是矯,冷水就不能洗碗,可是事趕事,偏巧這不是來了大姨媽,生的生理期是忌冷水的,這一點不管是千金小姐還是貧民窟的孩都是一樣的!
顧念放下手中的盤子,準備去問一問,可是客廳裡面除了電視劇明滅裡發出的聲音之外,哪裡還有蕭漠北和舒夏薇的影?
他們人呢,去哪了?顧念下意識地朝著舒夏薇的房間走去,門是敞開的,裡面沒人。可蕭漠北的車還在庭院裡停著,這代表沒出門。該不會是……心臟陡然停止跳,視線緩緩地向上轉移,停止在二樓,蕭漠北的門閉著……
他們在蕭漠北的房間裡面!
顧念的腦海裡面不由自主的就浮現了那一晚自己被蕭漠北在他的牀上的那一幕,繼而,主角卻變了舒夏薇的臉,他們兩個正在做著“那件事”。
頓時,小臉褪盡一片蒼白,清清的水眸眸底微微泛紅,似有淚閃爍,盯著那扇閉著的房門,整個控制不住的慄不止,心裡面酸難忍,狠狠咬牙,閉上雙眼不去看,不去想,可是眼淚還是順著眼角落而下……
Advertisement
突然,好像是想明白了什麼,扭頭返回廚房,像是豁出去一般,毫不猶豫的將手進冰冷刺骨的水中,咬著櫻脣,低頭一邊洗碗,一邊流淚。
手指間傳來冰涼,連落的眼淚都沒有了以往的溫度,可這些再冷也冷不過心底的寒意。
就是忍著那些刺骨的寒冷,讓整個廚房恢復到一塵不染,但是也因爲如此,的小腹因此糾痛難忍。
此刻,沒有心思去胡思想那些悲傷的事,只是想要趕回到房間洗個熱水澡窩在被窩裡面好好的睡一覺。
可是,顧念扶著樓梯好不容易到了樓上的樓梯口,經過蕭漠北房間的時候就聽到了舒夏薇嗔的聲音。
“唔……漠北,你討厭,輕點……”
顧念大腦一片空白,整個人就好像是大腦當機了一般,就那樣傻愣愣的站在原地,忘記了小腹的疼痛,兩條就好像是被灌了鉛一般拖不……
這樣的聲音就算是犢初開的都能明白,更何況這些天在蕭漠北的“幫助”下經歷了事,豈會不知道舒夏薇這樣意迷的聲音是在什麼樣的況下才會出現的。
曾以爲,即使和蕭漠北之間沒有可能,但是最起碼還有親的關係,可原來,他要的只是人,可以,舒夏薇也可以。
心,如絞痛。在心痛的襯托下,小腹的疼本算不了什麼。
的手的攥了拳頭,很想要衝過去破門而進,然後不顧一切的將他們分開。
可是……
是什麼份,又憑什麼那麼做!
是啊,於蕭漠北而言只是寂寞空虛時候的一個玩罷了,他和舒夏薇之間纔是真正的人,舒夏薇纔是他的未婚妻,是他將來的妻子,嚴格的說起來,就跟舒夏薇指責的時候說的那樣,他纔是那個第三者。
最後滿目傷的看了一眼閉的房間門,渾痠痛,安靜的邁著步子回到自己的房間,狠狠的將自己摔在大牀上。
將杯子蒙在腦袋上之後,那淚水就好像是決堤了的海水一般的肆……
蕭漠北的房間裡面,舒夏薇被吻的意迷,整個人更是癱在了蕭漠北的大牀上面。
“漠北……”的聲音裡面著,臉頰緋紅就好像是一顆了的蘋果。
蕭漠北約聽到了關門的聲音,估著顧念已經從廚房上來,幽黑的眼眸瞬間變得凝重,正好舒夏薇的雙臂就好像藤蔓一般的纏上了他的脖子,他想也沒想就將它們給剝離。
“怎……怎麼了?”舒夏薇的雙手就僵在半空中,有些不明所以。
蕭漠北轉眸並起,有些煩躁的扯開自己上襯衫的鈕釦,出前壯的,看得舒夏薇臉紅心跳,直咽口水。
原來,他突然停下來是因爲急不可耐!
看來,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哪怕是平日裡對冷淡的蕭漠北在剛纔那樣的親接之後還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至於顧念那個發育尚且還不完全的小丫頭,又怎麼可能會是舒夏薇的對手呢?
舒夏薇用手腕撐起腦袋,側躺在牀上,一雙眼睛貪婪的凝睇著蕭漠北赤果的上。
“我去洗澡!”蕭漠北只丟下這句話就徑直往浴室的方向走去。
舒夏薇一愣,有些反應的不過來,等到晃過神來,反覆在里面咀嚼這句話的意思,蕭漠北的意思是在邀請一起?
嗯,一定是這樣的!
如此一想,臉瞬時紅到無以復加!緩緩地起,著腳丫,低著頭一臉,輕輕地跟在蕭漠北的後,也往浴室的方向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31 章
過妻不候:傅先生,好久不見
“痛嗎?阿玉比你更痛!” 就為那個女人的一句話,傅君煜親手把她打入十八層地獄。她死裡逃生,原以為可以帶著孩子開始新生活,可四年後,越再次遇上了那個男人。 新的報複開始,她躲不掉,也不能躲。終於,她心死,傅君煜卻開始窮追不捨。 “傅君煜,你放過我們吧。” “好,你跟我複婚,我放過你。”
55.7萬字8 72290 -
完結1748 章

億萬首席寵妻成癮
「老公,快來看,電視上這個男人長得和你一樣帥!」在電視上看見和自己老公一模一樣帥的男人莫宛溪非常驚訝。賀煜城扶額,「你確定他只是和我像?」「不對,他怎麼和你一個名字?」被惡毒閨蜜算計以為睡了個鴨王,誰知道鴨王卻是江城最大的金主爸爸。天上掉餡餅砸暈了莫宛溪,本來是爹不疼,四處受欺負的小可憐,現在有了靠山,整個江城橫著走。
316.5萬字8 23753 -
完結2258 章

軍婚蜜寵:少帥大人讓一讓
顧念之不知道怎麼做,才能讓那個鐵血冷峻的少將大人愛上自己。眉目森嚴的少將大人一本正經:“……來撩我啊,撩到就是你的。”顧念之:“!!!”
562.9萬字8 171809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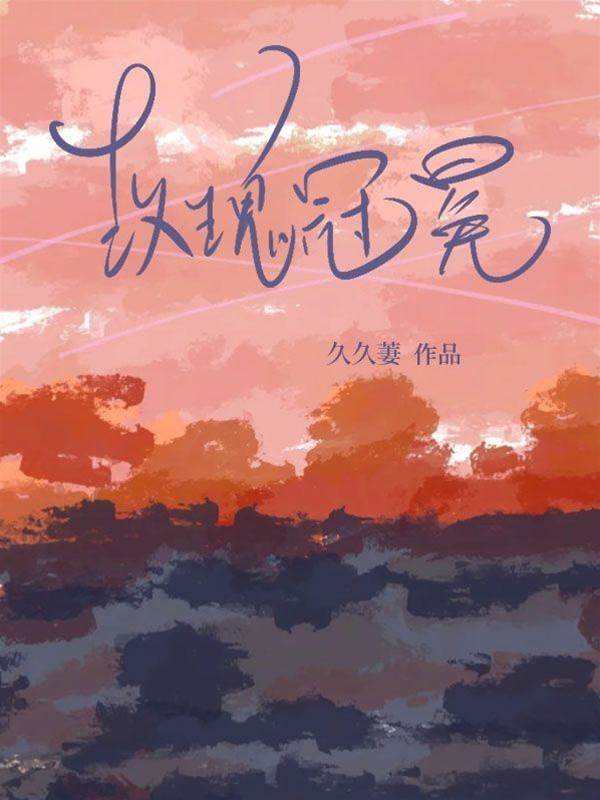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703 章

她美豔撩人,蕭律師心動了
喬星晚隻是為救家族企業,走投無路,想用身體換來蕭大律師的一場幫助。不料他卻拉她領證。“不為什麽,就因為我睡了你,拿走你的第一次,算理由嗎?”明麵上蕭大律師沉著冷靜,不近人情,私下卻瘋狂吃醋,邊吃醋邊為她保駕護航!老丈人被查?他二話不說為期洗刷冤屈,撈人!媳婦被同事欺負?他麵不改色把人逼瘋!媳婦要被雪藏?他大手一揮為媳婦開一間公司!“求求了,演過頭了,蕭大律師的演技無人能敵,你這樣容易讓人誤會!”“誤會什麽?”“誤會你當真喜歡我!”“是誤會了,誤會的太少,我是覬覦你太久,非你不可!而且是愛的很深,現在還需要再深一點……”到頭來,他真的愛了她太久,久到得從年少時開始說起!深情摯愛!
84.7萬字8.33 11594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