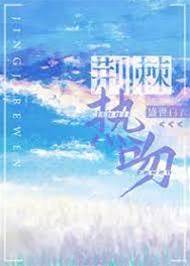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三爺寵妻太操心》 第65章 她送的卡通衣服
沈烽霖看切菜切得有模有樣,有點相信會做飯了,于是拿著裝著藥和服的袋子進了臥室。
江清檸長脖子了他的背影,有些心不在焉的切著菜,心里腹誹著: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歡這種服。
沈烽霖站在床邊,哭笑不得的看著他從袋子里拿出來的T恤,果真是小丫頭眼,選的東西都是別一格的年輕,只是確定這種卡通造型的服適合他這種老男人?
白的T恤正中心印著一顆大大的米奇頭像,前后都有。
沈烽霖面無表的把服拿了起來,照著鏡子比對了一下,尺碼還買的有點大了,難道在眼里自己屬于中年發胖類型?
他很嫌棄的把服放回了床上,解開袖口準備去換一正兒八經的家居服讓那個小丫頭看看。
然而他走了兩步,剛進帽間又折返回來,作迅速的把床上的T恤拿了起來。
帽間,男人神凝重的瞪著鏡子,雖然還是癱著那張不近人的面癱臉,但不得不承認,他好像年輕了一點。
嗯,其實自己也不老,穿這種朝氣蓬的服也是一種時尚。
“還行。”他自我安了一番。
江清檸切好了菜,正站在盥洗池邊清洗著蔬菜,聽著后有條不紊的腳步聲,下意識的回了回頭。
Advertisement
“哐當。”手里的菜簍子突兀的掉在了地上。
沈烽霖氣定神閑的走來,步伐穩健,心口位置的米奇頭像也在燈的折下閃爍著微弱的芒。
江清檸被自己的眼驚呆了,當時買這件服的時候有想過穿它的主人是什麼份嗎?
沈烽霖走進,一板一眼的說著:“怎麼了?不好看?”
“咳咳咳。”江清檸一陣急咳,說的戰戰兢兢,“好、好看。”
“好的。”沈烽霖打開冰箱拿出一瓶冰水,“眼不錯。”
江清檸面頰泛紅,更加賣力的洗著蔬菜,他是在夸自己嗎?
“叮咚……叮咚……”門鈴聲此起彼伏。
沈烽霖眉頭微擰,他很不喜歡自己的私人時間被不相干的人打擾。
“叮咚……”門鈴聲繼續孜孜不倦的響起。
林景瑄知道里面的人正在通過可視電話觀察自己,得意的晃了晃自己手里的珍藏版。
沈烽霖注意到對方手里的裝飾盒,毫不考慮的解開了門鎖。
林景瑄一路長驅直,一臉未曾辜負領導囑咐的興表,他道:“我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托人找到這只極品綠鬼,今晚上你必須用他招待我吃——”
沈烽霖這一尊大佛氣宇軒昂的站在屋子中心,那英氣人的劍眉星目,那得天獨厚的王者氣勢,那不怒自威的十米八氣場,全然的被他心口位置的那只米奇擊潰的然無存。
Advertisement
林景瑄一度以為自己瞎眼看錯了,很是用力的了眼睛,再次睜開眼時,震驚的連退兩步,不敢置信道:“三、三爺您是中邪了嗎?”
沈烽霖朝著他出右手,“綠鬼給我看看。”
林景瑄心口一一驚得慌,小心翼翼的把手里的瓶子遞過去。
沈烽霖仔細的研究了一番,很滿意的點了點頭,“確實是正品綠鬼,辛苦你了。”
“三爺,您今天有點與眾不同。”林景瑄了自己的心臟,這件服如果是穿在江城上,他們一定會開啟嘲諷技能笑他恬不知恥穿這種小鮮服。
“不好看嗎?”沈烽霖問。
林景瑄搖了搖頭,“好看,很好看。”
“這酒我先收著,過兩日帶去威斯。一起品。”沈烽霖隨意的將綠鬼放進了酒架,仔細想想廚房里那個手腳的丫頭,又慎重的關進了柜子里。
嗯,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江清檸圍著圍從廚房里冒了冒頭,“三哥,我可能需要一點點酒。”
“嗯,你自己挑。”沈烽霖瞥了一眼還杵著不的家伙,“你還不走?”
林景瑄這才反應過來這棟宅子里還有一個人。
沈烽霖徑直朝著書房走去,“正好,我還有一些話要和你說。”
林景瑄拼了命往廚房打量,還沒有看清楚里面藏著誰,就被后犀利的目著往書房邁開腳步。
Advertisement
“環意集團的事你打算怎麼理?”沈烽霖直接開門見山的問。
“強行收購。”林景瑄雙手在袋子里,“營業額一直于負增長,他們也撐不了多久了。”
“江城那邊怎麼說?”
“環意老總是個油鹽不進的犟骨頭,很難通,估計江城在他手里也是吃了不虧。”
客廳里,某個小丫頭還在研究哪瓶酒不是特別名貴的品種。
只是越想越糊涂,之前沈天浩說過他三叔收藏的大部分是絕版,哪怕隨意的放在客廳里,也是極品。
江清檸不敢酒架上那些熠熠生輝還在發著的紅酒,彎下腰打開柜子,一只木盒子吸引了的目。
拿起盒子,咔嚓一聲打開了。
江清檸思忖著三爺把它隨便放在酒杯柜子里,連盒子都沒有拆,而且看那樣子,新的,應該不是很名貴吧。
于是乎,很開心的把里面的酒瓶拿了出來。
“什麼味道,這麼香?”林景瑄一推開書房門就被香氣撲面,他本能的拱了拱鼻子。
沈烽霖很是意外,看來這丫頭的廚藝還不是很差勁。
林景瑄掩輕咳一聲,“我這來的匆忙也沒有吃晚飯。”
“所以呢?”
“這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要不我就冒昧吃一點東西再回去?”
“你倒是不客氣。”沈烽霖往餐廳疾步而去。
林景瑄厚著臉皮跟著上前。
只是,兩人不約而同的被桌子上的那一只酒瓶吸引了,很明顯,里面的酒水已經被揮霍一空了。
林景瑄心里咯噔了一下,如果他沒有猜錯,這只外形特別優的酒瓶子正是自己剛剛拿來的那一只。
江清檸拎著鍋鏟從廚房里跑了出來,看著一言未發的兩人,心里有些不安,忙道:“我是不是拿錯了?我看您放在柜子里,以為是普通的酒,我是不是又拿了什麼名貴甚至是絕版的珍藏品?”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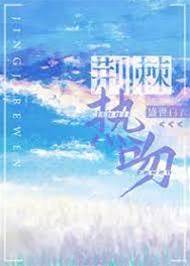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38 章

脫軌
不接吻、不留宿、不在公開場合調情……這是他和她之間的規矩。不管床上如何,床下都應時刻保持分寸;關于這一點,余歡和高宴一向做得很好。直到余歡所在的律所新來了個實習生,而人那正是高宴的外甥——事情開始脫軌。
6.1萬字8 31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