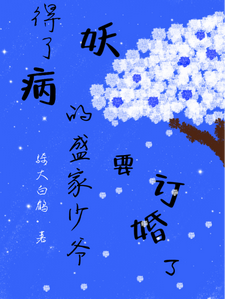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你快點心動》 第62章 心動了嗎
這才停電多久, 電就又來了。
同學們都在笑罵不愧是槐城一中的效率,生怕他們學一分鐘。
岑可轉頭找溫聽蘿的時候,忽然一愣,“蘿蘿, 你臉怎麼這麼紅?”
溫聽蘿不知道有多紅, 很明顯嗎?無辜地眨了眨眼:“熱的。”
是嗎?
岑可狐疑。
最近槐城是開始熱了, 但也沒這麼熱吧?
撓撓頭, “哦, 這樣。”
岑可忽然忘了自己剛剛是為的什麼事找蘿蘿, 迷茫地又轉回頭去。
溫聽蘿平生從來沒有這麼淡定地胡說八道過。有一種自己都被季清洄帶壞了的覺。
再一看邊的人, 正揚著在忍笑。
氣不過, 將課本豎起來擋在兩人面前——斷絕聯系渠道。
那邊好像真安靜了。
——就在溫聽蘿剛起這個念頭的時候, 他的聲音忽然近在咫尺:“真的熱麼。”
被嚇了一跳,啞聲失聲, 險些下意識地站起來。
溫聽蘿側目, 他竟就在耳邊,挨著豎起的課本與說話, 一雙眼, 已是恨不得將勾進其中。
咬著牙, 聲音都是出來的:“季、清、洄。”
他了下的臉, 一本正經地知溫度:“嗯……還好,不是很燙。”
溫聽蘿一愣。他的手就那樣自然而然地覆上來,在的臉上……
沒想到這人已經可以這麼淡定地放肆,渾然不覺自己的行為有多過線。一把拽下他的手,慌張地四下一看, 確定安全后又趕回來瞪他, 警告道:“你……安分一點。”
這個世界上。
大抵是第一次有孩和他說。
——你安分一點。
季清洄再次解鎖新的樂趣, 摁著眉心,卻不住笑。
Advertisement
“行。”他看上去可真是太好商量了,“聽你的,安分點。”
沒什麼可信度。
溫聽蘿聽聽而已。
為了他囂張的氣焰,溫聽蘿翻出了一道之前沒做出來的數學大題給他做。
——效果不錯,果然這廝安靜到了晚自習結束。
就在背起書包要走的時候,卻被他拽住,“解出來了,來,給你講講題。”
溫聽蘿:“?”
想準點走人,不想拖堂。可是自己挖的坑,咬碎牙也得自己跳。
溫聽蘿只能不不愿地復又坐下來,聽他講題。
“先設三點,這點是W,這點是L,這點是T。”
他似乎慣常用這幾個字母,溫聽蘿早已習慣,點點頭,聽他繼續往下講。
季清洄也不著急,不不慢地講完。
等他講完,已經是十幾分鐘后,班級的人走得飛快,早已走空。溫辛和溫聽蘿說了,去車上等,所以這時候班級里只剩兩個值日生和他們倆人。
值日生打掃完,一起提著垃圾桶去倒垃圾。
——班級徹底只剩下他們兩人。
季清洄猝然手拉過溫聽蘿,吻住。
錯愕的神甚至都來不及收。
——唔,這個混蛋!
一個晚上襲兩次,玩的還全是心跳!
明明是想讓他做道題,安分點兒,乖乖待到放學,可哪里想到結果卻演變了又被占了一次便宜……?
這什麼?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是不蝕把米?
季清洄沒有太過分,他知道倒垃圾的地方離班級的距離,對于他們多久會回來,他心里有個大概的估算,到底還是沒舍得浪費這麼一點時間。
只是蜻蜓點水的一吻,他就撤了回去,只是挲了下的手:“怎麼辦,不想放你走。想跟你一起回家,贅也行。”
Advertisement
溫聽蘿:“?”
男生有多會人,算是領會了一回。
只消淺淺淡淡地給說上幾句,輕易就能人心弦。
瞧他多會說呀。
三兩句話,幾乎要將未來的餅都給畫全了。
好聽的話實在是悅耳,尤其是,當這話還是季清洄說的時候,悅耳程度翻以數倍。
溫聽蘿回手,了通紅的耳垂,“走了啦,回家。”
他啞聲說:“要高考了。”
溫聽蘿不解地看他:“嗯?”
這自然是不必他提醒,難道還能不知道要高考了嗎?每天都在倒計時,老師在說、同學在論,哪里需要他來告訴。是以不知他忽然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高考后,就能在一起了。”他沉沉地凝著。
目燙得溫聽蘿幾乎無法對視。
狼狽地移開眼,閃爍著目,幾不可聞地胡嗯嗯著。
季清洄揚。
等待馬上結束。
聽見,他同說:“我等很久了。”
-
高考如約而至。
那是屬于這個夏天,屬于某個特定年人群的獨特記憶。
最后一科考完后,走出考場,也就意味著——全解放。
吶喊聲歡呼聲不絕于耳,這群高考完的年盡數釋放出了抑住的天。在這一刻,他們的笑容是最輕松的,也是最恣意的。
——年本該如此。
溫聽蘿仰頭看了眼依舊熾烈的日,抬起手遮了遮,彎起了。
考完了。
結束了。
的十年寒窗,也至此落下帷幕。
為了這一天,付出了十幾年的心。
好在,諸事順遂。
希,得償所愿。
當天晚上,他們全家還在外面吃飯的時候,收到了季清洄的消息。
——【不在家?】
聽這話就知道他現在或許正在溫家樓下。
Advertisement
溫聽蘿有些意外,連忙解釋:【在外面吃飯呢。你在哪里?在我家嗎?】
季清洄:【嗯。你先吃,待會有空了找我,有事跟你說。】
待會才說嗎?
溫聽蘿被他吊足了胃口,心的。
可只能先說好。
因為溫常賦和徐亦婉都在邊,在這種時候與他聊天,張。
——直到現在,仍然滿滿都是早怕被發現的慌張和心虛。
覺得,不太適合做虧心事。
徐亦婉不管孩子們績出來后是什麼樣,反正現在考完了,放松和休息就該是第一位。和丈夫帶著兩個小崽子又是吃又是玩的,慶祝他們高考結束,接下來可以擁有接近三個月的假期,一家人玩到了很晚才回家。
都已經是深夜了。
溫聽蘿才得以給季清洄打去電話。
“你剛才說有事和我說……是什麼事呀?”能用一句話就吊滿一晚上的胃口,也就只有季清洄了。
那邊卻傳來季清洄不滿的聲音:“給我打電話,就只是為了問這件事?”
溫聽蘿的聲音溫,有些無辜的疑:“不然……呢?”
季清洄愈發不滿意,提示道:“高考完了,都沒話要跟我說麼,也不想見我麼。”
“……”
溫聽蘿有被傲到。
站在臺邊打電話,抬眸看向天邊的月亮,任由月灑落在自己上。
彎著說:“那還是,有點想的。”
高考結束,第一個想看見的人就是他。
最想看見的,只有他。
想告訴他,完地答了題,狀態很好,沒有出什麼紕。
覺得答得還不錯,給這十年寒窗呈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高考終于結束了,還想給他一個很大很大的擁抱,告訴他:我們終于解放了,這一年終于終于結束了。
可是考場這樣大,加上人群涌,一時間不見他。他們沒有心靈應,沒辦法及時準確地應到對方的方位,所以找不見他。
爸爸媽媽就在校門口等,刻意地流連了會兒,也沒見他后,便只能離開。
季清洄慢悠悠地說:“作為懲罰——”
溫聽蘿連忙打斷:“等等,怎麼就懲罰了?”
都說想了!這人不講理!
季清洄勾著笑,“你到現在才勉強想起我,難道不該懲罰麼?”
他很有理有據。
但溫聽蘿覺得自己好冤,怎麼莫名其妙就背上了個懲罰。
蹙著眉,思考半晌,才猶豫道:“你先說來聽聽。”我再決定我要不要接這個懲罰。
季清洄:“?”
他嗤笑了聲,“你想得倒是,全天下的便宜都要你一個人占完了。”
溫聽蘿皺皺鼻子:“你別這麼小氣。”
季清洄挑眉。
得。
這還上升到他小氣了。
他摁了摁眉尾的無奈,不跟計較,“懲罰是,陪我去趟畢業旅行。”
溫聽蘿:“?”
還有這等好事?
原來這就是“季清洄的懲罰”?
眼前一亮,了下,“那再多來幾個懲罰。”
季清洄:“……”
“我溫聽蘿今天就舍生忘死一回,接下這懲罰。下回還有懲罰記得喊我。”
季清洄:“……”
溫聽蘿笑出了聲。
在這夜里,比銀鈴還要悅耳。
強迫自己認真一點,問些正經問題:“怎麼突然想去畢業旅行呀?你自己一個人嗎?想去哪里?”
“倒也不是突然,之前就想過,所以都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出發。不止我們兩個,還有符戈和岑可,地點先保,到時給你個驚喜。”
溫聽蘿聽得眼睛越來越亮,堪比漫天星子,甚至更勝三分,儼然是充滿期待。
剛想答應,但是謹慎起見,還是先問了下:“你們應該不會是聯起手來把我拐騙賣去深山老林吧?”
季清洄:“……”
他笑了聲,“就算是,我也能功。”
就算真的是要拐騙,他現在也完全有信心將功哄住,進退結合地打消的疑慮,將功帶走。
溫聽蘿愕然。
好囂張,好狂妄。
聽得拳頭都了。
“你知不知道,你這番話很犯罪?”不滿地質問。
“還有更犯罪的事想做。”他啞聲說。
溫聽蘿:“?”
“怎麼不問是什麼事?”
“……不太想知道。”這還用問嗎?
眼看著話題即將跑偏,溫聽蘿飛快地說:“等我考慮一下再回答你!”
一說完就掛斷了電話,就跟后有大尾狼在追著跑似的。
溫聽蘿本來是要答應的,和好朋友們一起畢業旅行是一件很妙的事,更何況……還有他。
但在他的危險發言之后,猶豫了,覺得得先考慮一下的人安全。不是擔心會被他們拐賣,而是擔心他……這個危險恐怖分子的行為。
溫聽蘿在房間翻來覆去地想了很久很久,卻是越想越糾結。一邊是按捺不住的想去,一邊是可能會有“危險”的預警。
最終,給岑可發了條消息:【可可,你會保護我的,對嗎?】
岑可莫名,不知此話何意。怎麼突然這麼問?
撓撓頭,老實地按照字面上的問題回答:【那當然啦,你可是我的寶貝蘿蘿!】
于是。
溫聽蘿一咬牙。
決定大膽地答應一回大灰狼的邀請。
拼了。
而且這麼多人呢,又不止他們倆,應該也不至于太“危險”。
——溫聽蘿腦海里的危險與旅途無關,只與季清洄有關。
給他發消息,說去。
季清洄收到消息時,勾笑了下。糾結了兩個小時,終于是,糾結完了啊。
掙扎什麼?兔子終究是要……
掉進狼窩的。
-
他們的畢業旅行暫且定下。在去之前,還有個謝師宴。
是一班的同學們自主籌備的,主要是大家想再聚一次,好好告個別。
定好的時間還沒到,人已經來了一小半。
溫聽蘿和溫辛已經提前了很早出發,沒想到來得都還算是晚的。
往里探了探,一眼就能定在某個人上。——他總有這樣的本事,于人群之中,也不曾堙滅半分,永遠都是最耀眼的那一個。
和溫辛隨便找了個地方坐。
不知道是不是溫聽蘿的錯覺,好像到季清洄若有似無的目。
猜你喜歡
-
完結92 章

陸教授的戀愛法則
臨大學生都知道數學系副教授陸昭嶼不僅生得一副好皮囊,還講得一嘴好課堂。性格嚴肅,學術嚴謹,眾嘆:高嶺之花摘不得。這條與陸教授有關的帖子常年置頂在臨大貼吧上。突然有一天25000樓裡一位名為“木舒坦”的樓主新發了一條評論:不僅炒得一手好菜餚,還說得一嘴好聽話,又會哄人,又會疼人,總說:我之於他,是如獲至寶。吧友們一眾驚訝,在25001樓裡議論紛紛,直到一位眼尖的吧友發現在1分鐘前有位“LZY”的回復了25000樓“乖,回家吃飯了”。吧友們:“LZY陸昭嶼?”、“真的是陸教授?”、“那是師母?”“師母,究竟是何方神聖,竟然摘下了高嶺之花”“我的陸教授(_)”“木舒坦何許人也”“ @木舒坦,賜教倒追陸教授的重要法則”...一時跟帖無數,評論區徹底炸開。舒槿姑娘微微紅著臉放下手機,抿唇看了眼往她碗裡夾糖醋排骨的男人,心想:才不是我倒追呢!
26.4萬字8.18 19994 -
完結125 章

熾焰流星
祝星焰年少成名,從頂流偶像到拍電影,拿下獎項大滿貫,也才十七歲。 少年如同橫空出世的一抹耀眼火焰,點亮娛樂圈,高高站在金字塔頂端,無數人仰望。 宋時月同他最遠的距離,是隔着無法跨越的屏幕。最近的距離,是教室裏,他坐在她身側。 作爲班長,需要肩負起重要通知下達到每個同學的任務,關於這項工作,她做了三年。 宋時月和他的聊天記錄有上百條,他們的見面,卻只有數十次。 - 媒體一次採訪,讓所有人都知道,祝星焰高中有一個很負責任的班長。 她是他高中三年唯一記得的女同學。 只可惜,畢業後失去了聯絡。 宋時月想起自己被盜的q q號,費盡周折終於登上去時,看到了好幾條未讀消息。 無人回覆的遺憾,最後一條,是想觸碰又戛然而止。 【今天路過京市,方便的話,能見一面嗎】 宋時月寫寫停停,回覆在對話框裏停留許久,發送出去。 【你還在嗎】 那邊頭像活過來,幾乎是秒回。 【我在】 很久之後,祝星焰官宣,是一張模糊不清的照片。 黑夜中,少年戴着鴨舌帽,等候在宿舍樓底下。 少女朝他飛奔而去。 配文是:【十六歲心動的月亮,終於被我抓在手裏】 所有人都以爲,祝星焰是最先動心的人。 他年少的暗戀終於修成正果,得償所願。 無人知曉,十六歲的深夜。 見到祝星焰的第一眼。 潮溼陰暗的細雨,一瞬間化爲春水綿綿,少年遞給她的那把黑色雨傘,她帶在身邊數年。
18.6萬字8.18 5077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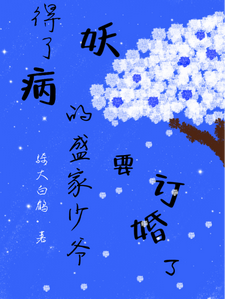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
完結104 章

糟糕!聞少他動了心
【清冷溫婉系花x高冷散漫太子爺】一見鐘情也好,見色起意也罷!他聞璟白的世界里就沒有忍這個字。 溫黎晚有一顆天上星,但從不曾有過非分妄想。 她知道那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所以一直循規蹈矩。 可是有一天,天上星主動向她降落,她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擁有,只能避而不見。 – 聞璟白放肆散漫地活了二十幾年,身邊最不缺的就是前赴后繼的女生,他對她們的熱情都是興致缺缺。 某一天,他被一雙藏不住愛慕卻又明顯疏離的眼眸勾起了興致。 更衣室狹小的角落里,他彎腰湊近退無可退的她,濕熱的氣息噴灑在她耳畔,嗓音低啞蠱惑,“要不要跟我試試?”
20.6萬字8 3915 -
完結39 章

我是你的小跟屁蟲
虞思慎第一次見安可蒙,是她八歲那年。 那年,她的眼眸宛如星河,清澈無雙。 跟在虞思慎的身后,可憐巴巴的叫“思慎哥哥”。 而他,一個十六歲的少年。 平靜的目光背后,是驚濤駭浪,是無底深淵。 再一次見到她,他把她一手拽進了無底深淵,絲毫沒有猶豫。 虞思慎覺得,安可蒙這個女人不論走到哪里,只能是他的人。 他可以完全掌控安可蒙。 沒想到,一年之約過后,安可蒙在他家一分鐘不愿意多留,直接收拾了行李,毫無預兆的扎進一場網暴。 虞思慎默默查找幕后黑手,安可蒙卻逃到了另外一個城市。
7.3萬字8 1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