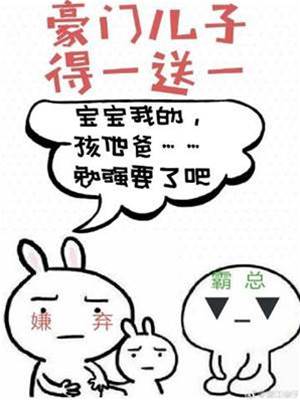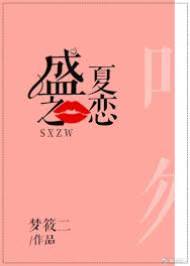《夢河夜航》 第56章 第 56 章
章閔敏地察覺到,從床戲那場戲開始,的兩位主演之間的氣場變得不太一樣了。本來以為是床戲導致的尷尬,后來發現,好像是相反的……
之前兩個人非常別扭,總隔著一層什麼東西,但那場戲之后,那層屏障好像已經被走,導致這兩天拍的戲也特別順,只要涉及他們的對手戲,幾乎都是一條過。
只能說演員之間如果克服了親戲,確實會對關系的拉近有很大幫助吧。
誰都不知道,事實是因為兩位主演的關系已經變了質。
就連婁語本人也不清楚,說不清是哪個瞬間來到了這一步。
也許是聽到聞雪時坦誠這些年的不安,也許是看到那條微博一直存在的剎那,也許是因為那一首《o》長達三分鐘的空白,也許是那張他在頒獎典禮現場拍下的照片……每一每一,那些龐大又被藏起來的意,一下子攤到了眼前。
人或許可以躲過一片的綿雨,但無法從一場暴雨里全而退。
尤其是,對于一個心里一直干旱的人而言。
像是回到了當年那條馬路,撐著傘,聽著雨滴打在傘面上噼里啪啦的聲音,每一聲都是吶喊。
于是終于將傘一把丟掉,選擇再一次去捉住命運的線。
這是一個很沖的選擇,知道。
但相比十年前,他們現在算是有底氣的大人了吧,很多當年左右他們的事已經不會再重演,年輕時那些自以為是的做法如今也不會再認為是正確的。
和舊人復合是一場讀檔重來的,但那些命運的節點卻又不完全相同。盡管害怕,也想再看。
因為他們腳下還流淌著歷久彌新的意,可以接住彼此。
Advertisement
從老房回到劇組后,通告單又是一場熬夜的大戲,回到劇組房間后昏天黑地睡了一天。
醒過來時,已經又是傍晚,作息這幾天都有點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讓栗子預約今晚的,心道是不是得去做趟皮護理比較好。今晚沒有排戲,可以好好放松。
但剛給栗子發完消息,突然愣住,意識到自己按照的是以往一個人的步調進行,但現在不太一樣了,不再是一個人。
的生活里重新多出了聞雪時。
婁語先撤回了消息,返回聊天界面,重新把聞雪時的頭像置頂,給他發了一條我醒了的微信。
他應該還在睡覺,一直沒有靜。婁語起洗了個澡,敷完面回來,點開手機,一條未讀消息。
『我剛醒。』
回了個豬頭的表。
他干脆發來語音,點開是還沒睡醒的沙啞聲音。
“出力的人總是要多睡會兒的。”
婁語的手心被這句話撓得蜷。聞雪時并不是說話的類型,說這句話也沒有調戲的意味,仿佛就是學探討一般替自己辯解,可讓人聽了會臉紅又無可奈何。
大概是覺得一直沒回,他突然跳出了一則視頻請求。
婁語被彈出來的提醒框嚇一跳,趕跑到衛生間湊近鏡子端詳自己,把剛吹蓬的頭發又往顱頂松了松,才假裝淡定地回來,接通手機。
對面的鏡頭很模糊,晃著晃著,視線一轉,正對著沙發,和的房間是一樣的布局。
剛剛應該是他拿著手機從房間走到客廳,發現被接通,他趕進鏡頭,屈往沙發上一座,頭發的,上套了件寬松的灰t和黑休閑。
他看著鏡頭對面的,忽然湊近屏幕,剛才還能看到半邊子的畫面一下子變他的五特寫,這剎那的變化沖擊的。
Advertisement
婁語咳嗽:“干嘛,太近了。”
“是你離鏡頭太遠了。”他直盯著鏡頭,“我都看不清你。”
一聽,有點張:“你不會這些年近視了吧?”
“……”
婁語笑出聲:“我逗你的。”
然后也把手機拉近,將自己的臉占滿屏幕,好像兩人就這樣近在咫尺。明明他們本就在同一個走廊,隔著兩三個房間,但偏偏只能以這樣的形式連線。劇組人多眼雜,去休息室倒還行,去房間如果被誰看見可就說不清了。
兩個人沒說話,安靜地著對方,好半天出聲問:“你等會兒準備干什麼?”
“看節目。”他舉起一旁的ipad,“今晚有《歌王》,我和你去錄的那一期。”
“啊……”
婁語恍然:“那我也要看。”說著立刻起也去抱了ipad回來。
他調整了一下姿勢,整個人舒服地窩進沙發里,笑著睨向鏡頭道:“那我數三二一,我們一起點開?”
“好。”
“三、二、一……”
“我點開了!”
兩人好像稚園的小孩,遵照誰都不能搶拍的規則,同時點開了進度條。
屏幕里的和他位置隔得很遠,主持人介紹時他們時,對方的反應都特別假模假樣地鼓掌。
如今看到這一幕,忍不住笑了。
“笑什麼?”
說:“好裝的兩個人。”
他聞言也笑:“所以天生一對。”
“……”
婁語抓過茶幾上的杯子猛喝水。
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互相問著為什麼給這個歌手推薦票,真的喜歡這首歌嗎,說當然不是,只是對方經紀公司提前打過招呼而已。
“但這首歌我是真心投票的。”
聞雪時忽然指著現在正在唱的,《袖手旁觀》。
Advertisement
婁語當時就對這首歌特別深,喃喃道:“我當時也是最喜歡這首。”
至于為什麼,他們都心照不宣,沒必要再過多追問。
他們沉默地,專心致志地再一次將這首歌聽完,到結尾時,鏡頭掃過嘉賓席,無意間帶到了聞雪時。
婁語一愣,連忙按下暫停,又倒回去看這一幀——他扭過頭,雖然鏡頭沒有明顯指明,但婁語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坐哪兒,因此知道,他看向的就是的方向。
當時還以為這是自己的錯覺。
但機仁慈地保留了這份小心翼翼的錯拍,將那份延時的不舍得越時間,投遞到面前。
婁語沒有再往下看,暫停在聞雪時看著的這個眼神中。
聞雪時還準備和討論
“卡了。”把ipad反過來,出暫停的這一幀,“卡在這了。”
聞雪時反應過來,了脖子:“嗯……”
看被抓包的尷尬。
節目也差不多到尾聲了,婁語把ipad往旁邊一扔,再度湊近屏幕,小聲說:“我們要不要見一面?”
他也湊近屏幕小聲問:“你確定?”
多年前的是一場來不及茁壯就得被迫藏起來的,而多年后,他們依然慣延續了之前那樣的模式,地,不讓任何人知道地在一起。
而且剛復合,還在拍攝中,他們目前也只能這麼做。
婁語安靜了片刻,問他:“你有和丁文山說我們……嗎?”
“還沒有。”他抿了下,“我覺得不著急。現在這樣就好。”
婁語著杯子的邊緣,在他這句話中突然到五年的時在他上碾過的痕跡。不再像當年那樣,當提出自己要和姚子戚炒cp時,他咬牙不甘心地問,那我們就見不得是不是。
而如今,聽到他沉穩又平和地說:“也不是說滿足于現狀,而是我是想給我們兩人留有余地。你慢慢考慮,可以等到戲拍完再決定是不是真的想好了。畢竟我們現在在一起,也不算純粹是我們兩個人的事,但現在還依然在我們兩個人能控制的范圍里,如果你想隨時離開,都還可以輕松地走。”
婁語聽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說話,微微嘆息說:“可是我已經想好了。”
五年前,的猶豫曾像刀,狠狠地扎過他。
而五年后的今后,終于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蓋上刀鞘。
他聽完的話,不由得了下鼻子,背過去打了個噴嚏。
回過時,鼻頭紅紅地說了句,鼻子有點。
配合地說小心不要是冒,沒有拆穿他微紅的眼睛。
聞雪時繼續著鼻子,輕描淡寫道:“那麼我也早想好了。”
婁語咬住,又松開,笑了笑,臉上的五都不知道該哪兒放。
認真道:“雖然我們暫時還不能讓外人知道我們的關系,至現階段是。但等接下來哪天我經紀人來組里探我班的時候,我會當面告訴他。一個是瞞不住,還有一個,是我想表達我的態度——你現在是我的人,以后也會是。”
聞雪時微微皺起眉:“他會不會為難你?”
“周生嗎?”婁語思忖,“應該不會吧……不過關于方面,我一直也沒機會和他討論。之前簽到他手下時就已經和你在一起了,就算當時他建議我去和姚子戚炒cp的時候也沒提過讓我分手。分手后這些年我也沒找人另談,他也不用心我這方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態度。但這些年,我和他的相模式不是你當年看到的那樣了。”
他神微怔:“是……你們一起過了五年,肯定會有變化。”
“當年我算什麼,能被他簽上就誠惶誠恐了。至于我為什麼能被他簽上,我當年告訴你的是因為運氣,我不知道你信沒信。運氣是一方面,但確實是瞞了你一件事。”
婁語停了半晌,還是選擇說了出來,如今時過境遷,也不怕再打擊到他的自尊心。
“當年你和團隊鬧得那麼難看,我擅自幫了自以為對你好的忙,你跟我說不要去求別人,你自己來。但我還是沒辦法眼睜睜看著你沒起……所以我私下里有去找過一次周生,就是那次讓他對我有印象了。”
事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推倒了第一塊,就接二連三地推下去,再不由誰控制。本是想為他謀求出路,最后卻了自己的天梯,而這道天梯又間接載著和他分離。
但至,他們又走回到彼此邊。
婁語輕吸口氣,覺得好恍惚。
“說回來,就是當年那個境況,金牌經紀人和小糊演員……我就算有別的想法也都是聽他的。而且他也確實厲害,考慮的東西遠比我全面。但這兩年不太一樣了,我逐漸有自己的想法,像夜航船的綜藝就是他開始反對但我堅持要去的。我們算是越來越能平等地去對話。”打趣自己,“再怎麼說我也是火了,他也得賣搖錢樹面子啊。你不要擔心,我會理好的。”
聞雪時定定地看著屏幕,眼睛慢慢地就彎了起來。
“小樓,你長得更加耀眼了。”他說,“本來還想克制住見你的,看來不行。”
打了個響指:“那就見吧,假裝只是偶然見那樣。”
十分鐘過去后,婁語扎起馬尾辮,換上運套裝出門了。
來到山莊的健房,在跑步機上跑了半小時,然后從口袋里掏出耳機戴上,假裝在聽音樂,但其實連的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氣吁吁地按下停止,滿頭大汗地往外走,邊說:“我準備回來了。”
回到中庭時,看見二樓某間房門同步打開。
聞雪時假裝隨意地走下樓,而上樓,兩人在無人的樓道里而過,汗的手心被他握住,輕輕了。
的心砰砰砰地跳起來。
這種覺,很像曾經想象中的校園。
時代曾經幻想過,但卻沒能實施的,和喜歡的男生在樓道偶遇,怕被同學和老師發現,因此只能在晚自修結束的時候看對方,黏糊糊又地牽一下手。
已經和兩個字毫無關系的,在這個很普通的夜晚,聞雪時手指若無其事纏上來的剎那,到了十五歲那年,獨自躲在閣樓里看電影里吻戲的那種悸。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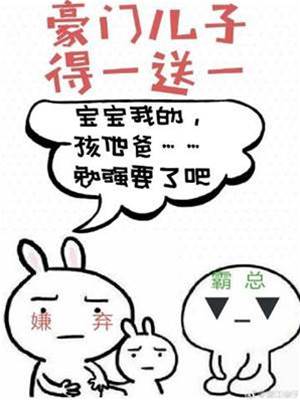
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別人去當后媽,要麼是因為對方的條件,要麼是因為合適,要麼是因為愛情。 而她卻是為了別人家的孩子。 小朋友睜著一雙黑溜溜的大眼,含著淚泡要哭不哭的看著林綰,讓她一顆心軟得啊,別說去當后媽了,就算是要星星要月亮,她也能爬著梯子登上天摘下來給他。 至于附贈的老男人,她勉為其難收了吧。 被附贈的三十二歲老男人: ▼_▼ ☆閱讀指南☆ 1.女主軟軟軟甜甜甜; 2.男主兒砸非親生; 3.大家都是可愛的小天使,要和諧討論和諧看文喲!
31.8萬字8.33 47271 -
完結437 章

少帥的冷情妻
結婚三年,她是雙腿殘疾的卑微愛慕者,他是令人畏懼的江城少帥。他從來不屑碰她,對她厭惡至極:”我不需要你生的孩子。“真相大白,婚約不過是一紙陰謀,她終于下定決心離婚。沈晚吟:“簽字吧,以后我們各不相欠。”“少帥,夫人懷孕了!”傅北崢震怒,撕碎…
93.1萬字8 35840 -
完結439 章

敬我余生不悲歡
凌墨言愛著冷冽,從五歲開始,足足愛了二十年。冷冽恨著凌墨言,恨她暗中搗鬼趕走自己此生摯愛,恨她施展手腕逼得他不得不娶她。這場婚姻困住了冷冽,同時也成了凌墨言精致的牢籠。所有人肆意踐踏她的自尊的時候,尚未成形的孩子從她的身體里一點一點流掉的時候,冷冽始終冷眼旁觀嘴邊掛著殘忍的笑。“冷冽,我累了,我們離婚吧。”“離婚?別做夢了凌墨言,地獄生活才剛剛開始!”
80.2萬字8 2518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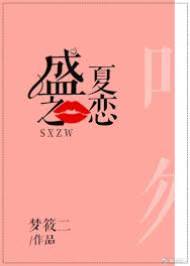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7.92 9024 -
完結143 章

透明的雪
盛衾從小性子溫和淡然,除了偷偷暗戀一個人多年以外。 做過最出格的事,莫過於在聖誕節的雪夜表白,將多年的喜歡宣之於口。 這次表白距離上次見宴槨歧已經有兩年多。 男人一頭烏黑的發變成了紅色,看上去更加玩世不恭。 他被一群人圍在中央,衆星捧月,人聲鼎沸中看向她,神色淡漠到似乎兩人並不相識,雪落在他的發頂格外惹眼。 等盛衾捧着那顆搖搖欲墜的心,用僅剩的勇氣把話講完。 四周幾乎靜謐無聲,唯獨剩下冷冽的空氣在她周身徘徊,雪花被風吹的搖晃,暖黃色的路燈下更顯淒涼狼狽。 宴槨歧懶散攜着倦意的聲音輕飄響起。 “抱歉,最近沒什麼興致。” 那一刻,盛衾希望雪是透明的,飛舞的雪花只是一場夢,她還沒有越線。 —— 再次重逢時,盛衾正在進行人生中第二件出格的事情。 作爲紀錄片調研員觀測龍捲風。 無人區裏,宴槨歧代表救援隊從天而降。 男人距離她上次表白失敗並無變化,依舊高高在上擁有上位者的姿態。 盛衾壓抑着心底不該有的念頭,儘量與其保持距離。 直到某次醉酒後的清晨。 她在二樓拐彎處撞見他,被逼到角落。 宴槨歧垂眸盯她,淺棕色眸底戲謔的笑意愈沉,漫不經心問。 “還喜歡我?” “?” “昨晚你一直纏着我。” 盛衾完全沒有這段記憶,呆滯地盯着他。 宴槨歧指節碰了下鼻子,眉梢輕挑,又說。“還趁我不備,親了我一下。” —— 雖不知真假,但經過上次醉酒後的教訓,盛衾怕某些人誤會她別有居心,癡心不改,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他卻步步緊逼。 有天被忽視後。 宴槨歧懶散地靠着車門,睨她:“看見了,不知道叫人?” “我覺得,我們不是可以隨便閒聊的關係。” 片刻後,盛衾聽見聲低笑,還有句不痛不癢的問話。 “那我們是什麼關係?” 盛衾屏着呼吸,裝作無事發生從他面前經過。 兩秒後,手腕毫無防備地被扯住。 某個混球勾着脣,吊兒郎當如同玩笑般說。 “之前算我不識好歹,再給個機會?”
33.8萬字8 1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