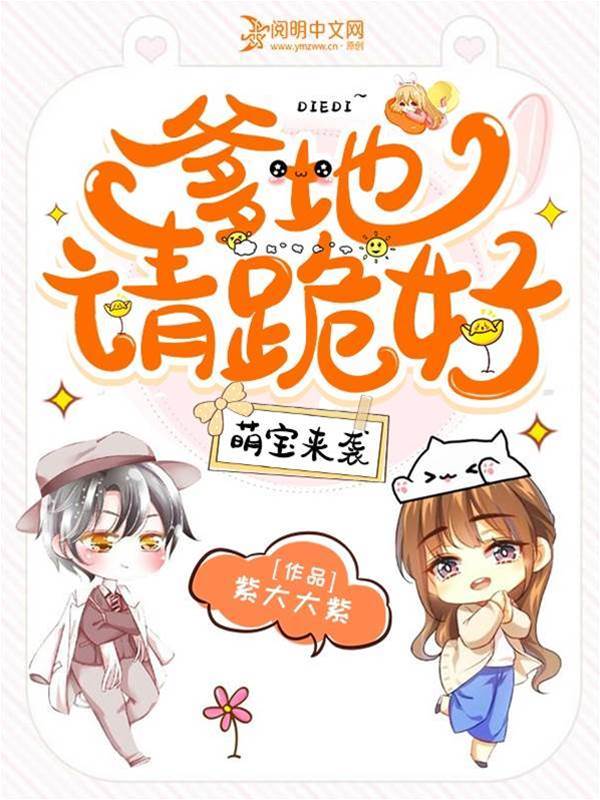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上癮》 第46章 第46章
黑的SUV開進小區, 緩緩地停在了柳煙家別墅門口,聶攰剛點的那煙還沒完,他靠在椅背上, 眼眸看著二樓的方向,那U型的臺紗窗飄了出來,輕輕晃。
但看不到屋里的況, 不過從另外一個窗戶可看到里面燈已暗。
聶攰咬著煙沉默地看著,等著。
夜深人靜。
小區里偶爾有家養狗的聲。
聶攰開了車門, 朝大門走去,隨后他站在大門口, 著口袋看著二樓的方向。
*
家里按的監控, 有三個人可以查看, 監控電視就放在陳姨的房里。有時起床時會看一眼。
今晚剛睡下沒多久便想起一樓還有扇窗戶沒關, 便起, 隨意地朝監控里看一眼。
這一看,醒了一大半, 門口有個高大的男人手外套看著二樓。陳姨把畫面放大,突然覺得那像是聶先生。
愣了愣, 披上外套, 走出客廳去關窗戶, 順便看向門口那人。
寸頭。
棱角分明的眉眼以及狹長的眼眸。
是他。
陳姨想起睡前去看柳煙, 柳煙手機響了一次又一次, 但都被柳煙給掛斷了,陳姨當時沒怎麼注意, 難道當時打電話來的人是聶先生?
這讓想起了六年前那一幕。
聶先生也是這樣, 在樓下站了一個晚上。
Advertisement
陳姨想了下, 還是上了樓, 來到柳煙的房門口,屈指敲了下門,大約敲了五分鐘后左右。
柳煙才踩著拖鞋,披著外套一臉睡意地打開門:“陳姨,這麼晚了,什麼事?是爺爺....”
“不是,老爺子睡得好好呢,是....”陳姨遲疑了下,道:“聶先生在樓下。”
柳煙一愣,擰眉,“什麼?”
“他在門口,我剛剛在監控里看到的。”
柳煙的睡意了很多,想起今晚那十來通的電話,頓了頓,轉走向U型臺,開了窗簾往外看。
一眼便看到樓下那高大的男人,對他實在是悉得很,一下子就能認出來。柳煙靠著玻璃門,抱著手臂看了幾秒。
陳姨跟進來,低聲道:“要不要把人進來。”
柳煙一把拉上窗簾,說道:“不必,我睡了。”
說完。
就朝床走去。
陳姨見狀,也只得說道:“那我先出去了,你...你要是睡不著就下來找我。”
柳煙掀開被子,含笑道:“嗯,放心吧,陳姨。”
躺下。
陳姨只能離開,輕手輕腳地給柳煙關上了門,在門口站了一會兒,仔細一想,覺得,可能是聶先生又做錯了什麼吧。這樣的話,也是站在柳煙這邊的,于是也沒再猶豫,下樓回了房。
*
Advertisement
柳煙閉眼,腦海里浮現聶攰的影,輕輕地嘖了一聲,翻躲進被窩里,能站就站著吧。
六年前下雨天他都能站。
六年后的好天氣也繼續站吧。
柳煙有時是真討厭聶老爺子那張,聶家就清清白白聶家就高貴嗎?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的。
可是商人就很差嗎?很差嗎?
想起自己立的慈善基金會,每一年都往山區藏區送送吃的,幫助山區建房子修路。
這難道不是貢獻?
呵。
翻來覆去,柳煙一直翻來覆去,總覺得熱,但醒了其實也不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總算是睡著了。
這一覺。
到早上六點多。
天蒙蒙亮。
柳煙看了眼腕表,起,抓了抓頭發,隨后拉開了窗簾往外看,那高大俊朗的男人還站在那里。
柳煙瞇了瞇眼,轉回浴室洗漱,換了一長,柳煙打開門,陳姨正扶著柳老爺子下樓。
柳老爺子見到柳煙立即道:“你看到門口的人沒?”
柳煙走過去,從陳姨手里接過,語氣淡淡:“你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
柳老爺子帶著幾分研究地看著,“昨晚在生日宴會上聶老頭是不是又說什麼難聽的話?”
“你怎麼沒跟我說。”
柳煙:“有什麼好說的,我跟林裴一起呢,他肯定要張刺一下的。”
Advertisement
“這個臭老頭,你都不喜歡聶攰了,他還刺你?國家怎麼不收了這人啊,禍害啊。”柳老爺子氣得吹胡子瞪眼,他是開始蓄胡子了,有人說蓄胡子長命百歲,他還想親眼看到孫結婚生孩子。
所以他也開始蓄了。
短短的胡子吹都吹不,柳煙看著笑起來,“爺爺,不要生氣,沒必要跟他生氣。”
“所以聶攰是替他爺爺來道歉的?”
柳煙瞞了一些事,笑著嗯了一聲:“可能吧。”
柳老爺子一邊下樓一邊道:“看著可憐啊,要不,讓他進來吧,黎城這冬天晚上是真冷的,要是在我們門口凍冒了,聶老頭又得怪我們上。”
主要是他看聶攰順眼了。
柳煙:“是他自己要站的,跟我們有什麼關系。”
柳老爺子看了眼心的孫,一時沒了話。兩個人吃過早餐,柳煙去練瑜伽,柳老爺子打發陳姨去看看,聶攰還在不。
陳姨回來了點點頭:“還在,確實是站了一個晚上,眉梢都寒意凜凜。”
柳老爺子看了眼孫的瑜伽室,沉默幾秒,說道;“把人請進來喝杯熱茶吧,然后再把他勸走,大白天的門口站個人,等下路過的人看著以為我們家怎麼了呢,罰啊。”
陳姨也覺得是。
說,“我這就去。”
說完,陳姨手,走出家門,穿過院子。聶攰掀起眼眸,看到陳姨,尊敬地站直了子。
陳姨嘆口氣,說道:“聶先生你這又是何必呢?與其在這里站著,不如去勸一下聶老爺子,留點兒口德。”
聶攰低了低頭:“抱歉,我這本就是來道歉的。”
“你來道歉有何用啊?”陳姨無奈,隨后,走上前,“聶老爺子不是戎馬一生嗎?一人做事一人當,怎麼讓孫子給擔著,真是可惜了他這個份....”
鐵門剛開。
一輛黑的轎車也跟著停在門口,接著老周下車,把聶老爺子扶下車,聶老爺子從后座里提了十幾份的禮袋,朝這邊走來。
他神有些僵地看著陳姨,“你好,是小陳吧,多年未見,還好嗎?”
陳姨愣愣地看著聶老爺子。
下意識地看了眼聶攰。
聶攰手口袋,垂眸看了眼聶老爺子手里的禮袋,聶老爺子沒敢看孫子,走上前,像是要進門,他笑道;“我來拜訪柳老頭,看看他。”
陳姨看他不等自己邀請就要走,立即手攔了下,“等等,聶老先生,我先通報一聲。”
聶老爺子:“.....行。”
老周在一旁捂了下眼。
微嘆一口氣。
猜你喜歡
-
完結566 章

顧先生的金絲雀
c市人人知曉,c市首富顧江年養了隻金絲雀。金絲雀顧大局識大體一顰一笑皆為豪門典範,人人羨慕顧先生得嬌妻如此。可顧先生知曉,他的金絲雀,遲早有天得飛。某日,君華集團董事長出席國際商業會談,記者舉著長槍短炮窮追不捨問道:“顧先生,請問您是如何跟顧太太走到一起的?”顧江年前行腳步一頓,微轉身,笑容清淺:“畫地為牢,徐徐圖之。”好友笑問:“金絲雀飛瞭如何?”男人斜靠在座椅上,唇角輕勾,修長的指尖點了點菸灰,話語間端的是殘忍無情,“那就折了翅膀毀了夢想圈起來養。”
159.6萬字5 1757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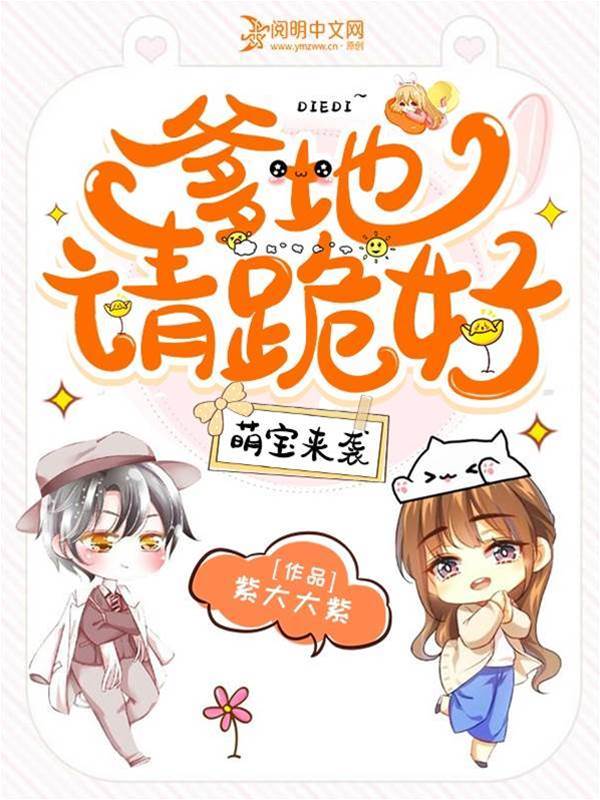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83 章

墜落
周挽X陸西驍陽明中學大家都知道,周挽內向默然,陸西驍張揚難馴。兩人天差地別,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誰都沒有想到,有一天這兩人會站在一起。接著,流言又換了一種——陸西驍這樣的人,女友一個接一個換,那周挽就憑一張初戀臉,不過一時新鮮,要不了多久就…
32.4萬字8 6560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30461 -
完結1 章

又是落花時節逢君
“向老師,你真的要申請離開去南疆支教嗎?那邊教學條件極差,方圓百里都找不到幾個支教老師。”看著向晚拿來的申請材料,校長有些疑惑。 畢竟她還有兩個月援疆期就圓滿結束了,這個節點上她卻突然申請去更遠更偏僻的地方繼續支教。 向晚扯起一抹笑意,聲音平和卻異常堅定:“是,校長。我已經向組織重新申請了兩年,我要去南疆。” 見她去意已決,校長也不在挽留,直接在申請書上蓋章:“等組織審批,大概十天后,你就可以走了。” “不過這事你和江老師商量好了嗎?他把你當心眼子一樣護著,怎麼能舍得你去南疆那邊。” 向晚面上一片澀然。 全校都知道江野是二十四孝好老公,對她好的就像心肝寶貝一樣。 可偏偏就是這樣愛她入骨的男人,竟會出軌另一個女人。 這叫向晚有些難以理解。 難道一個人的心,真的能分兩半交給另一個人嗎? 她搖搖頭堅定地表示:“不用跟他說了,反正他援期也快結束了。” 校長不明所以地看了她好幾眼,終究是沒開口。 剛走出門就收到黃詩琪發來的照片,還沒點開看。
3萬字8 1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