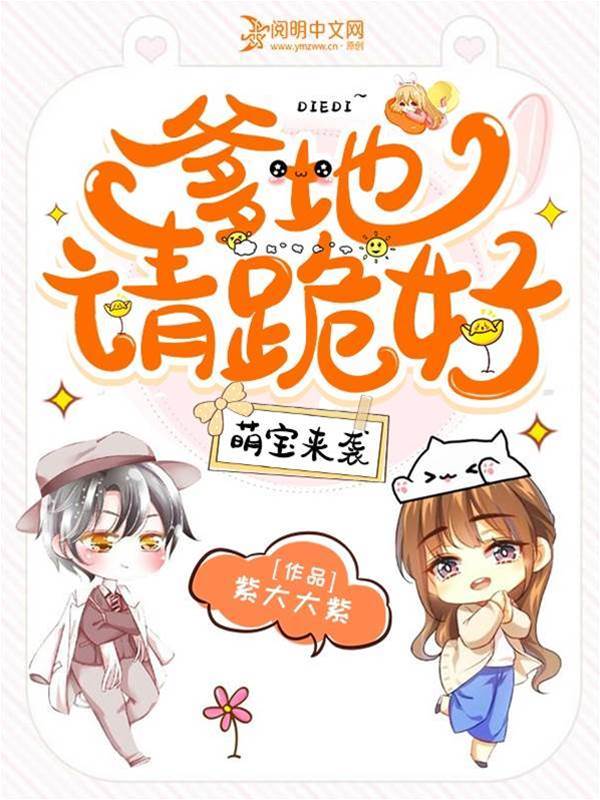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漂亮后媽看到彈幕后[七零]》 第53章 第 53 章
這話一落,姜舒蘭的臉蛋瞬間紅,輕輕推了推對方,“周中鋒。”
輕輕的聲音,聽在周中鋒耳朵里面,心跳如擂鼓,他往旁邊側了側,聲音忐忑,“舒蘭,我們結婚了。”
姜舒蘭睜大眼睛去看他,不知道自己這會多人,眼如,像是個勾人的妖。
姜舒蘭期期艾艾地嗯了一聲,手攥著服,盡管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還是會忍不住的張。
“合法的夫妻。”
周中鋒低語道,目灼灼中著幾分忐忑。
姜舒蘭答答地嗯了一聲。
抬手推他,催促,“周中鋒,你別這樣看我,你把燈拉了好不好?”
這話,仿佛是無聲的邀請。
周中鋒翻起來,拉滅燈繩,下一瞬間。
屋陷了黑暗。
男人并沒有想象中的出手,而是雙手都放在肚子上,規矩的不像樣子。
“舒蘭,你熱嗎?”
姜舒蘭嗯了一聲,額頭一直都是汗珠兒滾落,是的,也是張的。
“我也是。”
“舒蘭,你嗎?”
“舒蘭,你嗎?”
“舒蘭——”
姜舒蘭聽不下去了,翻了個,在周中鋒臉上輕輕地啄了下,“周中鋒,你是在張嗎?”
那一瞬間。
周中鋒好像不會呼吸了,臉一下子火燒一樣,他結滾,半晌,也沒能說出一個字。
“好像確實張。”
姜舒蘭一雙的小手,放在周中鋒的前,男人的心跳如擂鼓,在這安靜的房間,仿佛咚咚咚,一聲高過一聲。
周中鋒哪里得起姜舒蘭這般調戲,他一雙大手下意識的捉住姜舒蘭的小手,欺覆過來。
姜舒蘭驚呼一聲,剩下的所有聲音,都被吞了進去。
連帶著窗外的月亮,都被進了云層。
Advertisement
深夜,姜舒蘭半夢半醒間,去推著不知疲倦的男人,“周中鋒,我明兒的要上班。”
聲音迷迷糊糊,還記得自己早上要去食堂。
算是保留著唯一的一清醒。
周中鋒頓了下,在額頭上輕輕啄了下,聲音低沉,“我給你請假。”
姜舒蘭輕輕地嗯了一聲,太累了,一雙眼睛沉沉的睡了過去。
而男人雖然滿頭大汗,但是心里眼里卻說不出的高興,那種渾的都仿佛被再次激活的覺,讓他到了從來沒有過的另外一面。
熱沸騰,心滿意足。
難怪人家說,溫鄉英雄冢。
原來,是這樣的。
周中鋒的摟著,低眸在臉上看了片刻,然后忍不住笑了笑,是那種腔發出的笑意,帶著幾分震。
“姜舒蘭。”
他低頭在發上啄了下,聲音也是說不出的溫。
跟怎麼也喊不夠一樣。
“姜舒蘭。”
在額頭上啄了下。
“姜舒蘭。”又在眉上啄了下。
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
因為幫姜舒蘭請了假,周中鋒不用的趕早去食堂削洋芋,早上五點的時候,生鐘再次醒來。
只是,在察覺到旁邊有個人的時候,周中鋒僵了下,在看到姜舒蘭睡的昏天地暗的。
他忍不住又勾了勾,把人往懷里帶了帶,在帶過來的同時,幾乎是下意識的親了親對方的額頭。
跟怎麼也親不夠似的。
姜舒蘭被胡子扎的忍不住蹙眉,嚶嚀了一聲。
周中鋒瞬間僵住,保持著一個作好久,見徹底睡后,把抱到了隔壁床上,又把昨兒晚上胡鬧的半宿的床單被罩給扯了。
破天荒的,他沒有去晨練,而是端著大盆,一大早就在院子里面洗洗刷刷。
Advertisement
隔壁,老人覺淺,一大早那就在院子里面伺弄地上的菜園子。
聽到靜覺得稀奇,喊了一聲,“小姜?”
小姜怎麼起這麼早洗服??
周中鋒被單的手,跟著頓住,半晌,遲疑地接話,“那嬸子,是我。”
這下,一墻之隔的對面也跟著安靜了下來。
那手里摘的黃瓜,吧嗒掉在地上,“你在給小姜幫忙洗服?小姜呢?”
周中鋒回頭看了一眼窗戶,忍不住笑了笑,“舒蘭還在睡覺,我們小聲一些。”
那頓住,忍不住倒吸一口氣,“小周,昨兒的孩子們尿床了?”
不然,實在是想不到,為什麼一大早小周就在院子里面洗服了。
而且聽音兒,還不像是小服,倒像是床單被罩這些。
周中鋒看了一眼床單上的一抹梅花漬。
他沉默。
院墻那邊,那擺手,“哦哦哦,我懂我懂,大人會尿床也是正常的,不怕你笑,我老太太都六十多了,去年還尿過床呢。”
周中鋒,“……”
周中鋒終于忍不住開口了,“那嬸子,沒人尿床!”
“那你這是?”
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沒見過哪家掙錢本事業的男人,一大早在院子里面洗床單被罩呢。
這要是說出去,怕是海島上都沒人會相信。
這邊的男人,大多都是大男子主義,別說洗床單被罩了,就是讓他們自己洗自己的衩子,他們都不會手的那種。
周中鋒能怎麼解釋?
難道說,昨晚上和姜舒蘭兩人胡鬧了半宿,弄臟了床單被罩?
當然,這種話是不能說的,床笫之間的事,怎麼能告訴外人?
周中鋒思來想去,胡扯了個借口,“我們家舒蘭,不適合涼水,所以我才來洗的。”
Advertisement
等了半天,沒想到等到這麼一個答案。
歸究底,還是小周心疼媳婦。
那沉默了,語氣帶著殷切的期盼,“小周啊,你以后多來找下我們家了西關。“
那西關是那團長的名字。
周中鋒有些不解,那讓他去找那團長做什麼?
就聽見那繼續了,“你多找找我們家西關,然后平日里面怎麼對小姜的,你都跟我們家西關說一遍,日子久了,我們家西關也能像你這樣疼媳婦。”
兒媳苗紅云這麼多年生不了孩子,這是他們家最大的問題。
苗紅云這個兒媳婦不錯,是真不錯。
所以,也格外疼對方,只是現在還活著,還能管著西關。
怕將來自己沒了,西關的事業越來越好,那兒媳婦紅云日子就難了。
沒孩子的人,到最后有多難,那是最清楚不過的了。
不然,當初也不會收養西關了。
這一招雖然險,但是確實是賭對了。
周中鋒挑眉,沒想到是這個原因,他頷首,“那嬸子,我會的。”
那剛要道謝,聽到臥室傳來的呼嚕聲,突然就冷笑一聲,“小周啊,我就不打擾你了,我先回屋了。”
三分鐘后。
那抄著搟面杖,一把掀起了那團長上的被子,手里拿著一個搪瓷盆,搟面杖敲搪瓷盆,在那團長耳邊敲的砰砰作響。
那團長一個鯉魚打,“出事了嗎?”
“出事了嗎?”
等他一站起來,看到床旁邊是那的時候,頓時驚了下,“娘,你這是做什麼?”
那冷笑一聲,“隔壁家的小周都在洗床單了,你還在睡,你哪里有臉睡?起來,去把你昨兒的才換下來的服,自己洗了。”
那團長,“……”
那團長狠狠地了一把自己臉,“娘,服不是一直是你和紅云洗的嗎?”
當然是紅云洗的多。
“怎麼?我們就天生該給你洗服啊?那西關我告訴你,我這還是只讓你洗你自己的服,知道隔壁小周洗的是誰的嗎?他洗的是全家大件床單被罩,就因為他媳婦不能涼水。”
“你呢?你也知道你媳婦不能涼水,你怎麼還讓紅云洗?再說了,昨兒的紅云才被困,你做了啥?你除了指責紅云,你還做了啥?”
那團長都被罵懵了。
真的被罵懵了,任誰剛醒來被一頓劈頭蓋臉的罵,都是懵的。
那團長也不例外,他跳下床,求饒,“娘,我去洗,我現在就去洗。”
他要是在多說,多解釋兩句話。
他怕他娘,連他剛結婚的舊賬都被翻出來。
那才是一個沒完沒了。
五點一刻。
那團長穿著背心,睡眼惺忪的站在院子里面,拿著一個盆子,盆子里面裝著的都是他昨兒的換下來的服。
聽到隔壁傳來的服倒水的嘩嘩聲。
那團長都三十的人了,這會卻悲憤的要命,“周副團,你說你做什麼不好?一大早你洗什麼服啊!?”
這不把他給害了嗎?
隔壁,周中鋒洗干凈一條床單,又換下一條,在聽到那團長的話時,他挑眉,“我洗的我家的服。”
又不是洗的那家的。
那團長這般啥語氣?
“你洗服就算了,我也被喊起來洗服了。”他一個大男人洗什麼服啊!
還一大早起來洗服。
這不折磨人嗎?
周中鋒突然想到了什麼,“還有十五分鐘,拉練開始,等拉練結束后,我還會去食堂打早飯,我們家舒蘭早上起不來做早飯,等吃完,我還會把碗筷都洗了,另外,堂屋的衛生也該打掃了,還有家里的水缸該挑水了,地里面的野草該拔了——”
“這些都是我的活,有問題嗎?那團長?”
當然有!
那團長,“打住!”他本聽不下去。
但是,在院子里面的那老太太都聽的津津有味,甚至還頗為流的打了個響指,“西關,都安排上。”
那團長,“……”
殺了他算了!
做什麼要跟周副團做鄰居?
猜你喜歡
-
完結566 章

顧先生的金絲雀
c市人人知曉,c市首富顧江年養了隻金絲雀。金絲雀顧大局識大體一顰一笑皆為豪門典範,人人羨慕顧先生得嬌妻如此。可顧先生知曉,他的金絲雀,遲早有天得飛。某日,君華集團董事長出席國際商業會談,記者舉著長槍短炮窮追不捨問道:“顧先生,請問您是如何跟顧太太走到一起的?”顧江年前行腳步一頓,微轉身,笑容清淺:“畫地為牢,徐徐圖之。”好友笑問:“金絲雀飛瞭如何?”男人斜靠在座椅上,唇角輕勾,修長的指尖點了點菸灰,話語間端的是殘忍無情,“那就折了翅膀毀了夢想圈起來養。”
159.6萬字5 1757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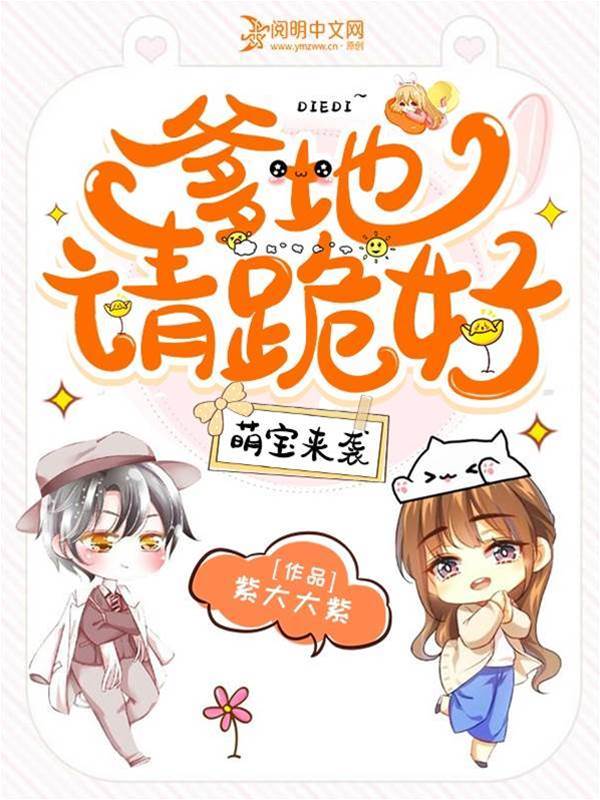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83 章

墜落
周挽X陸西驍陽明中學大家都知道,周挽內向默然,陸西驍張揚難馴。兩人天差地別,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誰都沒有想到,有一天這兩人會站在一起。接著,流言又換了一種——陸西驍這樣的人,女友一個接一個換,那周挽就憑一張初戀臉,不過一時新鮮,要不了多久就…
32.4萬字8 6560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30461 -
完結1 章

又是落花時節逢君
“向老師,你真的要申請離開去南疆支教嗎?那邊教學條件極差,方圓百里都找不到幾個支教老師。”看著向晚拿來的申請材料,校長有些疑惑。 畢竟她還有兩個月援疆期就圓滿結束了,這個節點上她卻突然申請去更遠更偏僻的地方繼續支教。 向晚扯起一抹笑意,聲音平和卻異常堅定:“是,校長。我已經向組織重新申請了兩年,我要去南疆。” 見她去意已決,校長也不在挽留,直接在申請書上蓋章:“等組織審批,大概十天后,你就可以走了。” “不過這事你和江老師商量好了嗎?他把你當心眼子一樣護著,怎麼能舍得你去南疆那邊。” 向晚面上一片澀然。 全校都知道江野是二十四孝好老公,對她好的就像心肝寶貝一樣。 可偏偏就是這樣愛她入骨的男人,竟會出軌另一個女人。 這叫向晚有些難以理解。 難道一個人的心,真的能分兩半交給另一個人嗎? 她搖搖頭堅定地表示:“不用跟他說了,反正他援期也快結束了。” 校長不明所以地看了她好幾眼,終究是沒開口。 剛走出門就收到黃詩琪發來的照片,還沒點開看。
3萬字8 1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