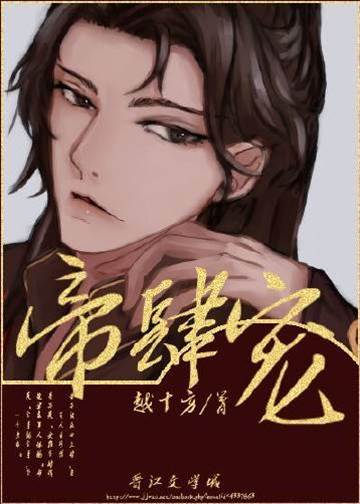《怎敵她軟玉溫香》 第67章 第67章
喬沅眨眨眼, 直起子:“大壯,你醒了。”
小人眼神無辜,眼睫纖長, 坐姿優雅漂亮,一點也沒有干壞事被抓包的樣子。
大壯眼神逐漸清明。
他還記得即使后來夫人被他擺弄得哭都哭不出來的時候, 還拖著綿無力的想從他邊逃跑, 因此意識清醒的第一刻就是地抓住的手。
“別走……”
他的力氣出奇的大, 一點兒也不想剛從暈倒中醒來的病人。
喬沅在那場事中已經力竭, 強撐到現在,大壯都沒用多大力氣,喬沅就跌進他懷里, 鼻尖撞上堅的膛。
小人了鼻尖,細白手搭在他肩上,正要推開他, 卻覺掌下強健的軀幾不可見地著抖。
大壯地抱著, 確認夫人還在,才有力回想自己暈倒前的事。
暈之前那種似乎即將撥云見日的清明被那錐心的疼痛打斷, 他極力想找回那種覺,卻不得其法, 剛褪去的疼痛又要卷土重來。
喬沅見他神不對,連忙環住男人脖頸,轉移他注意力:“罷了,想不起就算了,大夫說一切自有定數。”
這樣想下去不出問題才怪,若是到時候好不容易恢復了, 腦子落下什麼病就麻煩了。
大壯果然不想了,撐著額頭緩了緩, 轉而目沉沉地看,顯然還記得兩人還未解決的爭執。
“夫人還沒有什麼想說的嗎?”
這完全是個無解的局,他認定自己被當替,偏喬沅又不能直說,他自己就是他一直耿耿于懷的“已死”鎮國公。
方才只意識不清時說的幾個字眼都鬧到大半夜請府醫,喬沅現在完全不敢輕舉妄了。
大壯盯著,鼻梁高,角繃,著堅持的意味。
Advertisement
他的因暈倒還泛著白,他平日里強壯,渾都似鐵疙瘩,冬日里都是用冷水沐浴,鮮見這樣脆弱的時刻。
小人無措地跪坐在床上,到底是有些愧疚,片刻,主湊過去抱住男人的腰,白臉蛋著他的膛蹭了蹭。
“別生氣了。”
大壯低頭,小人又湊近,泛著香氣的瓣在他角落下一個吻,帶著討好意味。
若不是心虛,怎麼會這麼乖。
大壯眼里最后一亮熄滅,這是默認替的事了。
再沒有比知道自己只是心上人懷念舊人的影子更難過的事,尤其活人是永遠也比不上死人的,夫人的亡夫不在了,他在心里就永遠是最好的樣子。
喬沅見他這樣也不好,抱住他脖子,綿綿地著他:“方才府醫說你腦的淤清得差不多了,三日后就可以恢復記憶。”
大壯轉了轉眼珠,沒有一喜悅,這麼大的事仿佛都與自己無關。
有時候他都覺得自己太過冷,也許他的朋友親人都還在等著他回去,但失去記憶的這段時日,他卻很想這些,似乎夫人一人就足夠占據他所有的心神了。
小人還在生疏地開導他,嗓音綿綿的,“到時候你再回頭看,會覺得現在的這些不算什麼。”
好一個不算什麼。
大壯心里陡然生出一暴戾,角僵直:“夫人是想和我劃清界限,待我恢復記憶,就趕我走?”
喬沅有些懵:“我何時說過要趕你走?”
大壯此時已經聽不進任何話,他陡然生出一焦躁,迫切地想確認什麼。
喬沅趴在他肩上,細發鋪散在他前,大壯偏了偏頭,映眼簾的是人纖長脆弱的天鵝頸,瑩白細膩,線條得讓人心。
Advertisement
“是替也好,不是也罷,我都認了。”
男人的氣息越來越近,突然耳邊傳來男人狠厲的聲音,“總之,夫人是我的,這輩子也別想擺我。”
喬沅正疑,脖子突然傳來一陣疼痛。
大壯在咬。
喬沅嗚咽一聲,使勁想掙開大壯的懷抱,卻被腰間的鐵臂錮得不能,只能被迫仰著細白的天鵝頸。
小人嚇得直掉眼淚,差點以為大壯要直接咬死了。
好在大壯似乎很快就清醒過來了,松開箍著的手,喬沅連忙捂著脖子退到床角。
似乎嚇壞了,水眸里蓄著眼淚,要落不落,“你發什麼瘋!”
大壯抿了抿,湊過去拿開的手。
潔白瑩潤的雪上綻放點點胭脂,像是一塊人的糕點,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頭有一個牙印,紅紅的一圈。
男人盯著這個烙印似的標|記,眼眸幽深。
喬沅氣急,“快去拿鏡子!”
等大壯拿著鏡子回來,一把奪過,張兮兮地對著鏡子左看右看。
之前太過張,總覺得很痛,以為都要出了,實際鏡子里呈現出的沒那麼嚴重。
咬的人剛開始確實下了力氣,抱著非要留下標|記的決心,只是到底舍不得,中途又突然歇了力,因此印記邊緣很淺,看樣子過不了多久就能消。
喬沅最了,一雪瑩潤無瑕,似是上等的羊脂玉,若是落了疤,都要恨死大壯了。
大壯抿了抿,盡管不需要,他還是轉從妝臺上拿出一大堆瓶瓶罐罐。
夫人弱,饒是他平日在榻間還算控制些力氣,但一場事下來,總會留下些痕跡,因而他也習慣了收集些消腫去疤的香膏。
大壯指腹挖了厚厚一層,輕輕抹在牙印上。
Advertisement
牙印上還覆蓋了一圈啄吻的痕跡,星星點點,充分展示了那人輾轉反側,又又恨的緒。
喬沅現在也覺得自己委屈死了,難道是不想把事說出來的嗎,明明是為了他好,憑什麼就被這樣對待?
方才他還在祠堂對做那樣的事,喬沅現下上還疼著,都還沒追究,結果又被咬了一口。
越想越氣,等大壯上完藥,惡狠狠地推開他,“出去!”
大壯作一頓,漆黑眼珠看了半晌。
他現在像是變了一個人,以前就算是裝,也要在夫人面前裝出些溫的假面,如今眼神間總帶著兇,似是咬住獵就死不松口的兇。
喬沅本來還在生氣,被他看得又有點怕,白玉似的手指蜷了蜷,不自覺著角。
上只穿著一件漂亮單薄的寢,方才見外人時只在外頭加了一件披風,順的綢襟因剛才的掙扎散開,出致的鎖骨和泛著暈的渾圓肩頭。
偏還渾然不覺,只一雙水眸張地著他。
坐在床上,微微仰著頭,更像一只貴的小貓了,雪白,漂亮矜貴,偏偏脆弱得沒有一點自保能力。
若是遇到什麼不正常的主人,說不定還會被關進漂亮的小房子里,每日里穿著仙氣的小子,得到心照顧,但是不被允許見任何外人,是獨屬于一人的珍寶。
大壯還在盯著,喬沅心里打鼓,正要默默地后退,卻見他突然出手,幫把落的領口合上。
溫熱指尖在雪上停留一瞬,然后收回。
喬沅驚得后退,卻見大壯收拾好瓶瓶罐罐,轉出去了。
*
自那晚不歡而散,兩人之間的氣氛就變得有些微妙。
在回莊子的馬車上,連綠袖都察覺到不對勁,趁著國公爺回去取東西,連忙問喬沅:“夫人可是和公爺吵架了?”
吵架?喬沅有些迷茫,應該算是吧。
和齊存的行事天差地別,在嫁給他之前,還以為婚后兩人都會鬧得不得安寧,然后在茍且的婚姻里慢慢蹉跎,沒想到不知不覺竟過到了現在。
喬沅認真想想,這竟然還是兩人第一次真正意義的爭執,偏偏源頭還是因為一個虛無縹緲的替。
如今大壯還是如以前一樣細地照顧,兩人晚上也依舊同床,男人強地要摟著睡,掙開一點都不行,卻難得安分地不再手腳。
但確實是有不一樣了,大壯的行事強了不,節慶剛結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安排馬車回莊子,似乎一刻也不能忍在公府待下去。
喬沅事先一點都不知,早晨睜開眼才發現自己在行走的馬車上。
綠袖小心翼翼勸道:“夫妻間哪有不發生口角的,若是有什麼誤會,說開就好了。”
喬沅扣了扣懷中枕上的花紋,眼睫垂下,默不作聲,線偶爾從窗簾的隙中進來,照在白里紅的臉蛋上,連細小的絨都清晰可見。
綠袖看夫人這樣,也不好多說,待大壯取完東西回來了,自覺地下車到后頭的馬車上。
大壯手里拿著一個纏枝紋樣的錦盒,不知是什麼重要的東西,本來行程都走到一半了,他非要折返回去。
喬沅移開視線,偏他還湊過來,獻寶似的打開錦盒。
竟是一副東珠頭面,在線下熠熠生輝,流溢彩。
喬沅一懵,隨后臉上爬滿紅暈,不敢置信:“你還收起來做什麼!”
還以為這東西早就被扔了,乍一看到,腦子里全是那日的荒唐畫面,渾都快燙了。
大壯輕輕噬咬冒著熱氣的耳尖,聲線低啞含糊:“扔了多可惜,夫人別惦記那支釵了,瞧這個多好看。”
好看確實好看,一副耳鐺上還用金纏繞繁復的圖案,喬沅想到了什麼,氣急敗壞道:“你還把這些珠子給匠人師傅了?”
大壯趕忙解釋:“沒有,我請教了珍寶閣的師傅,這幅頭面是我自己做的。”
他先是用普通的珍珠跟著匠人聯系,然后才慢慢自己用東珠打造了這幅頭面。
他怎麼舍得讓別人看到那些珠子,上頭沾了夫人的氣息,外人一下他都恨不得砍掉他們的手。
大壯觀察了一下夫人的臉,補充道:“夫人放心,做之前把珠子都潔凈了的。”
——那也不行!
喬沅到這幅頭面都覺得燙手,唰的一下合上蓋子。
如果大壯的目的是想讓不要想著那支釵,那麼他現在達到了,因為一想到釵就會聯想到東珠頭面,恨不得從此再不要聽到關于這兩樣東西的字眼。
等回到莊上,整理好行頭,大壯還試圖把這幅頭面混進喬沅平日用的首飾盒,可惜被識破,一一挑出來,準備放到最不顯眼的地方積灰。
大壯表甚是憾,之后也沒放棄,熱衷于包辦喬沅的一切食住行,幾乎要把邊所有的件都換一遍,鐵了心想讓與過去斷絕關系。
喬沅懶得管他,隨他去折騰,自己吃吃喝喝,等著他兩日后恢復記憶。
提出要去看喬母,被大壯以“天氣太過炎熱,恐出門中暑”的理由擋回來,喬沅模糊覺不對勁,但此時確實快到伏暑,不宜出門,也就沒有在意。
傍晚,兩人坐在秋千架上,喬沅坐在男人懷里,迷迷糊糊地仰著腦袋被他親。
有人路過,這時候外人只知大壯是鎮國公夫人跟前的紅人,應是不清楚其中的親,喬沅驚醒,推了推他的肩膀。
大壯垂眸,按住的手,十指叉,加深了這個吻。
那個下人仿佛沒看到秋千架上的旖旎,遠遠地繞了另一邊的路。
喬沅這時才驚覺,回來之后的莊子和以往已經大不一樣。
按理來說,如今大壯藏了份,喬沅是這莊上唯一的主人,偏偏他不知道怎麼做到的,把下人都換了一遍,提出什麼要求,下人得先去回報給大壯,請示他的意思。
不止如此,大壯還以夫人邊伺候的人為由,撥了幾個小丫鬟,在他不在莊上時,這幾個丫鬟就寸步不離地跟著夫人。
喬沅從喬府到公府,邊的丫鬟還過麼,再多幾個人也沒什麼,本沒放在心上,直到在一次用膳時,從湯勺的反面看到后丫鬟低眉順眼的臉。
猜你喜歡
-
完結245 章
愛妻如命之一等世子妃
大婚前夕,最信任的未婚夫和最疼愛的妹妹挑斷她的手筋腳筋,毀掉她的絕世容顏,將她推入萬丈深淵毀屍滅跡!再次醒來的時候,殘破的身體住進了一個嶄新的靈魂,磐涅重生的她,用那雙纖纖素手將仇人全部送進地獄!爹爹貪婪狠戾,活活燒死了她的孃親,搶走了她價值連城的嫁妝?用計把嫁妝翻倍的討回來,讓渣爹身敗名裂,活埋了給孃親陪葬!妹妹口腹蜜劍,搶走了她的未婚夫,得意洋洋的炫耀她的幸福?那就找來更加妖嬈更加勾魂的美女,搶走渣男的心,寵妾滅妻,渣男賤女狗咬狗一嘴毛!繼母狠毒,想要毀掉她的清白讓她臭名昭著,成爲人人可以唾棄的對象?用同樣的手段反擊回去,撕開繼母仁慈僞善的假面,將她狠狠的踩到泥濘裡!她手段殘忍,心狠手辣,視名聲爲無物,除了手刃仇人,她沒有別的目標,然而這樣的她依然吸引了那個狡詐如狐貍一樣的男人的目光,一顆心徹徹底底的爲她沉淪,併發誓一定要得到她!片段一:"你這個喪心病狂的女人連給露兒提鞋都不夠格,怎麼配做本王的未婚妻,定情信物還回來,別死皮賴臉纏著本王不放!看到你這張臉本王就覺得噁心."氣焰囂張的男人一手摟著溫柔似水的美人,一手指著她的鼻子罵道.
142.8萬字5 65928 -
完結286 章

神醫毒妃手下留情
一次意外,她和自己養成的偏執九皇叔在一起了。“幼安,你得對我負責。”“……”“請立刻給我一個夫君的名分。”震驚!廢物王妃和離之后,轉頭嫁給了權傾朝野的九皇叔。下堂婦?不好意思,她21世紀的外科女博士,京都第一神醫。窮酸鬼?各大藥行開遍全國,…
70.1萬字8 70228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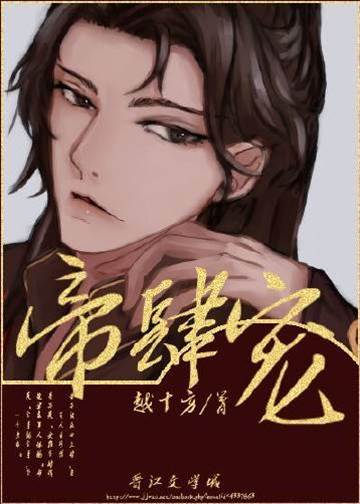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
完結296 章
恃寵為后
容晞是罪臣之女,入宮后,她將秾麗絕艷的姿容掩住,成了四皇子的近身婢女。 四皇子慕淮生得皎如玉樹,霽月清風,卻是個坐輪椅的殘廢,性情暴戾又孤僻。 宮人們怕得瑟瑟發抖,沒人敢近身伺候,容晞這個專啃硬骨頭的好脾氣便被推了出去。 一月后,四皇子讓容晞坐在了他的腿上,眾宮人驚。 六月后,四皇子的腿好了,還入東宮成了當朝太子,容晞卻死了。 慕淮面上未露悲郁之色,卻在一夜間,白了少年...
45.5萬字8 42165 -
完結149 章

摔鳳冠!剛和離攝政王就抬來聘禮
家破人亡前夕,沈玉梔匆匆出嫁,得以逃過一劫。成婚第二日,丈夫蔣成煜帶兵出征。她獨守空房三年,盼來的卻是他要納她的仇人為妾。沈玉梔心灰意冷,提出和離。蔣成煜貶低她:“你不知道吧,那夜碰你的人不是我。你帶著一個父不詳的孽子能去哪?還是識時務些,我才會給你和孩子名分。”春寒料峭,沈玉梔枯坐整個雨夜。第二日,帶著兒子離開了將軍府。全京城都等著看她的笑話時,那個冷厲矜貴、權勢滔天的攝政王霍北昀,竟然向她伸出了手!“本王府上無公婆侍奉,無兄弟姐妹,無妻妾子嗣,唯缺一位正妃。“沈小姐可願?”後來,前夫追悔莫及跪在她身後,攥著她的裙角求她回頭。霍北昀擁緊了她的腰肢,用腳碾碎他的手指:“你也配碰本王的妃。”沈玉梔不知道霍北昀等這一天等了十年。就像她不知道,在她做將軍夫人的那些年裏,這個男人是怎樣錐心蝕骨,痛不欲生過。
26.4萬字5 230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