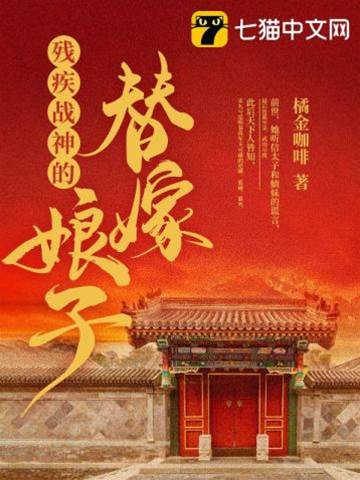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207章 第 207 章
“過宮刑的,是沒法自如排尿的。唉,這孩子,大概是從不在陌生地方解手的。”
唐荼荼是聽著,就要難死了。
南邊靜海縣巡衛衙,又一波焰火轟然上天,漫天的彩與煙塵經風一吹就散。
月澄明,人間的愁與苦全升不上天。
*
初五,就算是過完了年,京城家家戶戶門前攢了一地的紅鞭屑兒,都揮著掃帚出來掃,掃完了拜一拜,喊個“諸事大吉”,點把小火燒了。
一季的糧草和十萬床棉服棉被一齊上路,竟用了五萬輜重兵。
從京城一路行出通州,兩側百姓夾道歡迎,最多時候一條街上聚了幾萬百姓,出了通州城,空氣才算是通暢了。
晏昰回著不見頭的車隊,角一捺,燥郁升上了臉。
京城都夸皇家娘娘們心慈,棉被用的是八斤重的棉花,十萬套棉被要防,包裹起來就是百萬斤。
Advertisement
只看斤秤確實不算多,可棉被跟糧草不同,糧草一車能堆垛千斤,棉被捆扎嚴實,一車裝不下十床,一路淋霜雪,送到邊關還得等天暖和的時候晾曬。
紀氏挑頭出這主意,果然是蠢貨。
上百面彩旌高揚,那是各式各樣的儀仗旗,舉旗的小兵練久了,行走步速都有規矩,那麼大的旌旗鼓著風,走得拖拖拉拉的,全是在耽誤輜重兵腳程。
一群影衛默不吭聲,護著馬車圍了兩圈,把吹號敲鼓的樂兵攆得遠遠的,就怕殿下不高興。
晏昰無甚表,了東南方向,又算算行程,起碼還要走六天,難免了點心思。
初五了。
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胖了沒,瘦了沒,天津口味習慣沒,想我……咳。
心尖上仿佛有螞蟻挪步,得止不住。晏昰低低喚了聲:“馮九,你過來。”
Advertisement
一名長相俊俏的影衛應了聲,打馬靠近,附耳過來,才聽殿下說了一句話,這影衛臉立馬驚悚起來了。
聲音都變了調兒:“小的哪里敢……”
被二殿下瞪了一眼,只好趕鴨子上架了。
負責輜重的副將俞丘明一路警惕,不停跑前跑后巡視著。
他看見殿下莫名其妙地從馬車鉆出來,換了騎馬,筆直筆直坐在寒風中,披風也不穿。
吹了半天風,突然就染了咳疾,吭坑咔咔一聲接一聲的,又從馬上換到了馬車里。
俞丘明驚得不輕,把殿下給吹得風寒了,真要怪罪起來這是他的罪責,連忙請了軍醫過來。年侍衛卻寒著一張臉,說他們隨行中有大夫,不用心。
與此同時,一隊普通裝束的騎兵岔了另一條道,朝著天津方向沖去了,馬蹄如飛,濺起滾滾黃塵。
俞丘明數了數,一二三四五六,六個人,張兮兮地又來請示。
Advertisement
車里的二殿下咳了兩聲,聲音有氣無力的,啞著嗓說:“本殿用他們辦點私事兒,你不必置意。我頭疼得厲害,想清靜清靜,你不要聲張,每日把飯食送來就行。”
不要聲張……
俞丘明想起那些“二殿下宿有頭疾”的約約的傳聞,心里一咯噔:頭疾可大可小,但放皇子上,這就是要命的大事。
二殿下鐵骨錚錚,能讓他疼得氣虛無力的頭疾必然是大疾,絕不能傳揚出去!
他一骨碌翻下馬,跪地打千:“殿下只管好好靜養,末將以項上人頭發誓,決不讓任何人靠近此車一步!”
作者有話要說:大家久等啦~狀態不佳,調整了兩天,繼續肝!
猜你喜歡
-
完結3305 章

嫁給帝君之後
(正文已完結!!!)特戰女王戚流月穿越成了暴君棄妃,強者的尊嚴豈能被人踐踏!為了美好的生活,我們還是好聚好散離婚吧! 某暴君冷冷的看著她:想和離?冇門! 於是戚流月在某暴君的縱容下,開始了禍國禍民禍天下的道路…… “王爺,王妃在城南開了一家男妓院。” “嗯,封了吧。” “王爺,王妃幫你找了一堆的妾室回來。” “嗯,休了吧。” “王爺,王妃把皇上的寵妃給揍了。” “嗯,揍的好。” “王爺,王妃她扔下和離書跟人私奔了。” “臥槽,她還反了不成?”
286.3萬字8 66517 -
完結414 章
王妃真給力
她意外跑到古代,成了奸臣的女兒還沒有娘疼。指婚給他,他卻在新婚之夜給她點上守宮砂,對她說;「做了本王的妃就得承受住寂寞。」哼,俺可不想在一棵樹上弔死,俺會在周圍的樹上多試幾次滴找個機會離開他,自主創業是王道、王爺在尋她,說沒寫休書她還是他的王妃、風流倜儻的俠士說領她一起笑傲江湖、太子登基之後也在等她,說皇后的寶座只有她才有資格坐、NND、頭大了、選誰好呢?
119.6萬字8 92584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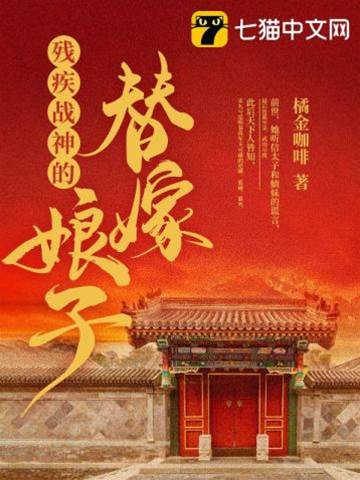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連載304 章

王府繼兄寵我如寶,親哥卻后悔了
前世聞星落嘔心瀝血為父兄籌謀前程,終于熬到家族顯赫的那天,卻被突然回家的姐姐奪走了父兄的寵愛和與太子的婚事。直到死,聞星落才知道原來父兄這些年一直厭惡她心機深沉、精于算計,他們只愛單純柔弱的姐姐。 再次睜開眼,聞星落回到了爹娘和離的那年。 這一世,姐姐突然改口要跟著父親,還揚言她將來會當太子妃。 聞星落果斷放棄父兄,隨改嫁的母親進入王府。 豈料前世對姐姐不屑一顧的王府繼兄們竟將她寵成至寶,而昔日厭她入骨的父兄們看著她喚別人父兄,為別人籌謀算計,紛紛紅了眼,卑微求她回家。 繼兄們把他們統統擋在外面:“落落是我們的妹妹!” 那位矜貴孤傲的王府世子爺,更是將她霸氣地護在懷里:“她是我的,只是我的。”
54.4萬字8 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