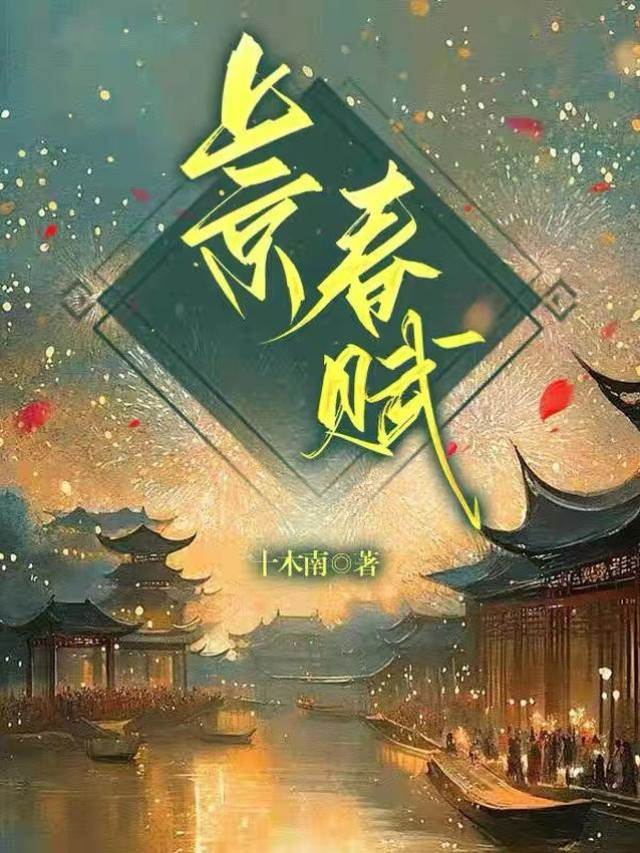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枕叔》 第61章 061
第六十一章
封岌打量著寒。換了寢,臉上的面紗也摘了。上帶著一點沐浴之后特有的染著氣的淺香,頭發被挽起,后頸和鬢間的一點發還是被打了。尤其是臉頰側一縷,著的臉頰,發尾橫在臉上的疤痕之上。
封岌的視線順著那縷發,向臉頰上的疤痕。這樣一張的芙蓉面之上,臥著這樣明顯的一條長疤實在是很顯眼。
他抬眼,向寒的眼睛,問:“每日可都按時兩次上過藥了?”
寒點頭:“剛剛沐浴之后便上過藥了。”
寒說謊了。
封岌給的那瓶治療臉上疤痕的雪凝膏,一次也沒有用過。臉上的疤痕,是假死離開封岌之后的護符,并不想除掉這道疤痕。
寒輕推封岌搭在后腰的手,繞過去,在封岌右側坐下。這樣渾然不覺地藏起了自己的右臉,便可以只左臉面對他。
可沒有面紗遮擋,屋的線實在是讓心里不太舒服。不喜歡臉上的疤痕就這樣毫無遮擋地暴在封岌面前。一想到等會兒他必然會近距離地看著,說:“我去熄燈。”
站起朝桌上的燈火走去。著那簇燈火,寒眸浮現了一茫然,著燈蓋的手久久不能落下。
親手將事推到這一步,可真到了這一步,心下恍然。事到如今,也不清楚自己能不能真的將戲演到真。
該如何藏起抵和抗拒,扮演眷著郎的娘與他抵纏?可若不如此,又怎麼打消他的懷疑?
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若狠不下心腸,該怎麼了結這一切?
自知道他是赫延王,寒從始至終只想著和他了斷,從未有過一息想要與他在一起,從未。
Advertisement
從未。
他有不能家的誓言相錮,依然免不了很多名門貴的青睞。待他日山河定誓言破時,他的婚事將會是怎樣的惹眼?人踏破門檻,又或者優秀郎們主示好,都是可以預見的景。
在那個時候,嫁給他?想想都覺得有些荒唐。寒幾乎可以想象到時候旁人驚訝地問“赫延王為什麼會娶”時的驚詫表。
為什麼會娶?
他有太多選擇,他對不過是錯差之后得不到的征服罷了。若當真了,拿自己的一輩子去當賭注是可笑愚笨的做法。若對他沒便也罷了,也了心難免會困在其中一敗涂地。
有些人有些只適合放在心里,冒險走進去只會被現實摧毀得滿目瘡痍,又何必讓份珍貴的愫最后狼狽收場。
很多事,寒承擔不起。
借住在姨母府上守孝期勾搭上姨丈的兄長,這罪名實在是太大了。若真如此,議論的不會是一個,還有姨母。如果因為這事使和姨母之間生出一嫌隙,簡直對不起姨母為了和娘家決裂。
一想到姨母對自己和妹妹的好,心里就萬不敢傷姨母一分一厘。
至于他?時日久了,待他日沒了婚事束縛無數人主撲上來時,他自有更多更好的選擇,不會在意一個已經“死”了的。
封岌著寒背對著他的纖薄背影,他眼底似乎有察一切的了然。他畔扯出一莫測的淺笑,他問:“你熄燈要熄半夜?”
寒著燈蓋的手一抖,回過神來。熄了燈,屋一瞬間暗下去。皎月發白的過窗紙灑進屋,勾勒出大致廓,讓屋不至于漆黑一片。
寒悄悄舒了口氣,著頭皮朝封岌走過去。心里藏著小小的期盼,盼著自己能演得真不被他看出不愿,甚至盼著他能魯些不要那麼細心覺察出的抵。
Advertisement
“將軍。”寒主靠過去,纖臂搭在封岌的肩上,于他后頸相勾。封岌抬手搭在的腰側,攬著躺下,他將寒攬進懷里,放在腰側的手輕輕了。寒安靜地伏在他懷里,閉上眼睛,一副任他采的溫順模樣,乖無邊。
可是寒等了很久,也沒等到封岌的其他作,他只是像很久之前一樣悠閑自在的偶爾一下的腰。他似乎很喜歡在沒有多的腰側一把細。
突然而至的腳步聲由遠及近。翠微在門外叩門稟話:“娘子,祁家娘子派人送了個魚缸過來。”
寒抬頭向門口的方向,蹙眉詢問:“山芙親自過來了?”
“沒有。只是派府里的下人送東西來。”翠微稟話。
封岌搭在寒腰側的手輕推了一下,示意去辦自己的事。
寒下了床,拉過床幔將封岌遮住,快步朝門口走過去。房門“吱呀”一聲拉開,寒向翠微腳邊的瓷魚缸。
只一眼,寒就明白了祁山芙為什麼送這個。
寒以前的閨房里有一個一模一樣的魚缸。祁山芙必是因為看見這魚缸和屋里以前那個一模一樣才派人送過來。彼時,曾對祁山芙說過屋子里養一點活,更有朝氣些。然后兩個人一起去挑選了很久才選中一個魚缸。后來與祁山芙親自去釣魚,也是花了心思,釣了很久才釣上來兩條干瘦的小魚養在魚缸里。那兩條小魚倒也爭氣,后來越養越。
寒著這個魚缸,恍惚想到了很久之前日長的靜好閨中時,角微彎,眸中浮現幾許。
彎腰,抱起這個魚缸,對翠微說:“明日再弄兩條鯉魚養著。很晚了,去休息吧。”
Advertisement
翠微瞧著寒眉眼間和的淺笑,也跟著笑起來。寒大多數時候都冷冷清清,很笑。翠微急忙說:“那我去打水,放在魚缸里困一晚,明天好養魚!”
說完,轉就跑。寒來不及阻止。寒轉進了屋,將魚缸放在桌上,又去了門口等翠微,不打算讓翠微進來,畢竟房里藏了一個人。
翠微很快提了一壺水回來給寒,寒沒讓翠微進屋,讓去休息。
寒提著這壺水回屋,看見封岌已經從床榻上下來,正立在窗前,背對著寒。窗戶關著,不知道他在看什麼。屋暗,寒也沒能看清。寒收回視線,提水走到桌旁。琢磨了一會兒,給那個魚缸調整了好幾次位置,最后才放在滿意的地方。
屋沒重新點燈,很昏暗。寒提水小心翼翼地將水灌進魚缸里。有幾滴水從魚缸里濺出來,濺在手背上,濺出一點涼意。做完這些,重新抬眼向封岌,見他還是背對著立在窗前。
寒緩步朝封岌走過去,直到立在他邊,才知道他在看窗下的那盆綠萼梅。
寒心里咯噔了一聲。
這盆綠萼梅,是祁朔千里迢迢從家鄉帶過來給的。
“是山芙給我送了魚缸。”說。
是祁山芙,不是祁朔。寒悄悄解釋。
可封岌還是沒什麼反應。
寒往前挪了半步,挪到封岌面前,手擁住封岌的腰,慢慢近他。著他,在他懷里仰起臉來。
封岌這才將目移回來,落在寒的眉眼,他說:“你今晚沒有半月歡影響?”
寒愣了一下。確實,前幾晚總是半月歡影響。可今晚因為先前專心寫東西,后因心事重重,并沒有讓半月歡發揮作用。
然而此時被封岌提起,寒心口突然就毫無征兆地滌了一下,生出幾許暖熱之意。
再往前挪一點,更他,然后踮起腳來在封岌畔輕輕親了一下。
“一直想著將軍的。”聲,向來清冷的聲線摻了一點。
半真半假。
起來的樣子,封岌還是有些不適應。封岌抬起的臉,去看眉眼間的溫,暫時不去深想此刻的溫有幾分是真。
他的沉默無作,卻讓寒心里有一些急。他是不是覺察到了什麼?寒一直沒有十足的把握完全騙到他。
寒悄悄咬了下牙,手拉過封岌的手腕,拉著他的手覆在心口。用低的聲音帶著一點央求:“里難,我要。”
的勾引太過明顯,可是封岌還是甘愿俯去吻。即使是連親吻這樣人之間最溫綿纏的舉,由他做來也有著不可拒絕和反抗的威之意。舌抵纏間,他恨不得吮卷口中所有的香意。
寒毫無回應之力。暴雨傾,芙蓉被澆了個凌。他的親吻,讓惶惶不可站穩。寒下意識手扶在封岌的臂膀,心里頓時踏實了些,只有扶著他靠著他才能得以片刻地站穩。
在寒沉睡的半月歡慢慢蘇醒,小蟲子啃咬一樣開始催促。在半月歡和封岌雙重的迫之下,寒覺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一些不該從口中發出的聲讓閉上眼睛。
被抱到窗臺上的時候,寒有片刻的清醒。后背抵在窗棱上,到一點涼,可這點涼氣抵消不掉心里的熱。有什麼東西掉落在那盆綠萼梅上面。
真與假錯。
寒猛地睜大了眼睛,悄悄藏著一委屈的眼眸被震驚狠狠撞上、替代。
“將軍!”急急地封岌,幾乎破音。
耳畔突然想起那日封岌湊近時,低語的第三件事。
封岌抬起頭來,帶著意味地輕輕一的臉頰。寒驚愕的眼眸睜得大大的,縱使是在未點燈的昏暗視線里,還是看清了封岌上的。
寒整個人都傻掉了,就連半月歡的熱也被嚇得煙消云散。
封岌看著呆怔的模樣,他拉過寒的手,將一個小瓷瓶放在手里。著實嚇得不輕,整個人呆呆的,封岌只好慢慢握住的手,讓握住那個小瓷瓶。
寒后知后覺地緩慢眨了下眼睛,孱聲:“避、避子湯嗎……”話一出口,又覺得不對勁。雖然沒有吃過,可大概也知道避子湯是苦的一碗湯藥,而不應該是這樣一個小瓷瓶。
垂眸,著手里的小瓶子。
“半月歡的解藥。”封岌道。
寒懵懵地著他:“解藥?半月歡有解藥?”
封岌去眼底的晦濃,努力讓自己的語氣沉穩正常些:“世間萬相生相克,皆有所解。”
他直起,往前再踏半步,將寒抱在懷里。他的手進后脊與窗棱之間,輕輕將的子徹底擁在懷里。
“我說過我不會讓你現在懷孕。”他克制低聲,“也不會讓你服避子湯那種傷的東西。”
彼時赴京路上沒什麼時,他尚且可以因為責任和道義而忍耐沒有真的要。如今將人放在心上,又怎麼可能讓困在擔心懷孕的惶恐里、讓承擔未婚孕的風險、讓心不甘不愿地付。
態度的轉變太突然,封岌又不是個傻子,哪里猜不到心里藏著小算計。對他的所有溫不過是假意服,另有他謀。
他不揭穿,是因為有些貪。
也是因為這是難得給他靠近的機會。
寒整個子被封岌抱在懷里,周圍都是他的氣息,還有一點暖甜的味道。寒握手里的小瓷瓶,茫然之后一時說不清是什麼心。
才想到一件事。他是赫延王,是無所不能的赫延王。就連這世上最醫湛的人也不過是他的私醫。其實若他想,他早可解了半月歡的毒。不必讓他自己困在半月歡的攪鬧里半月。
好半晌,近乎呢喃般詢問:“將軍自己為什麼不服解藥?”
很久之后,就在寒以為封岌并沒有聽見的話也不會作答時,封岌有些悵然地開口:“想知道可以想一個人想到何等程度。”
他略放開懷里的寒,垂眼看,幫將微的上整理好,又將堆在膝的擺推下去。他握住的腰,將人從窗臺上抱下來,道:“去吧,把解藥就水服下。”
猜你喜歡
-
完結41 章

東風惡,歡情薄
我不惜性命的付出,不如她回眸的嫣然一笑。
4.4萬字8 6828 -
完結117 章

嫁給大理寺卿後我真香
一盞牽緣燈,她賭上了一輩子的感情。成親五年,他不曾在她的院落裏留宿,她因此被背上了無所出的罵名。她愛了一輩子的裴燃居然還因她無所出,在她病入膏肓當天娶了平妻。當年大婚時,他明明說過這輩子隻有一位妻子的,那這位被賦予妻子之名的女子是誰......一朝夢醒,回到相遇前。就連薑晚澄也分不清哪是前世還是大夢一場。薑晚澄想:估計是蒼天也覺得她太苦了,重新給她選擇的機會。不管選誰,她都不會再選裴燃,她寧願當老姑娘,也不會再嫁裴燃。 薑晚澄發誓再不會買什麼牽緣燈,這燈牽的估計都是孽緣。可這位脾氣古怪,傲嬌又有潔癖的大理寺卿大人,偏偏賠她一盞牽緣燈。賠就賠吧,那她兩盞燈都帶走就好了。誰知道這位大理寺卿大人竟然說牽緣燈是他的心頭好,千金不賣......
21.2萬字8 28771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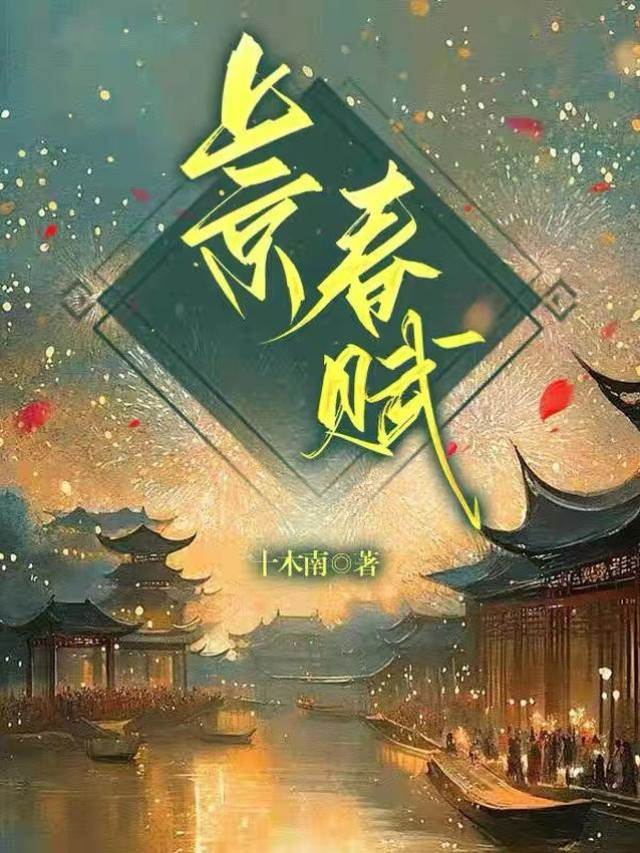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
完結133 章

重回暴君黑化前
昭寧三年,少帝病危,史官臣卿羣情激奮要處死蘇皎這個妖后。 她入宮五年,生性鄙薄,心胸狹隘,沒幫少帝料理好後宮,反而sha他寵妃斷他子嗣,硬生生將一個性情溫潤的少帝逼成了暴君不說,最後還一口氣把少帝氣死了! 羣臣:造孽啊!此等毒後必須一杯毒酒送上黃泉路陪葬! 蘇皎:我屬實冤枉! 寵妃是他親自sha的,子嗣是他下令zhan的,這暴君自己把自己氣死了,又關她什麼事? 然而羣臣沒人聽她的呼喊,一杯毒酒把她送上了黃泉路。 * 蘇皎再睜眼,回到了入宮第一年。 那一年的暴君還是個在冷宮的傀儡皇子,是個跟人說一句話就會臉紅的小可憐。 百般逃跑無果後,爲了不讓自己再如前世一樣背鍋慘死,她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阻止暴君黑化之路。 蘇皎勤勤懇懇,每天都在試圖用言語感化他,兼之以雨天給他撐傘,冷宮日夜陪伴,生怕他一個長歪,自己小命難保。 計劃實行之初卓有成效。 暴君從開始的陰晴不定,到後來每天喚她皎皎。 “你以後成了皇帝,一定要勤勉溫和,不要當個暴君,那樣是沒人喜歡的。” 少年眼中閃過幽暗。 “知道了,皎皎。” 蘇皎欣慰地看着他從皇子登上皇位,一身輕地打算功成身退的時候—— 小可憐搖身一變,陰鷙扭曲地把她囚在身邊。 “皎皎若是前世就這麼對朕就好了,朕和你都不必再來這一回了。” 蘇皎:? ! 這暴君怎麼也重生了? * 重回到冷宮最黑暗的兩年,拜高踩低的白眼,冷血無情的君父,一切都與前世無異,謝宴唯獨發現身邊的這個女人不一樣了。 她前世是個狹隘淺俗的人,今生卻斂了所有的鋒芒,乖巧小意地陪在他身邊,甜言蜜語哄着不讓他黑化。 起初,謝宴留她在身邊,是想看看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後來日日相伴,他沉溺於她溫情的哄,甜言的話,明知曉她沒有真心,卻還是飲鴆止渴般一頭栽了進去。 直到從冷宮出去之時,得知她要功成身退逃離的時候,謝宴終於忍不住徹底撕碎了這溫良的皮囊,眼神陰鷙地將她鎖在身邊纏歡。 華麗的宮殿門日夜緊閉,他聲聲附耳低語。 “你喜歡什麼樣子,我都能裝給你看。 皎皎,聽話乖乖留在我身邊,不好嗎?”
31.2萬字8 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