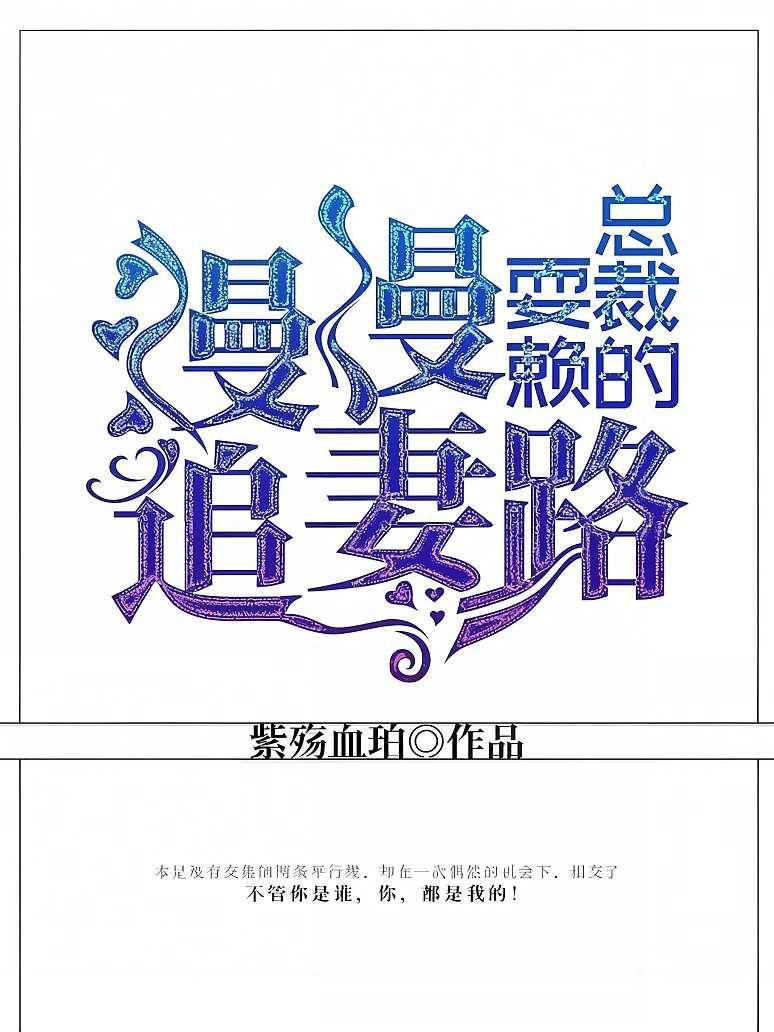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定制良緣》 第79章 先生的馬甲(43)
石璋趕到石家別墅前,發現整個別墅白的外墻都被熏黑了,玻璃全都掉,留下狼藉的窗框。
房子四周圍了許多看熱鬧的群眾,還有聞訊趕來的記者。消防人員來來往往撲滅了余火,有人正從別墅里抬出一蓋著白布的。
他踉蹌著走過去,掀起白布的一角,只看到滿目焦黑。
“你是屋主的兒子嗎?”消防員走過來問他。
“怎麼會突然失火?”
“初步判斷是客廳的電視發生短路,造的火災……一路燒到二樓,老爺子是不是腳不方便?”
石璋紅著眼睛點點頭。
“怪不得,所以沒跑掉。請節哀。”
石璋置若罔聞,默默走進失火后的屋子。
木質樓梯被燒得只剩下骨架,消防員把架的梯子撤走后,他暫時無法去二樓。
作為起火點的客廳附近燒得最嚴重,他蹲下,在電視的殘骸灰燼中拉。
被燒得漆黑的細小金屬鉤吸引了他的視線。
一連找出了十幾個金屬鉤,還有更多對應的小鐵圈。
這是……電視里面的什麼零部件麼?
他疑又迷茫地站起,在一樓的屋子里無目的地搜尋,直到蹭了滿灰塵。
石璋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只是很難有實,去接這突如其來的意外。
他的父親死了。
生他養他的人沒了。
他的家被燒了。
震撼的緒似乎過了悲傷,他覺自己飄在半空。
他穿過已經不存在的臺玻璃門,踩著一地玻璃碎片,走到花園中。
原本蒼翠的樹葉被煙熏得彩黯淡,樹蔭下有一個盆,盆里有一條鮮活的鯉魚,在僅剩半盆水中掙扎。
他在臺階上慢慢坐下,看著那條撲騰的魚,思考昨天午夜,他的父親是不是也是如此一般掙扎。
Advertisement
在睡夢中被煙火和高溫嗆醒,想要跑出去卻限于不方便的腳,只能徒勞地呼救可唯一能救他的保姆卻被他放了假。
最后只來得及從床上滾到地上,一步步向門口爬去,直到被火焰徹底吞噬……
“老東西……”他把頭埋進膝蓋里,喃喃道:“砸我電腦的帳還沒有算,你怎麼就死了呢?”
鯉魚又撲騰了一下,水花濺出盆外,求生反而加速了它的死亡。
石璋的手機一直在震,他沒心看,就這麼坐在花園臺階上,一直等到消防員和記者都散去了,才起,回到車里。
他趴在方向盤上,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想了很久,決定先取消今晚的新品發布會,然后再做打算。
拿起手機準備通知負責人的時候,安全部主任的電話打了進來,他之前已經打了很多個電話了。
石璋接起,聽到那邊傳來的大:“石總!那個雪魚又來了!”
石璋兩眼發花,差點暈過去:“上次侵之后,不是讓你們把后臺都堵死了嗎?怎麼還會讓他黑進來!”
“這次……這次是從我們天際部侵的”主任焦急地說:“總之石總你快點回來,防火墻快要撐不住了!”
石璋一腳踩下油門,汽車沖了出去。
“怎麼這麼魂不散,就盯著個長安不放?”他恨恨地說:“有這種技,干什麼不行?”
“不,這次他的目標不單單是長安,是我們上線的所有產品!”主任驚道。
“這麼大的胃口,也不怕撐死。”石璋眼眶通紅地瞪著前方,仿佛紅綠燈是自己的殺父仇人:“你不是說從我們部侵?那人還在大樓里面?”
“應該是的……”
“快點查啊,來個生人你們都沒發現嗎?”
Advertisement
“已經在調監控查了……”石璋幾乎能想象到電話那頭安全部主任滿頭大汗的樣子:“暫時沒發現生人啊。”
這個時段的通不算擁堵,但距離擺在那里,石璋趕慢趕還是花了將近半個小時才回到天際大樓下。
主任果然滿頭大汗地站在門口,連襯衫都汗了,在背上。
看到他來,眼神很是古怪。
“他已經進去了?”石璋視著下屬。
安全部主任閉著眼睛點點頭:“我們沒攔住。”
“人找到了沒有?”
“人沒找到,找到了他在用的電腦。”
“那不就等于找到了!”石璋怒道:“帶人去把他扣下來啊難得自投羅網!”
“是您辦公室的電腦……”
石璋仰頭看天,咆哮道:“沒完沒了了是吧!同一種手段反復用有意思嗎!”
上次用醉太平歌搭載病毒,這次用他的電腦侵天際,石璋算是明白了,雪魚就不是針對天際,而是專注地在搞他石璋。
怒火中燒,反而冷靜了下來,石璋大步走到電梯前,按下按鈕,卻發現毫無反應。
“他把電梯停了?”
“整個天際現在就是雪魚一個人的天下。”主任無奈地說:“只要他想,他還可以讓電短路失火,把大樓燒了。”
石璋眼神一凝,電火石間想通了許多。
“電梯停了,就是想讓我爬樓梯唄。”石璋冷笑著推開消防通道的大門。
“石總!”主任住他:“今天上午去了頂樓的……”
“只有洪書而已。”
石璋罵了一句臟話,三步并做兩步地向樓上爬去。
洪曉妝,洪曉妝,這麼明顯的事,他為什麼一直沒看明白?
“曉妝已經保研了,寧大計算機學院網絡安全方向……”虧他還曾經在酒桌上這樣驕傲地炫耀。
Advertisement
真相一直攤開了放在他眼前,他只是不愿意去看而已。
二十層樓爬到一半的時候,石璋開始覺得累。
不想到雪魚第一次侵天際的時候,就是把天際的電全部掐斷了。那個時候洪曉妝為了一份不太重要的急文件爬了二十層樓。
頂著膝蓋的傷病一步一步走上來的時候,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因為天際的電是掐斷的,為了不讓無辜的同事牽連,所以必須負起責任,主攬下這個送文件的任務。
石璋搖搖頭,抹了把臉上的汗,才發現了一手灰。
怪不得剛才安全部主任這麼看自己。
那次還摔傷了膝蓋,他背著下樓時,說了些很自私的話,利用了的喜歡。
應該是被狠狠傷到了吧?
所以現在要把電梯停掉,他一步步走上來,去會當時的心。
石璋想,這個人真是稚且無聊。
人和人的悲喜是不相通的,男人和人的想法更是如隔天闕,一個人是不可能會到另一個人的心的。
人連搞清楚自己的心都不容易。
他現在只想爬到頂樓,把從總裁辦公室的椅子上拎起來,然后掐死。
石璋著酸痛的大,想到雪魚侵長安的那次。
之前一直覺得雪魚的行神出鬼沒,像是隨心所的惡作劇,可如果把事簡化起因和結果,一切都真相都昭然若揭。
起因是那天醉太平歌和櫻桃甜甜結婚,解紅表示了反對和譴責。
結果是雪魚阻止了這件事。
就這麼簡單。
他只是不愿意去想而已。
所以解紅才能不病毒影響,保留完整的角形態,隨心所地唱歌。
雪魚第一次侵,向他攤牌,表明了的意。
雪魚第二次侵,他看明白了自己的心。
如今第三次侵,石璋約有預,覺得這個故事將要走向結局。
石璋站在二十樓,平復了一下急促的呼吸,推開防火門,走了出去。
曉妝坐在他的辦公椅上,看到他走進來,彎起眼睛笑了笑。
面前的電腦屏幕上有一條緩緩游的卡通魚。
“為什麼起名雪魚?”
洪曉妝托著腮:“當時還小,上語文課讀到李后主的曉妝初了明雪,春殿嬪娥魚貫列,覺得很喜歡,又正好嵌了我的名字,就這麼了唄。”
石璋走近兩步,從兜里掏出一把小東西,叮叮當當甩在桌上:“認識嗎?”
是他在火災現場發現的小金屬扣。
曉妝搖搖頭:“燒這樣,哪里認識。”
“我想了很久,發現我居然認識。”石璋說:“我在你肚子上見過這樣的痕跡。”
“是你的束腰帶,對吧?”他輕輕搖頭,好像在奇怪自己過于廣闊的知識面:“主要材質是棉綸和聚酯纖維,做助燃多好啊。”
“要不是這個金屬扣沒燒掉,簡直一點縱火的痕跡都沒有。”
曉妝輕笑:“毫無用的知識又增加了一點呢。”
“還有花園里的那條魚。”石璋沒有笑:“是吃的又不是看的,為什麼不在廚房里?”
“因為是你爸爸釣上來的魚,所以你不忍心它活活燒死。”
“所以,你要報警把我抓起來嗎?”眨眨眼睛,兩手平舉到他面前。
石璋突然暴起,一把揪住曉妝的領子,把按到墻上,大手無地死死卡住的脖子,聲嘶力竭地咆哮:“你連你爸釣的一條魚都舍不得燒怎麼敢活活燒死我爸爸!”
“你是不是真的以為這場謀殺天無?我爸平時睡眠很淺,我家地方又大,他卻一直沒有來得及呼救,你是不是給他吃了什麼藥?”
曉妝輕輕點頭:“是我平常吃的藥。”
在不和你在一起的夜晚,我不吃藥本沒辦法睡著。
半夜時對著電腦說要理點工作上的急事,然后隔著幾十公里路,遠程縱他家的電視短路失火當他的父親在烈火中掙扎的時候,他卻在和殺父仇人做。
這是多麼狠的安排,多麼強大的心理素質!
他恨到極致,也恐懼到了極致。
“我申請做尸檢,你以為你逃得掉?”
“你先殺了他,下一步是不是也要殺了我?殺了我你才能解氣?”
的脖子那麼細,石璋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完全握住,阻斷了空氣來源,曉妝的臉迅速憋得通紅,卻沒有踢打反抗,四肢綿綿地垂在側,雙眸平靜地注視著石璋。
那眼神平靜而悲傷,讓石璋想起了自己七歲時抱起那個四個月小嬰時的心。
“我你啊……我怎麼舍得殺你?”
為你付出那麼多,怎麼舍得讓你輕易死去?
眼神撞,緒洶涌翻騰,石璋覺得自己才是那個被扼住嚨的人。
他惡狠狠地,像是要吃掉一樣盯著瀕死的孩,許久。
突然用盡全力地,近乎撕咬一般吻了上去。
他們向野一樣啃咬彼此,分著鮮和疼痛的鐵銹味。
最強烈的恨只有一線之隔。
在雪魚第三次侵天際的那一天的某個時刻,在憎恨到達頂點時,石璋徹底上了洪曉妝。
作者有話要說:還有最后一章,結束本單元
洪曉妝的行為這里不作評價,但別惹理工是真
猜你喜歡
-
完結497 章

她攜財產離婚,前夫全球追妻
結婚三年,她始終得不到他的心,而他的白月光卻秀出鑽戒和孕肚,疑似好事近。本以為她會死纏爛打,她卻反手霸氣提出離婚,並要求他進行財產分割,一分都不能少!霍璟博不屑冷嘲:“你婚後好吃懶做,養尊處優,一分錢都沒賺過,還想分我身家?妄想!”不曾想,被離婚後的某天,有吃瓜群眾親眼目睹,不可一世的霍璟博主動獻上全部身家,抱著前妻大腿求複合:“老婆,再給我一次機會!”
91.2萬字8.17 59943 -
完結240 章

民政局門口我被求婚了,前夫哭了
【追妻火葬場+破鏡不重圓+修羅場+蓄謀已久+雙向救贖】【已完結】發現老公出軌后,林嬌毅然提出了離婚。 男人很是憤怒,以為是女人耍的欲擒故縱的把戲,決定給她一個教訓,便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他可以寵她,卻決不允許她騎在他的頭上。 而且她這麼的愛他,根本就離不開他,七天內必定哭著求他復婚。 賀霆自信滿滿,然而七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林嬌始終沒有出現。 再見時,林嬌的身邊已圍著無數個優秀的男人,包括他的雙胞胎大哥,賀家真正的掌權人賀冥。 賀霆慌了,尤其在民政局門口看到前妻接受別人求婚的時候,他哭了。 他哭著跪在林嬌的面前,卑微到了極點。“嬌嬌,我錯了,求你再愛我一次,不要嫁給別人好不好?” 然而林嬌只是摟著未婚夫,看著前夫,眼里已然沒有了一絲的愛意與溫度。“對不起賀先生,我早已經不愛你了,以后不要再叫我嬌嬌,請叫我大嫂。”
43.6萬字8 8029 -
連載278 章

她來邊境入隊,狼王夜夜燒水!
陸舒然第一次見顧驚絕,他就空手屠狼,血濺了她一臉。知道她是他未過門的妻子,也只是冷冷一句:“滾出獵戰團。” 第二次見面,她努力了一把終于留了下來,滿心歡喜以為男人軟化了,卻又被提醒:“少自作多情。” 獵戰團最后一面,她只在角落偷偷看他一眼,留下一封書信:“陸家要退婚,剛好遂了團長的心意,祝您早日覓得良人。” 顧驚絕卻如同被激怒的野獸,連夜駕著直升機追去:“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你當獵戰團是什麼地方?”
49萬字8 1838 -
完結23 章

深情錯付陌路人
“阿凌,簡兮要回國了,你還不把簡忻甩了?”門內傳來嘻嘻哈哈的打鬧聲,只有這句突兀又清楚地傳進簡忻耳里。 簡忻要推門的手縮了回來,無聲握緊了拳。 “怎麼,司少爺不會舍不得了吧?” “簡忻不就是個替身嗎?” 替身? 簡忻死死盯著面前的門板,呼吸一滯,迫切想聽到司亦凌的回答。 她在一起兩年的男朋友語氣漫不經心:“她算什麼替身,比不上小兮一根頭發。” 門內的眾人哄然大笑。 “對,連替身都算不上,只是你司亦凌的舔狗哈哈!”
2.6萬字8 1337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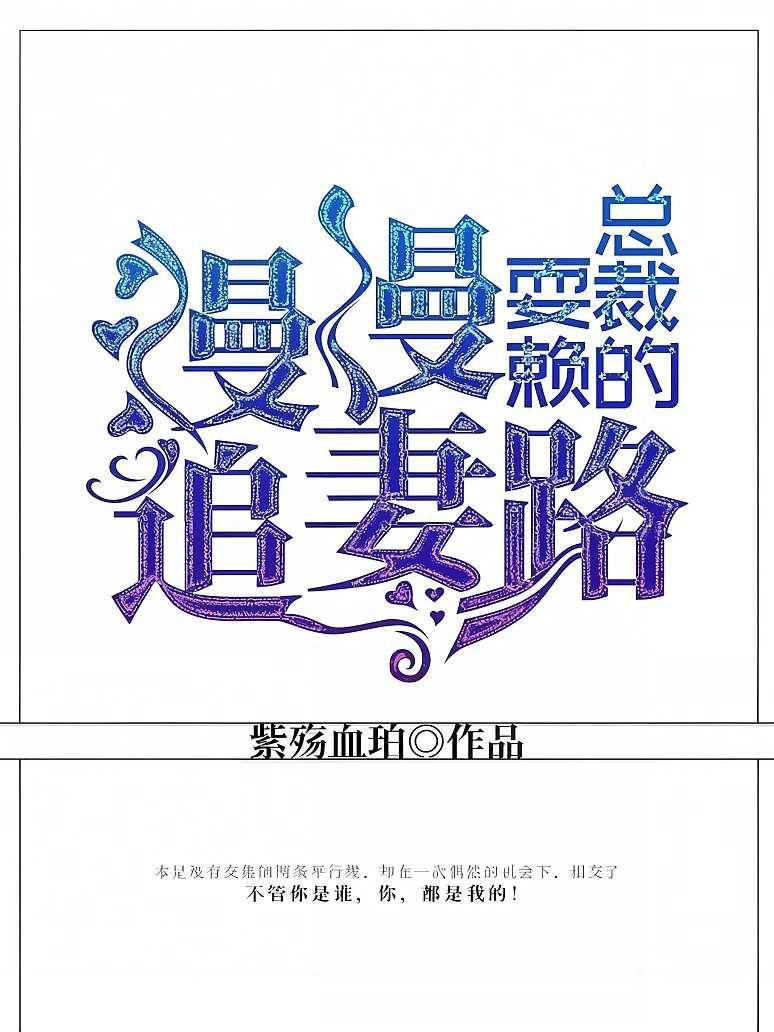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