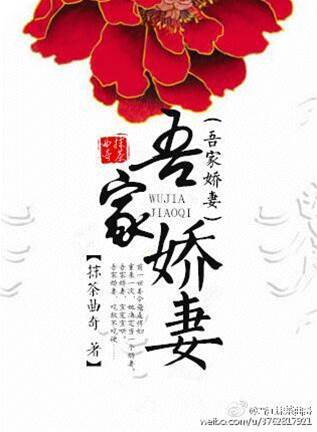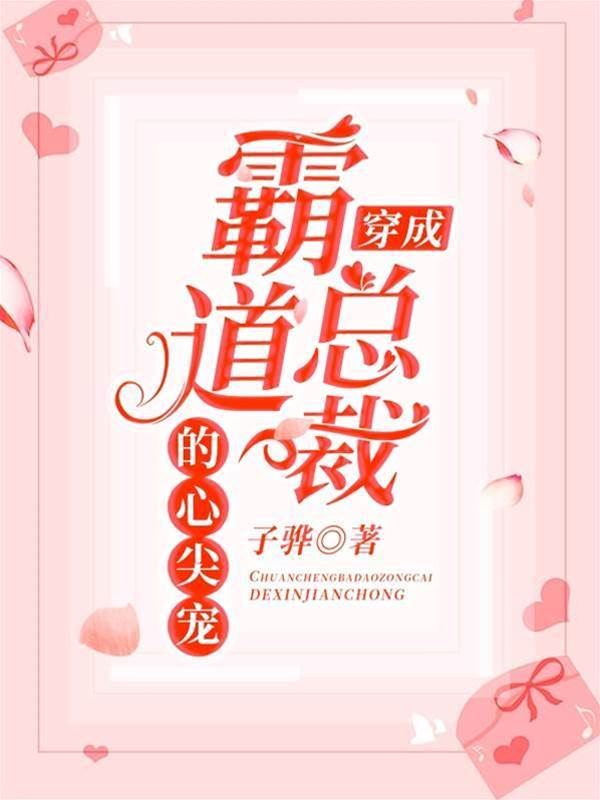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穿成流放男主的前妻》 第90章 第九十章
晨熹微,亮從欞格窗紗屋,屋中逐漸明亮。
虞瀅是在伏危的懷里醒來的,懵了半晌才反應過來。
——已經不是單了。
今日是與伏危談已經第五天了。
第—天,他們牽手。
第三天,他們相擁,齒相。
第四天,相擁而眠。
這進程屬實是快了些,可他們在這之前已經同榻而眠了許久,說快卻又不是特別的快。
虞瀅作輕緩的抬頭向呼吸輕緩的伏危。
便是從這個仰視的角度看著伏危,也還是完的。
虞瀅細細打量,才發現的他的睫很翹。
伏危現在還在睡,看來這幾日是真的累到了。
先是三日路程,而后又連著兩日都陪著周知縣去應酬,神都繃著,唯有關上房門,他才能松懈一口氣,怎會不累?
端詳片刻后,時辰也不是很早了,虞瀅打算起床梳洗出門,先去給知縣娘子送去口脂,再出門去買做面脂的材料。
正要起床時,卻發現伏危卻摟著的腰,摟得很牢固。
只是了他的手臂,伏危就醒了。
他半掀眼簾,問:“怎了?”
伏危剛醒時嗓音低沉沙啞,倒是出奇的悅耳。
虞灌道:“我準備起來梳洗。”
伏危聞言遲鈍片刻,在推了推他的手臂,他才恍然松開手臂,而后坐起。
虞瀅從床上下來,穿上外衫后,去梳理頭發。
“對了,我今日要去買做面脂的材料,也會去宋三郎那做面脂,可能會晚些時候回來。”
在床邊穿上外的伏危聞言,作一頓,略一斟酌過后才問:“可是只有你與宋三郎?”
虞瀅輕笑:“我會避嫌的,下午回去時,會喊上蘇姑娘一塊,正巧蘇姑娘的家也在附近。”
Advertisement
到底是孤男寡,在這個時代還是得避諱。
聞言,伏危暗暗呼了一口氣。
虞瀅轉頭看向伏危,說:“你前天帶回來的金簪,畢竟玉縣的當鋪比不得郡治的當鋪,所以我打算今日就去當鋪給當了,你覺得怎樣?”
伏危不怎麼在意:“既給了你,就由你做主。”
虞瀅點頭,隨而閑聊道:“昨日我去市集的時候,聽到旁人提起你,都說有一個坐著素輿,姓伏的年輕男子,在郡守府出盡風頭,五支箭,四支正中靶心。”
說到這,虞瀅瞇眼道:“我還聽說獎賞是一支金簪,還有與貌舞姬共度春宵。”
聽這麼一說,伏危怕誤會,忙解釋道:“我只要了金簪,絕沒有做旁的事,便是舞姬到跟前來,我也目不斜視,并未多瞧一眼。”
虞瀅掩一笑:“我又沒說你做了旁的事。”
說罷轉回頭拿起一個小瓶子,打開瓶蓋,用布團沾上些許的墨,然后涂抹在臉上。
伏危暗暗呼了一口氣。
虞瀅去端水回來洗漱。
洗漱后,又復而給伏危多打了一盆水回來。
虞瀅梳妝過后,便也就拿著昨日多做的口脂去尋知縣娘子。
到底是住在行館,伏危又是幕僚,這些天還是得去給知縣娘子請安。
再者與知縣娘子友好往來,也是百里無一害。
虞瀅去到知縣娘子的院子,才知知縣娘子今早一早就去寺廟上香了。
虞瀅把口脂留給下人,讓下人轉給知縣娘子,隨后才拿上從玉縣帶來的藥材出門。
虞瀅去市集買了做面脂的羊油和酒,隨后才拿著去攤子那。
蘇姑娘看到虞瀅,忙喊“東家。”
虞瀅笑道:“不過是小小一個攤子,喊東家也讓人笑話,不若就喊我余娘子就好。”
Advertisement
蘇姑娘有微微的驚訝,一時不知該不該喊,猶豫地看向一旁的宋三郎。
宋三郎點頭道:“就聽伏家弟婦的。”
蘇姑娘得到宋三郎的準許后,頓時朝著虞瀅出天甜笑意:“余娘子。”
虞瀅莞爾一笑。
最近天氣好,街上的行人也多了,不多時就有客人來瞧面脂,虞瀅便讓先去忙。
把材料放到攤子下邊,隨之低聲與宋三郎道:“我想去一趟當鋪,怕不大安全,你與我一塊去吧。”
手上到底有金子,一換就可能得十幾兩,這銀錢足夠在玉縣買下一宅子了,如何讓虞瀅不擔憂被人盯上。
宋三郎叮囑蘇姑娘看著攤子后,便與伏家弟婦一同去當鋪。
當鋪不遠,走個一刻左右就到了。
到了當鋪后,宋三郎沒有進去,而是在外邊等著。
虞瀅進當鋪,走到柜前才把金簪取出給掌柜。
掌柜看到是樣式致的金簪,耐人尋味地瞧向柜臺外穿著簡樸,貌不驚人的婦人。若是臟,倒也可比正常金價給收了,然后重新融化再做首飾賣出去,也是穩賺不賠的。
虞瀅覺得出來這掌柜的目有異,想是以為得金簪的渠道不明,或許現在心里也打著其他算盤。
例如——料準不敢聲張,從而價。
虞瀅微抬下頜,神從容不迫的道:“我這金簪來路清明,掌柜你便莫要胡猜想了,能給合適的價格我就死當,若價格不合適我就換一家當鋪。”
掌柜見自己的想法被這婦人看穿,尷尬地咳了兩聲,隨而問:“既然娘子說這金簪來路清明,不知可否告知是從何而來的?”
虞瀅皺眉,拿回柜臺上的金簪,道:“既懷疑是臟,那恕我不在此當了。”
Advertisement
當鋪掌柜忙道:“娘子莫惱,只是我們也是怕惹上麻煩,所以才如此一問。”
他斟酌了一下,說:“我先稱一下這簪子,再給娘子說價錢。”
說罷,他取出戥子看向婦人。
虞瀅斟酌片刻,還是把金簪給他稱了。
稱了重量,掌柜道:“一兩六錢,換做銅錢是一萬六千錢。”
這重量并未造假,與虞瀅掂量的也沒差。
說出重量后,當鋪掌柜繼而琢磨兩息,才給出一個數:“我出一萬六千二百錢收下,二百文的做工錢,已然是好價了,娘子不妨考慮考慮。”
虞瀅道:“我能接的價是一萬七千錢。”
掌柜驚道:“這位娘子可真敢說,一千錢的做工錢,哪家當鋪都不敢收呀。”
當鋪旁就是首飾鋪子,不用多想,這當鋪是首飾鋪子是一家的。
虞瀅道:“據我所知,金首飾樣式難做,越是復雜的樣式越貴,就我取來的金簪,樣式雖不是特別復雜,可勝在致,若是擺上鋪子出售,最都得十八兩銀子,我要一萬七千錢并不過分。”
掌柜搖頭,連聲道:“不不,一千錢的做工費還是太貴了,我頂多能出道五百錢。”
虞瀅琢磨了一下:“那便一人退一步,我能接的最低價格是一萬六千八百錢,低于這個價錢,我便不當了。”
當鋪掌柜擰眉猶豫,半晌過后還是點了頭,隨即問婦人是要銀子還是要銅錢。
銀子輕便,有銀子自然是最好的。
當鋪掌柜稱了十六兩銀子,又拿出八串銅板,讓婦人確認后再收下。
虞瀅檢查過銀子,再大概數一下銅板,確認過后才把銀子和銅錢放布包裹著,然后放籃子中。
虞瀅從當鋪出來后,與宋三郎道:“你先與我回一趟行館,等我把東西放下,下午收攤時再與蘇娘子一同去你那做面脂。”
宋三郎沒有意見,且半點都不好奇究竟當了什麼。
這時在對面街道上,有一個叼著草倚靠在墻上的二流子,不懷好意地帶著打量著婦人手中的籃子。
進去的時候是癟的,出來的時候卻漲了起來,顯然是當了好東西。
賊心才浮起,就見婦人與站在門口前的一個高壯的男主說話,然后一同離開。
二流子眉頭皺起。
方才怎就沒注意到這二人是一塊的?!
思索再三后,二流子還是扔下草,和站在不同方向的兩個人對上目,相互會意,然后分別行。
回去時,宋三郎笑道:“昨日我也在街市上聽說了伏家二弟在郡府的事,大家都在好奇那伏郎君是個什麼樣的能人。”
虞瀅笑了笑:“二郎自然是有本事的能人。”
二人有一句沒一句地閑聊著。
正在說話時,前方有一個穿著流里流氣的男子朝著他們走來,虞瀅時下戒心極強,所以在男子朝著自己側走來時,警惕地換了個方向,走到宋三郎的一側。
那男子沒有半點的端倪,徑自走開,不讓虞瀅懷疑自己是不是太過杯弓蛇影了。
宋三郎微愣,問:“伏家弟婦,怎麼了?”
虞瀅到底是擔心自己多慮了,然后讓宋三郎也跟著張,所以搖了搖頭,說:“無事。”
聲音才落,忽然被人從后一撞,因虞瀅警惕,所以很快就發現有一只手朝著籃子來,反應極快的一籃子,怒斥:“做什麼?!”
的聲音一出來,還沒等看清楚撞的人,那人就飛速地跑開了。
因虞瀅的聲音,引得旁人側目。
這時的宋三郎也反應了過來,知道他們被人盯上了!
但看著人逃跑,宋三郎腳步剛,但反應過來有可能是調虎離山,腳步頓下,不敢貿然去追。
虞瀅看向手中無恙籃子,呼了一口氣后,臉瞬間沉了下去,肅然道:“我們趕回去。”
銀子險些被搶,讓虞瀅心全然繃。這十幾兩銀子可是伏危的家當,若是真的被搶了,也不知如何與他代。
而且,現在不怕別的,就怕那些小是團伙作案。
若是團伙作案,就與宋三郎肯定是應付不過來。
憂心間,忽然聽到宋三郎驚訝道:“那不是伏家二弟麼!?”
虞瀅聞言,驚詫地看向宋三郎,再循著他的目去。
人來人往間,虞瀅與伏危對上了視線。
在這街市上看到伏危,虞瀅是驚喜的,而最驚喜的莫過于在看到他后的霍衙差和吳小衙差。
虞瀅原本繃著的那弦,頓時松了下來。
猜你喜歡
-
完結371 章

側妃謀略
南國第一美人軒轅蔦蘿上一世家族蒙冤,丈夫另娶,被即將進門的越泠然越側妃,逼迫身死。重生醒來,命運跟她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她變成了越泠然,這其中到底有多少陰謀,她的枕邊人到底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既然她重新活過,必然要讓局面反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84萬字7.75 27949 -
完結281 章

獵戶家的小悍妻
穿越成被父丟棄的小可憐腫麼破?顧南喬表示有仇報仇,有恩報恩! 原身因不願嫁給繼兄,被愛子心切的後孃暴打一頓,奄奄一息,怕惹上人命官司,親爹用破草蓆一卷,把她丟棄到深山。 好在山裡獵戶把她撿了去。 既來之則安之, 望著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農家,顧南喬擼起袖子努力乾,勢必要在亂世中,闖出一片天地! 一手種田,一手經商,從兩袖皆空的苦菜花到家財萬貫的富家翁,顧南喬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愜意。 名有了,財有了,該解決自己的終身大事了,她對著人美、心善、脾氣好的獵戶哥哥笑了笑。 啊喂,別生氣啊,獵戶哥哥,你不要誤會,我就是認錯了人,表錯了白。
168.7萬字6.5 92793 -
完結831 章

穿書後我成了首輔的心尖寵
宋綿綿穿進書裡,成了未來首輔的炮灰前妻。 和離? 不可能,這輩子都不可能……除非她有車有房有存款。 家裡一窮二白? 挽起袖子使勁乾。 種種田,開開荒,做做生意,攢點錢。 宋綿綿終於賺夠錢想要逃時,某人強勢將她拽進懷裡,“夫人,彆想逃。”
139.6萬字8.33 67906 -
完結2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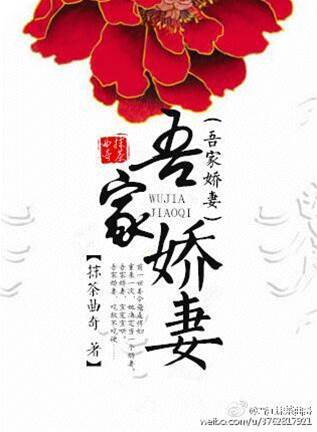
吾家妻寶
甜寵文~前一世薑令菀是個悍婦,成親五年都沒懷上孩子,偏生陸琮還寵她寵得要命,就差把心肝掏出來給她了。 重來一次,薑令菀決定當一個嬌妻,努力養好身子,然後給陸琮蒸包子、煮包子、煮包子、蒸包子…… 目標三年抱倆!十年一窩!!! 可問題是——現在她自己還是個白白胖胖的奶娃娃。 “唔,奶娘我餓了。”還是吃飽了再去找陸琮吧。
76.4萬字8 12497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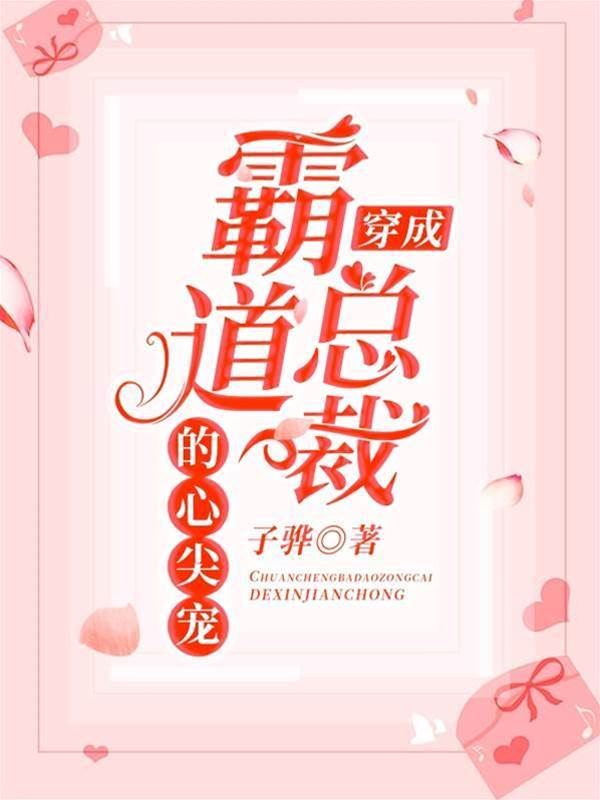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7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