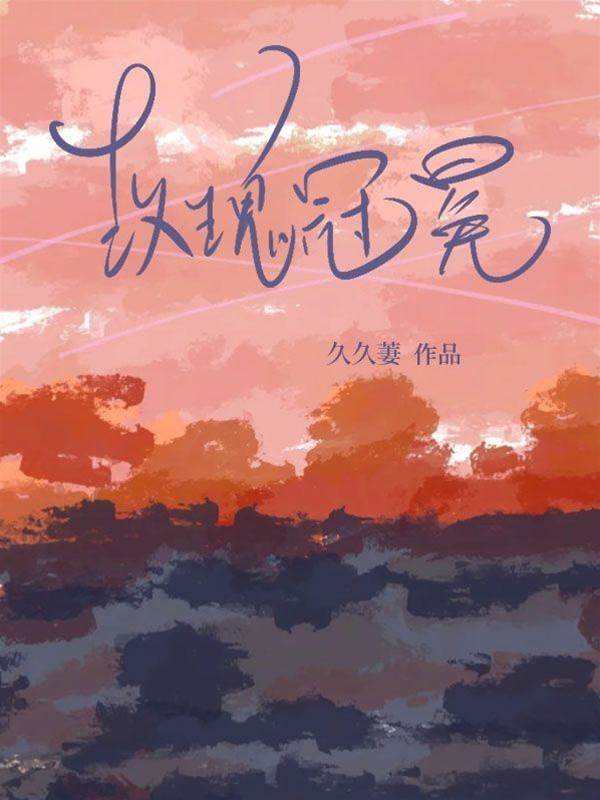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南風也曾入我懷》 317章 我只是聽你的話
最終人接了他的辦法。
俞溫去了一套服來給換,等換好了,他又把扎得高高的馬尾辮解開,頭發,讓看起來更像個落難的婦。
的頭發很,讓俞溫想起了遠在國的妹妹,眼神不溫了幾分,低聲問:“你什麼名字?”
用阿拉伯語說了個詞,俞溫奇怪地重復:“九?數字九?怎麼這個名字?”
“我排行第九。”
“小九,記住,沒接近哈德之前,你不能暴自己殺手的份。”他自顧自把人家的名字給篡改了,人抬眼看他一本正經地叮囑,就只是蹙蹙眉,沒提出什麼異議,淡淡的‘嗯’了聲。
俞溫也給自己了一套士兵的服,又往臉上了個假胡子,抹了幾把泥,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顯眼,然后就拎著小九明正大地走出去。
走到那個帳篷門口,俞溫看了小九一眼,后者心領神會地低下頭,裝出害怕驚恐的模樣。雖然有些一筋,但很聰明,俞溫教一遍就知道該怎麼演,而且演得還真。
俞溫眼底閃過一笑意,也調整自己的表,一把掀開帳篷,將人大咧咧地丟進去。
帳篷里有很多人,老的的小的都有,每個人上都很狼狽,們本能地恐懼士兵,一看到有士兵來就尖哭泣,不停地往后躲,就怕被抓出去。
俞溫把小九丟在比較顯眼的地方,警告地喝一聲:“都安靜點!”
人們立即捂住,哭也不敢哭出聲,只是眼睛里寫著滿滿的驚懼。
俞溫轉離開時,迎面上三四個士兵結伴而來,他頓了頓,大大方方地抬手打招呼:“嘿,你們也來啊。”
對方不認識他,不過看他這麼主,心里也沒起懷疑,畢竟軍營里士兵這麼多,他們也不可能每個人都認識,就回道:“是啊,你弄完了嗎?”
Advertisement
“剛剛弄完,你們挑,我還要去換班。”
“好,哈哈。”
俞溫走出帳篷,眼角往后一瞥,確定沒有人在看他,便飛快側躲到帳篷一側,從帳篷的破觀察來里面的況。
那四個男人像在菜市場挑白菜似的挑人,其中一個男人注意到了小九,睜大了眼,立即把拉起來:“這個是剛抓來的嗎?fuck!真漂亮!”
另一個男人也湊上來看,,二話不說手去搶:“這個給我!”
“憑什麼?我先看到的!”
“老子看上就是我的!”
……
四個男人爭搶了起來,互相推搡咒罵,小九在旁邊看著,臉上什麼表都沒有,只是眼底閃過一不耐煩,大概是覺得這四個人擋了的路,要見的是哈德,又不是這些雜碎。
俞溫看著的反應,覺得有些好笑,他是真的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怎麼養的,本不像個殺手——哪有殺手這麼輕易相信人?他讓假扮被強擄來的婦,就一口答應,也不怕他是要故意害的。
四個男人爭執到最后決定流上,有了小九后,他們對其他人也不興趣了,四個人抓著小九往外走,其中一個說:“這個人是啞嗎?一聲不吭的。”
“這樣才好,其他人哭哭啼啼的煩死了。”
“是啊。”男人往小九臉上了一把,細的讓他更加興,“你要是乖乖的,以后你就伺候我們兄弟幾個就行,不用再回那個帳篷。”
俞溫跟在他們后,去了另一個帳篷。
這個帳篷是專門提供給士兵的,四個男人一把將小九丟上床,其中一個就迫不及待地撲上去,一邊撕扯的服,一遍快速解著子。另外三個看著眼饞,不肯讓他第一個上,四個人又吵了起來。
Advertisement
俞溫在帳篷外看著,小九上的服被撕開,雙手在床板上拳,眼神冷若冰寒,明顯是在忍耐,但那男人在上胡作非為時,卻一點反抗都沒有。
男人的作越來越過分,俞溫心里浮現出一冷戾,覺得那只在小九上游走的手礙眼極了,從長靴里出一片柳葉形的刀片,手一擲,直接扎進那個在小九上的男人的手背上!
男人立即慘一聲,滾到了地上,罵起來:“Idiot!你們竟然敢用刀!!”
他立即爬起來,和另外三個扭打一團。
俞溫又用另一片柳葉傷另一個人,那人以為是第一個傷的男人刺傷他,偏偏那男人還給了他一拳頭,怒發沖冠之下,直接掏出槍斃了那人。
槍聲引起帳篷外的其他人的警惕,士兵們紛紛沖進來看究竟,俞溫也混在圍觀的士兵之中,他注意到,哈德也被引了過來。
“干什麼?”
殺人的士兵一看到首領就慫了,另外兩個男人對視了一眼,默契地把責任都推到殺人的士兵上,一口咬定他是想獨占小九所以開槍殺人。
殺人的士兵喊著冤枉,哈德懶得聽真相到底是什麼,直接讓人把他拖下去決,他又走到小九面前,去看引起爭執的源頭,小九低著頭像是很害怕,他手,抬起了的下。
小九是阿拉伯統,五深邃立,就算用東方人的審目看也會覺得很驚艷,尤其是的眼睛,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沙漠里的月亮,清冷的,孤高的,像冰霜一樣拒人于千里之外。
哈德眼睛一亮,用阿拉伯語連夸了幾句‘漂亮’,手一揮,召來兩個士兵:“把帶到我帳篷!”
Advertisement
俞溫主上前,和另一個士兵一起將小九帶去哈德的帳篷。
路上俞溫觀察著,哈德的帳篷外有兩個士兵看守,周圍不間斷有士兵來回巡邏,如果帳篷里有什麼異樣,外面的士兵會立馬察覺到。
殺哈德……比他想象的還要困難。
同時他還發現,和小九合作,可能不是明智的決定——因為小九是殺手,對來說,只要能殺死哈德,完上面給的任務,無論能不能全而退都沒關系。
但是他不行,他是要活著離開的。
“你們都出去。”哈德揮退他們。
“是。”
俞溫和士兵一起離開帳篷,他轉前朝小九遞了一個眼神,希能懂他的意思,可小九卻沒有看他,低垂著眼睛,濃纖長的睫完全蓋住眸子里的彩。
士兵要回休息區,俞溫跟著走了幾步,心下還是不放心,重新潛回哈德的帳篷。
哈德的帳篷不好靠近,俞溫蹲著二十分鐘都沒能找到機會進去,他心思一轉,計上心頭,悄然走到旁邊的帳篷后,趁著沒人注意,用隨攜帶的火柴,點燃帳篷的布。
布料易燃,沒一會兒火就大起來,俞溫立即喊起來:“著火了!著火了!快救火!”
巡邏的士兵立即圍過去救火,唯獨守在哈德帳篷門前的兩個士兵沒有。
俞溫拿出一把匕首藏在袖子里,一邊喊‘救火’一邊倒退著跑,‘不小心’撞到門前一個士兵上,士兵咒罵:“沒長眼嗎?”
“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俞溫說著話,側著子擋住其他人的視線,手上匕首一轉,直接將士兵割!
另一個守門的士兵發現到了他,剛想喊,俞溫平地一躍,同樣將匕首捅進他的咽!
悄無聲息解決掉兩個士兵后,俞溫立即跑到帳篷去看小九。
帳篷里的小九衫凌,半跪在床上,雙手抓著用布條勒住哈德的脖子,的力氣很大,布條三分,哈德完全出不了聲,翻著白眼,雙腳一直蹬著掙扎。
看到他來,小九低喝:“幫忙。”
俞溫快速跳上床,抓住布條,用力一絞,直接絞斷哈德的脖子!
解決完目標,兩人對視了一眼,都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也就沒有多廢話,立即往外跑。
外面的火已經滅了,場面漸漸被控制組,并且還有士兵發現兩尸,當下吹響口哨發出警報。
俞溫和小九跑不出去,只能躲到一個堆放雜的帳篷里,外面沒多久就有人喊‘首領死了’,整個軍營立即一團。
小九挑起帳篷的一角,觀察著外面的況。
俞溫在后,無意間注意到上的服破碎,完全遮不住,頓了頓,就把上的T恤下來。
“穿上。”
小九下意識轉頭,一眼看到他小麥的膛,愣了愣。
現在是夏天,俞溫上只有這件T恤,了給,自己當然就沒有服。
俞溫眼里帶笑:“我是男人你是人,你覺得我們兩誰沒穿服問題更大?”
“……”
最終小九還是穿了他的服,T恤上有淡淡的汗味,不難聞,只是殘留的溫燙得的臉頰有些發熱。
俞溫盯著泛紅的臉頰,想著原來也會害,想起剛才士兵在上胡作非為的事,臉上的笑意漸漸收斂,低聲問:“他們剛才那樣對你,你怎麼不反抗?”
小九皺眉,仿佛覺得他問這個問題很奇怪:“不是你說的?沒見到哈德之前,我不能暴份。”
短暫的沉默后,俞溫忽然問;“六乘五等于多?”
“三十。”小九看他,“怎麼?”
猜你喜歡
-
完結263 章

偏執男主白月光我不當了
楚殷死後才知道自己是豪門文裡的白月光。 偏執男主年少時對她一見鍾情,執掌財閥大權後將她禁錮,佔有欲瘋魔。楚殷備受痛苦,淒涼早死。 再睜眼,她回到了轉學遇到陸縝的前一天。 “叮~學習系統已綁定!宿主可以通過學習改變垃圾劇本喲!”這輩子她不要再做短命的白月光,發奮學習,自立自強,這輩子逆天改命,最終揭開上輩子的謎團,拿穩幸福女主劇本。
37.9萬字8 10745 -
完結1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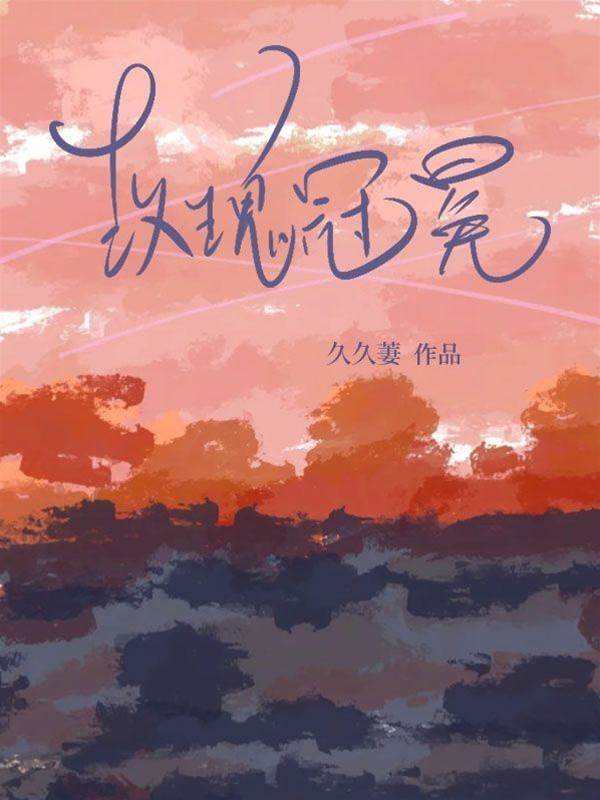
玫瑰冠冕
【先婚後愛?暗戀?追妻火葬場女主不回頭?雙潔】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多年暗戀成真【偏愛你的人可能會晚,但一定會來。】*缺愛的女孩終於等到了獨一無二的偏愛。
33.4萬字8 61089 -
完結1063 章

四年后,前妻帶崽歸來虐翻渣爹
懷胎八月,他們第二次見面。 她以為他至少會關心關心孩子,卻沒想到他竟然要離婚,只因他們是商業聯姻,他對她毫無感情。 她希望他看在孩子的份上,至少等他們平安出生,可他卻無情的說:“你不要妄想我會接納他,他就不該來到這個是世上。” 四年后,她帶著天才兒子歸來,卻發現當年沒帶走的女兒,如今不但身患重病,還被渣男賤女一起虐待到自閉。 她憤怒的和他對峙,誓要搶回女兒。 他緊緊的抱住她,“老婆,我知道錯了!你別不要我……”
199.2萬字8 8573 -
完結261 章

驚呆!我親媽竟是帶球跑女配!
越蘇大學時見色起意,撿了一個男人。失憶,身材野,長得好。 后來,失憶的男人成了男朋友。 越蘇和他陷入熱戀,男人卻恢復了記憶,一朝成了京圈傅家太子爺。 他記得所有人,獨獨忘了她。 雪夜里,越蘇在樓下站了一晚,只為見他一面,卻等來了他的未婚妻。 越蘇心灰意冷,事業受阻,果斷退圈生娃。 四年后,她帶著孩子上綜藝,卻在節目與他重逢。 男人冷漠疏離,對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視若珍寶。 全網都在嗑他和當紅小花的CP,嘲笑越蘇不自量力。 卻在節目結束的某一天,狗仔拍到—— 那矜貴不可一世的傅家太子爺,將越蘇堵在角落。 低下頭顱,卑微乞求她的原諒。 * 要要做了個夢。 醒來驚呆,她媽媽竟是霸總文里的帶球跑女配! 她問小胖:“什麼是女配?” 小胖說:“白雪公主的惡毒后媽就是女配。” 要要:“女配的女兒呢?” 小胖:“那是小炮灰。” 要要不想成為小炮灰,督促媽媽努力賺錢,卻在綜藝偶遇便宜親爹。 便宜爹看著很有錢。 要要:“叔叔,等你死了,能把手表送給我嗎?” 傅西燼:“我不死也可以送你。” 要要:“還是等你死了再給我吧。” 傅西燼微笑,小棉襖還不算太漏風。 要要又問:“可以明天就送我嗎?” 傅西燼:“……”
50.2萬字8 147 -
完結143 章

透明的雪
盛衾從小性子溫和淡然,除了偷偷暗戀一個人多年以外。 做過最出格的事,莫過於在聖誕節的雪夜表白,將多年的喜歡宣之於口。 這次表白距離上次見宴槨歧已經有兩年多。 男人一頭烏黑的發變成了紅色,看上去更加玩世不恭。 他被一群人圍在中央,衆星捧月,人聲鼎沸中看向她,神色淡漠到似乎兩人並不相識,雪落在他的發頂格外惹眼。 等盛衾捧着那顆搖搖欲墜的心,用僅剩的勇氣把話講完。 四周幾乎靜謐無聲,唯獨剩下冷冽的空氣在她周身徘徊,雪花被風吹的搖晃,暖黃色的路燈下更顯淒涼狼狽。 宴槨歧懶散攜着倦意的聲音輕飄響起。 “抱歉,最近沒什麼興致。” 那一刻,盛衾希望雪是透明的,飛舞的雪花只是一場夢,她還沒有越線。 —— 再次重逢時,盛衾正在進行人生中第二件出格的事情。 作爲紀錄片調研員觀測龍捲風。 無人區裏,宴槨歧代表救援隊從天而降。 男人距離她上次表白失敗並無變化,依舊高高在上擁有上位者的姿態。 盛衾壓抑着心底不該有的念頭,儘量與其保持距離。 直到某次醉酒後的清晨。 她在二樓拐彎處撞見他,被逼到角落。 宴槨歧垂眸盯她,淺棕色眸底戲謔的笑意愈沉,漫不經心問。 “還喜歡我?” “?” “昨晚你一直纏着我。” 盛衾完全沒有這段記憶,呆滯地盯着他。 宴槨歧指節碰了下鼻子,眉梢輕挑,又說。“還趁我不備,親了我一下。” —— 雖不知真假,但經過上次醉酒後的教訓,盛衾怕某些人誤會她別有居心,癡心不改,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他卻步步緊逼。 有天被忽視後。 宴槨歧懶散地靠着車門,睨她:“看見了,不知道叫人?” “我覺得,我們不是可以隨便閒聊的關係。” 片刻後,盛衾聽見聲低笑,還有句不痛不癢的問話。 “那我們是什麼關係?” 盛衾屏着呼吸,裝作無事發生從他面前經過。 兩秒後,手腕毫無防備地被扯住。 某個混球勾着脣,吊兒郎當如同玩笑般說。 “之前算我不識好歹,再給個機會?”
33.8萬字8 1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