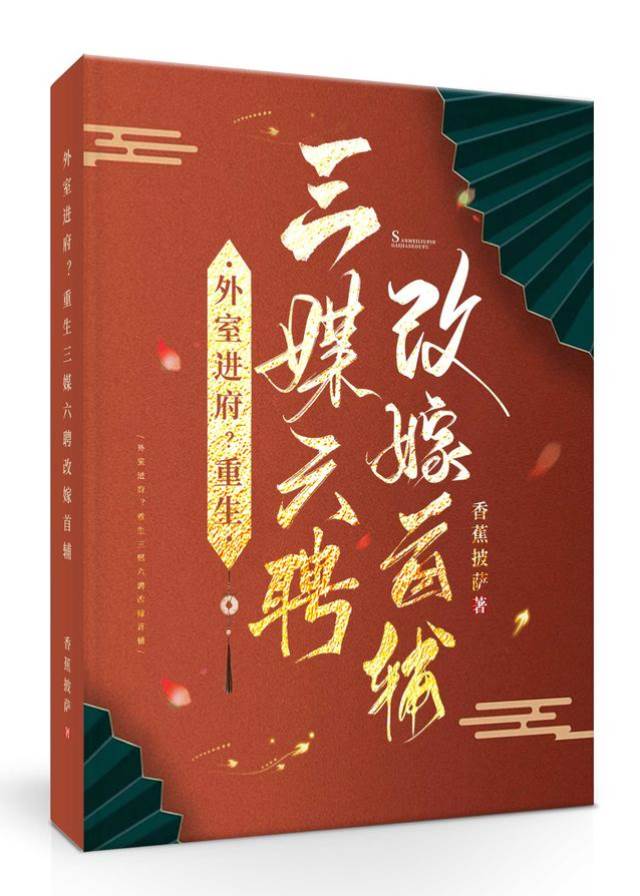《我力能扛鼎》 第298章 第298章
屋里一餿臭味,漕司府的幾個丫鬟跪在床尾,味兒更沖,都憋著氣用呼吸,不敢出表來。
“爺!爺不敢再吐了啊!您這吐的都帶了!船上的大夫都死絕了嗎?!不會治就送我家爺上岸!”
唐荼荼站在外間探頭瞧了一眼。
那公子倒趴在床邊,像從水里撈出來的,后頸了個,汗珠子雨一樣啪嗒啪嗒往地上滴,噦(yue)一聲噦一聲的。口鼻里都是穢,這麼趴著,是怕他仰面躺著會嗆死自己。
嘔吐的間隙里,弱聲弱氣嚷了句:“拿冰……要熱死老子麼?”
“爺,不能用冰啦!杜大夫說冷熱一激,得折您半條命,您再忍忍,可不敢吐啦!”
“夭壽……噦……”
嗓子眼淺的人最怕聽別人的干嘔聲,唐荼荼立馬拿手捂口,悶聲問船醫:“怎麼樣了?”
幾個船醫誰也沒顧上回,抻長脖子往里屋,一排眼睛睜得溜圓。
房間背,這黎明時分屋里不亮堂,進門頭一眼沒瞧清楚。等唐荼荼定睛去看,一個喜上眉梢大架立在床頭,右手邊的喜鵲桿頭上倒掛著一個圓肚玻璃瓶,底下蜿蜿蜒蜒一白線,穿在漕司公子的手背上。
等看清這是什麼,唐荼荼一涼氣沖上天靈蓋。
“杜、杜仲,你出來一下……”
唐荼荼控制不住的手抖,把杜仲拉出室,著聲問:“你怎麼敢給他吊水!!”
杜仲不不慢反問:“為何不敢?”
唐荼荼像個將要炸膛的炮仗,氣音都哆嗦了:“你連實驗都沒做全!你怎麼敢給活人吊水?!”
杜仲道:“他已經吐了一宿,汗出如漿、視模糊、神志不清了,再讓船返航送回岸上去,不知會是怎樣景——姑娘不是說大膽嘗試,小心求證?你常掛在邊的話,怎的不對了?”
Advertisement
唐荼荼臉皮抖得厲害,怕嚇壞漕司家的仆役,沒敢進屋,兩手搭在額前上琉璃窗細看,飛快念叨。
“金針頭燙過了,問題不大……海南的橡膠還沒到,膠皮管還沒做出來,那用的是什麼管?”
杜仲眼里浮起笑意來:“是小羊的腸,很細,不會流得很快,我洗干凈、煮過又曬干的,很干凈。”
唐荼荼又一寒戰。
什麼腸!分明就是羊的小腸!排尿的那通道!
什麼洗得干凈,那是洗了洗!
一個醫學半吊子,也知道“干凈”和“無菌”之間隔著天上地下的差別,杜仲怎麼敢的?
他用沒消過毒的針頭、沒排過空氣的針管、細菌超標的小羊腸、不清楚能不能的鹽糖水,往病人管里輸——還不知道有沒有找準靜脈!
唐荼荼戰戰兢兢往屋里瞭,仿佛預見了這家公子高燒、心梗、臟衰竭、暴斃的癥狀,眼前一陣陣發黑。
生理鹽水,這東西做出來四個月了,葡萄糖稍晚一些,上上個月剛鼓搗出來,是淀經水解生的糖,簡而言之,就是稀硫酸攪合玉米淀的溶,60℃左右的溫度加熱。
葡萄糖有許多種生產工藝,但唐荼荼只能做最原始的。
把配方給年掌柜后,沒天天盯著,因為用不同的淀、不同濃度的硫酸、水解條件的不同,產出來的單糖差別很大。
年掌柜家里上千個釀酒工,自有一套嚴格的生產管理法,工人做事細、口風,一個人只掌握一步工序,配方就不會在外邊傳。
至于鹽糖水,氯化鈉葡萄糖水,既補水又補充能量,唐荼荼混合了低糖高糖各種濃度的鹽糖水。
裝瓶后,還要一遍一遍檢——先是瓶子封裝嚴度測試;再讓活活兔飲用,觀察記錄;要試驗人喝了有沒有補充能量的作用;高溫低溫極端條件存放、或超過保質期后,再經服用,會不會嘔吐腹瀉,以此試驗不合規的存放條件下,瓶中的菌群會不會超標……
Advertisement
這項工作煩瑣又累贅,慢工,還出不了活,純粹是一天一天地磨人。
口服試驗完了沒病,再試著洗患,比如鹽水皮炎、腳氣,乃至外瘙。
公孫家幫了大忙,軍營里多的是衛生習慣不好得了皮病的兵,生理鹽水本不能殺菌消毒,但能把膿、壞死組織沖洗干凈,菌群了,慢慢就自愈了。
他們那個小軍營了臨床實驗基地,鹽糖水也是他們實驗的,將士們高強度的訓練后,口干舌燥,大汗淋漓,喝一瓶鹽糖水,下能不能快速恢復力。
因為主基是水,喝完了代謝快,即便濃度不合適也不會對人造大問題。
這就是全部的實驗了,沒有實驗材,沒有量化單位,甚至沒條件做嚴格的對照樣本,只能慢慢觀察,慢慢記錄。
唐荼荼打算起碼驗證個一年半載的,再開始琢磨如何輸,走管的東西跟走消化道的不一樣,自然不能等閑視之。好在量產后本一路下降,玻璃瓶還能回收利用,能供備得起。
可眼下。
唐荼荼氣得想踹他:“你真是……你吃了豹子膽了!”
杜仲神不,引往船舷邊沒人的地方走。海風很大,吹得他聲音輕飄,腳下卻是穩的。
“姑娘,我沒問過你從何來,從哪兒學的那些通天徹地的學問,但我心里未嘗沒數。”
唐荼荼一凜。
“師父家里所有的醫書我都看過,世上大多醫書都是一脈相承,能革故鼎新自樹一幟的醫圣人,百年也出不了三人——神農嘗百草,后醫才知世上有百草,繼而嘗出千草萬草,生出千萬方劑變化;上古有脈診,扁鵲一輩子研學琢磨,才有了、聞、問、切,后人匯編整理,寫一本《脈經》,天下大夫都學這本經,不停地取正驗錯,增補新說。”
Advertisement
“你瞧,幾千年來的醫衍變,都是循著前人步伐往深走的,是一代代的繼往開來,從沒一門學問,能冷不丁地冒出來。”
“看不著細菌,而知有細菌;看不著細胞,又是怎知有細胞的?”
“太婆留下的醫書里,有許許多多的配圖,畫了皮的層瓣,表皮、真皮、神經、淋管,還繪有肺腑五臟的模樣,好像天生知道該怎麼剝皮剖骨,怎麼完完好好地把死人幾顆臟剖出來。”
他說著淋淋的話,眼里的笑竟還沒落下,朝一照,一雙瞳仁亮金,甚至顯出幾分無機質的冷漠。
唐荼荼有一瞬間的晃神。
記憶里的杜仲,好像還是第一面見他的樣子。
沉默的、寡言的、不自信的,塌著肩駝著背,不大愿意搭理生人,像個沒經過事、藏在師父翅膀底下的孩子。
也是圍場上,師父遭上排、遭同僚欺負時,那個著脖子紅著眼睛罵“你們欺人太甚”的年。
他在疫病所時穿上了這白大褂,再沒過,縣學那些小大夫們不止一次笑穿這一白不吉利,杜仲也我行我素地穿著,白了靜海縣的一道風景線,白了一種風格。
這兩個月忙得太狠,竟不知道杜仲在哪里坐堂,混出了怎樣的名聲,是被什麼人請上這條全是家子的船的。
唐荼荼就這樣啞了聲。
手腳發地坐下,等著屋里的靜。
怕針頭進脈,反流;怕腸管里有空氣柱,怕小小一個氣泡栓塞流進去就是心衰和腦梗;怕染,怕配得不對,糖高鹽低要了那公子半條命。
這一上午,唐荼荼拼命回想輸輸錯的后癥,可離大夫差了十萬八千里,一個生理鹽水、一個葡萄糖水用的還是高中實驗課上那點知識。大學衛生課上學過半拉急救,學過自己給自己扎腎上腺素,卻實在記不起輸輸錯了該如何,一條“羊小腸”,就足夠腦子里各種死相排隊走。
大概是杜仲的膽了天,一瓶輸下去,漕司公子竟慢慢止了吐,睜眼把杜仲看了看,筋疲力盡地睡下了。
幾個船醫各個紅滿面,目灼灼,活像看了一場彩絕倫的大秀。
杜仲慢騰騰地收拾好醫箱,在漕司家仆人的歡送中出了艉樓。
唐荼荼這才驚覺自己在大太底下坐了一個時辰,汗出得全沒幾個干,忙問:“如何了?”
是真的嚇怕了,杜仲看得出,很是老氣橫秋地嘆了聲。
“姑娘怎麼,變得膽小了呢?”
唐荼荼張張,有一肚子話想往外說,愣是一句沒出來。
杜仲淺笑著問:“你猜第一個往人管里輸鹽水的大夫,治死了多人?”
“……”
唐荼荼不敢想。
在的時代,醫學已經蓬發展,哪怕資源再匱乏的時候,也只是頒布了個全國藥品最嚴管制令,沒聽說過輸輸死人的事。
可往前想,最早,是哪個大醫學家發現鹽水能往管里輸、進而彪炳史冊的?又是哪個大醫學家把病畜的脊髓磨,潦草地兌了點兒水注到人,治好了狂犬病的?
那一定也是用病人試藥……
各科醫學的早期必定都有一段無知到野蠻的歷史。
唐荼荼手指發麻,杜仲這一問,才意識到自己的短視——揣著點與時代斷了節的基礎醫學常識,沒能耐在古今醫學演變的進程里一腳,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閉上。
一咬牙:“行,你盡管治!治壞了,咱倆一塊跪漕司面前給他償命去。”
杜仲笑了聲,話里著幾分文士的狂。
“姑娘說笑了,我是過了太醫院選試的大醫士,天底下活著的醫加上大醫士僅有一百四十二位,我就是治死了人,也得帶上尸帶齊醫案,押回京城判,漕司不敢當街殺我。”
得,敢他全想了。
這是半個醫癡,半個瘋。
猜你喜歡
-
完結11833 章
邪王追妻:廢材逆天小姐
她,21世紀金牌殺手,卻穿為蘇府最無用的廢柴四小姐身上。他,帝國晉王殿下,冷酷邪魅強勢霸道,天賦卓絕。世人皆知她是草包廢材,任意欺壓凌辱,唯獨他慧眼識珠對她強勢霸道糾纏誓死不放手。且看他們如何強者與強者碰撞,上演一出追逐與被追逐的好戲。
1055.4萬字8.18 447425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953 章

將軍的病弱美人又崩人設了
傅明嬌是知名網站作者,曾被評為虐文女王,后媽中的后媽。在她筆下be了的男女主數不勝數,萬萬沒想到她居然穿進了自己寫的虐文里,成了男主的病弱白月光。明明生的容色絕艷,傾國傾城,卻心腸歹毒如蛇蝎,仗著家世顯赫身體病弱,以治病為由百般誘騙男主,讓…
84.8萬字8 20522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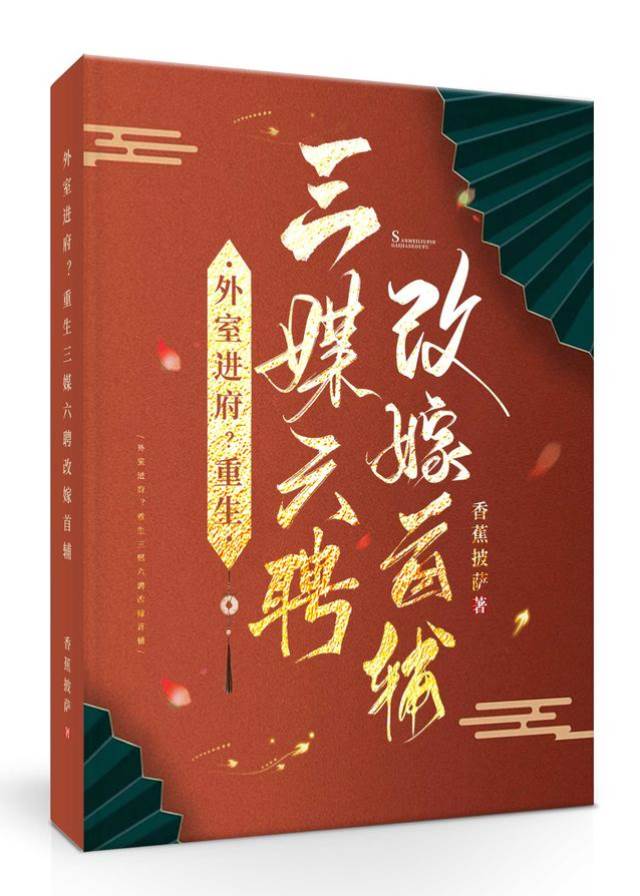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
完結304 章

夫君他天下第一甜
明王府獨苗苗世子謝蘅生來體弱多病,明王將其看的跟命根子似的,寵出了一副刁鑽的壞脾氣,那張嘴堪比世間頂尖毒藥,京城上下見之無不退避三舍。 初春,柳大將軍凱旋歸朝,天子在露華臺設宴爲其接風洗塵。 席間群臣恭賀,天子嘉獎,柳家風頭無兩。 和樂融融間,天子近侍突然跑到天子跟前,道:“有姑娘醉酒調戲明王府世子,侍衛拉不開。” 柳大將軍驚愕萬分,久不回京,這京中貴女竟如此奔放了? 他抱着好奇新鮮的心情望過去,然後心頭驀地一涼,卻見那賴在世子懷裏的女子不是隨他回京的女兒又是誰。 雖剛回京,他卻也知道這世子是明王的心頭肉,餘光瞥見明王雙眼已冒火,當即起身爆喝:“不孝女,快放開那金疙瘩!” 一陣詭異的安靜中,柳襄伸手戳了戳謝蘅的臉:“金疙瘩,這也不是金的啊,是軟的。” “父親,我給自己搶了個夫君,您瞧瞧,好看不?” 謝蘅目眥欲裂盯着連他的近身侍衛都沒能從他懷裏拆走的柳襄,咬牙切齒:“你死定了!” 柳襄湊近吧唧親了他一口:“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 謝蘅:順風順水頤指氣使了十八年遇見個女瘋子,她一定是我的報應! 柳襄:在邊關吃了十八年風沙得到一個絕色夫君,他是我應得的! 女將軍vs傲嬌世子
49.1萬字8.18 135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