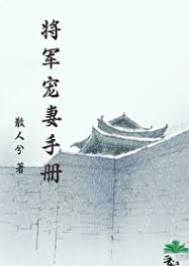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守寡后我重生了》 第 174 章(春日思)
大事談完,呂、陸、沈三位閣老送諸位藩王一道出宮。
元祐帝帶著陳廷鑒、何清賢去了書房。
他手里拿著一份《告列祖列宗書》,上陳他這次推行新政的起因與新政概要,簡簡單單一封文書上,除了加蓋他的玉璽,二十一位藩王也都簽了名字按了王印。
縱觀本朝二百余年,唯獨元祐帝做了這麼一件聯合眾藩王的大事。
元祐帝展開明黃的卷宗,又細細欣賞了一遍。
何清賢不滿道:“那麼多告狀的折子都燒了,皇上對諸藩王還是太仁慈。”
元祐帝:“讓他們做事,總要給些好,更何況朕只是一筆勾銷了前罪,若他們以后再犯,朕仍然可以追究。”
何清賢:“諸王雖然應承了此事,回封地后未必真就愿意配合,或是找些借口推諉,或是在紳那邊拱火,只要紳出頭功阻攔了新政,藩王照樣坐其。”
元祐帝看向陳廷鑒。
陳廷鑒笑了笑:“召他們進京,是為了向天下紳百姓表態,朝廷推行新政勢不可擋,敢擋者,殺了便是,此乃先禮后兵。”
何清賢:……
還說他狠,輕描淡寫放狠話的首輔大人才是真的狠!
翌日早朝,二十一位藩王也來了。
滿朝文武,其實絕大多數都是被閣著同意新政的,聽說元祐帝要召藩王們進京時,他們比元祐帝更盼藩王們早點來,盼著藩王們能掐斷小皇帝的荒唐念頭。
讓他們失的是,曹禮才宣讀完推行新政的圣旨,二十一位藩王比閣跪得還快,轉眼就烏跪了一片。
藩王們份比他們高,手里的田地也比他們多得多,藩王都跪了,滿朝文武誰還敢反對?
當天傍晚,華從陳敬宗口中得知了此事。
Advertisement
新政的第一步真正出去了,最難纏的藩王們那邊至面上已經承諾會配合新政,不敢生太大的,否則朝廷憑借一卷《告列祖列宗書》便可前往其封地治罪。
華松了口氣。
陳敬宗拎起酒壺,看著道:“總算沒白費我認了那麼多親戚。”
華笑道:“將來新政有了效,我皇上給你記一大功。”
陳敬宗將壺口對準的白瓷碗:“不用勞皇上,長公主陪我喝兩口,便足以做我的報酬。”
華連果子酒都能喝醉,哪里能沾他常喝的烈酒?
陳敬宗提議這個,圖的便不單純。
想到室那面昂貴的西洋鏡,華撥開陳敬宗的手,并瞪了他一眼。
陳敬宗也不失,自斟自飲起來。
只是到了夜里,他還是抱著長公主好好地討了一番報酬。
.
藩王們千里迢迢地來到京城,一路上不容易,但為了避免藩王與京勾結,元祐帝只款待了他們三日,便客客氣氣地送走了這群藩王。
華仍然跟著弟弟送了一回。
第二日安樂大長公主就來做客了。
春融融,姑侄倆并肩在花園里散步,牡丹尚未綻放,海棠開出了一團團緋云。
安樂大長公主折了一枝海棠,在自己發間,問侄:“如何?”
華笑道:“似天仙。”
安樂大長公主看看侄細如凝脂的臉,再自己的,輕嘆道:“天仙什麼啊,已經開始老了,眼角都生皺紋了。”
華仔細觀察姑母,剛想說哪里有皺紋了,安樂大長公主故意笑得夸張些,果然在眼角了幾條細紋出來。
華:“……您平時又不會那麼笑。”
安樂大長公主:“可我以前這麼笑也不會出現皺紋,所以還是老了。”
Advertisement
華才二十四歲,還無法理解姑母的心,而且在看來,姑母真的貌依舊,倒是宮里的母后,竟然已經長了銀,所幸只是兩三,宮梳頭時瞧見,從發剪斷了。
漸漸變曬,姑侄倆坐到了涼亭中。
安樂大長公主提到了這次新政:“這兩日我出門,街上百姓都在討論新政,皇上年輕膽大,陳閣老也真是有魄力,敢跟天下紳對著干,我還聽說,他把陳三郎派去了徐閣老所在的華亭縣?”
現在的閣沒有姓徐的閣老,安樂大長公主口中的徐閣老,乃是已經回鄉養老的前前首輔,曾經陳廷鑒都得乖乖聽對方的話。
據說,徐閣老家里有幾十萬畝田地,便是他還是正一品的大員時,也只能免稅一萬畝田而已。可想而知,這次朝廷推行新政,一個徐家就得多繳多田賦,陳孝宗在那邊又會到多大的阻力。
華苦笑:“這些事總要有人去做,若陳閣老都不敢帶頭得罪紳士族,其他員更加投鼠忌。”
安樂大長公主哼了哼:“拜你公爹所賜,姑母也得多一筆田賦。”
華:……
有些訕訕,安樂大長公主撲哧一笑:“逗你的,姑母領朝廷的俸祿就能一輩子逍遙快活了,又沒有子孫要養,豈會介意田賦,更不至于為了新政跟你抱怨什麼。”
華欽佩道:“若天下宗親都如您這般支持新政就好了。”
安樂大長公主:“難啊,咱們當公主的還好,那些藩王郡王們,個個養了一堆小妾通房,養的人多花銷就多,要想一直維持奢華的用度,便只能想方設法地往家里斂財。”
華冷笑:“財路不正,便只能咎由自取。”
Advertisement
安樂大長公主:“我居然剛看出來,你還是個嫉惡如仇的,真應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用過午飯,安樂大長公主告辭了。
華被姑母的話勾起思緒,傍晚陳敬宗回來,閑聊道:“大哥三哥離京三個月了,可有寫信給你?”
陳敬宗:“不曾,怎麼突然提到他們?”
華防著他吃飛醋,提起自己與姑母的談話。
陳敬宗:“大長公主還真是消息靈通,京城什麼事都瞞不過。”
華:“你就不擔心他們嗎?大哥在廣東,就算他是首輔家的大公子,到了那邊也難以靠份服眾。還有三哥,別說他當年只中了探花,就是中了狀元,對上徐閣老也無濟于事。”
陳敬宗:“難才要派他們出去,不然哪顯得出他們的本事。”
華:“……跟你沒什麼好說的,月底休沐,我要回去探母親。”
陳敬宗:“探母親,還是打聽大哥三哥有沒有給家里寫信?”
華:“怎樣都與你無關。”
陳敬宗將人拉到懷里找關系,一直到丫鬟們要端晚飯進來,他才松開了氣微微的長公主。
待到休沐日,夫妻倆一起坐車前往陳府。
剛下車,就見里面管事送了一位婆出來。
婆激萬分地給長公主、駙馬行禮。
陳敬宗臉發沉,自家三兄弟都親了,婆為誰而來?最大的侄婉宜也才十四歲!
在陳敬宗眼中,十四歲的侄依然是個孩子,誰敢早早盯上侄,那就是不安好心!
華雖然吃驚,倒也沒有他這麼抗拒這回事,十四五歲的大家閨秀,本來就是談婚論嫁的年紀。
兩人直接來了春和堂。
首輔陳廷鑒早就沒了休沐日,今日又在宮里,春和堂這邊,因為來了婆,俞秀、羅玉燕都陪著婆母。
華坐到了孫氏旁邊的主位,陳敬宗坐在兩位嫂子對面。
他先開口:“有人看上婉宜了?”
俞秀覺得小叔此時的眼神帶著幾分兇狠,不敢直視,看向婆母。
孫氏淡笑道:“是啊,吏部侍郎馬大人家的長孫今年十八,飽讀詩書,與婉宜年齡倒是相配。不過老頭子說了,等你大哥回來再考慮婉宜的婚事,反正那時候婉宜也才十七,不算晚。”
今年的新政比前面考法、清丈土地都難,場人心浮,有人不確定老頭子能堅持多久,不敢與陳家結姻親,有的人看好老頭子,愿意用結親的方式向老頭子投誠,總之各有心思,惦記的都是場那一套,沒幾個是真正喜歡婉宜這孩子的。
丈夫不想拿孫去拉攏黨羽,孫氏比他更舍不得,一直想要個兒,生不出來沒辦法,婉宜是的第一個孫輩,從小聰慧伶俐溫婉明,孫氏當心肝一樣疼,不千挑萬選,絕不會草草率率地定下親事。
陳敬宗聽了母親的話,臉好轉:“理該如此,多留幾年吧。”
華手里端著茶碗,茶水是清綠的。
婉宜是陳家眾人的掌上明珠,亦是最喜歡的晚輩。
上輩子陳家眾人被發配邊關,最擔心的也是婉宜,所以,那日大雪回到長公主府,便讓周吉準備兩輛馬車與寒,再帶上一隊侍衛,去護送陳家眾人出行。不要曾經玉樹臨風的探花郎手戴鐐銬被人圍觀,不要大郎幾個年承千里跋涉吃苦,更不可能讓兩位嫂子與侄們遭遇任何子都避之不及的災禍!
公然照拂被朝廷發配的罪臣家眷,這個長公主大概也是頭一份了。
當時的華,沒心去想別人會怎麼看,也不在乎。
甚至盼著哪個言去弟弟面前參一本,然后好看看,弟弟是不是連這個姐姐都不認了。
可一直到病倒,京城里都沒什麼靜,那些言像不曾聽說此事一樣,在朝堂上閉口不提。
母后不會干涉,弟弟,他怕是沒臉管。
華端起茶碗,淺淺地飲了一口。
自打回京,做了那麼多事,也一直在明著暗著將弟弟往明君的路上帶。
用不了多久便是端午,倒要看看,的好弟弟究竟有沒有正回來。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報告王爺,王妃又在裝柔弱
聽說,容王殿下點名要娶太傅府的那位花癡嫡女,全城百姓直言,這太驚悚了! 這幾個月前,容王殿下不是還揚言,要殺了這個花癡嗎? 太傅府,某花癡女看著滿滿一屋的聘禮,卻哭喪著臉,“來人啊,能不能給我退回去?” 京城貴女們紛紛爆起粗口,“你他媽要點臉!”
130.7萬字9 2426690 -
完結815 章
暴君他綁定了讀心術
穿成了瑪麗蘇小說里大反派暴君的炮灰寵妃,司玲瓏告訴自己不要慌,反正暴君就要狗帶了。 卻不想,暴君他突然綁定了讀心術。 暴君要殺女主自救,司玲瓏內心瘋狂吐槽,【狗皇帝快住手,這是女主!】 司玲瓏替受傷的暴君縫傷包扎,暴君夸她手法正宗,卻聽她內心得意,【那必須的,咱是專業獸醫!】 夜里,司玲瓏睡不著在腦內唱歌,忍無可忍的暴君直接將人攬進懷里。 “閉嘴!再吵就辦了你。” 司玲瓏:……我都沒出聲!
95.2萬字8.33 12726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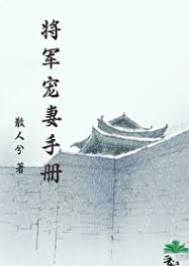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