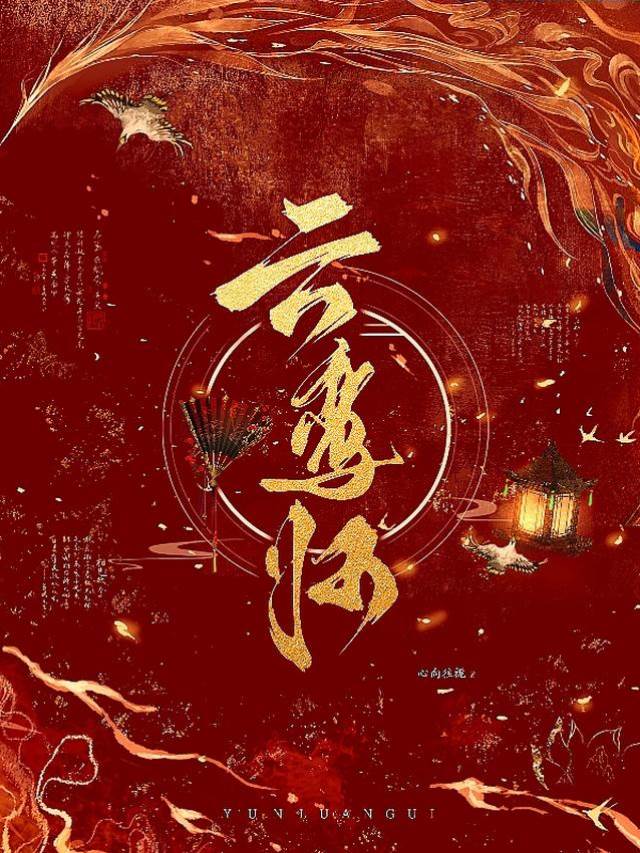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無鹽為後》 第四十七章
張後來領個兩個強壯的太監匆匆趕上來,最終搭人轎把王容與給送回儲秀宮,他則忙不迭的去找許醫。
等到王容與在炕上躺好,太醫也來了。王容與對喜桃說,「你上靜茹,劉靜的宮,讓們在殿門外守著,我神不濟,現在不見任何人。」
「是。」喜桃說。
王容與對許醫笑道,「許醫,又見面了。」
「下不是很想和姑娘見面,這個頻率可以控制一下的。」許杜仲說,「下事務繁忙,來治姑娘的外傷,有點殺焉用牛刀。」
「這個我可做不了主。正好張侍也在這,不如許醫跟張侍說說,下次不要徐醫了。」王容與還有餘裕說笑。
張苦著臉說,「姑娘可不要為難我,許醫是陛下親點的,陛下只信得過許醫呢。」
「這會知道心疼了,當初何必要罰了呢?」許杜仲說,「姑娘這次的氣可比上次好的多,看來下這次不用擔心金字招牌不保了。」
許杜仲先診脈,讓喜桃去尚膳監要了燕窩粥來,「多放點糖,讓姑娘先吃了粥甜了,之後可有好幾天苦藥子吃。」
「許醫,姑娘吃不下湯藥子,可有丸藥?」喜桃擔憂的問。
「等我回去藥丸子,一天一碗藥丸子,保管你也吃什麼都沒胃口。」許杜仲說。
「徐醫,就沒什麼不影響胃口的方子?」張問。
「下覺得憑姑娘的態,隻影響幾天的胃口沒什麼妨礙,或許還是好事呢。」許杜仲說。
王容與輕笑,「徐醫真是把我胖這件事說的清醒俗。」
許杜仲搖頭,問喜桃要了剪子,把膝蓋兩的子剪了個出來。白皙的膝蓋現在幾乎不能辨認,紫的紅的,還發腫。
Advertisement
「姑娘跪的忒實在。」許杜仲說。
喜桃和張起初見王容與和許杜仲一應一和的還以為不嚴重,這下看了膝蓋都大驚失,喜桃幾乎立即就是淚染睫羽,「天哪,怎麼這麼嚴重,許醫,姑娘這以後不會落下病吧?不會影響出行吧?」
「好生養著,並無大礙。我若連一個跪傷都治不好,也不用吃陛下這碗飯,趁早回家得了。」許杜仲看了一眼彷彿無知無覺的王容與說,「只是以後吹風下雨,年老弱的,一點骨痛在所難免。」
「沒有變一個瘸子已經是萬幸。」王容與說。「我很知足。」
許杜仲又看王容與的手腕,「這個單純的勞累傷,下開點藥,用開水浸了帕子捂住手腕,一天敷三次,一日可消腫止痛,不過姑娘可以多敷幾天。再有就是短期,這隻手不要勞,最好是連剪刀都不要拿起。」
至於膝蓋許杜仲開了服外敷的葯,還開了葯浴湯,讓喜桃每天給王容與熏腳,關節最是要,好好保養都會落下點,更何況不好好養。
等許杜仲診完出去,張是要許杜仲再寫一張方子他要面呈陛下,許杜仲招手讓喜桃出來,說是還有些護理的細節告知。
「等姑娘睡著了可能要發熱,等會葯送來紅紙包的藥丸子,在姑娘睡前要讓姑娘吃下。」許杜仲說,「你須徹夜不睡悉心照料,高熱來勢洶洶,若是照看不好,姑娘怕是要壞。」
「怎麼這麼嚴重?」喜桃焦急的問。
「外傷本就容易引起高熱。高熱並不可怕,重要是不能放任熱下去,葯已下肚,就看自己的求生慾,你只管拿著帕子給降溫,其餘的我明天會再來看。」許杜仲說。
他又對著張說,「我是沒有額外時間再寫一張藥方子,你就跟我回醫院,等葯照方子拿了葯,你直接把姑娘的葯案帶回去面呈陛下吧。」
Advertisement
喜桃憂心忡忡,但又不能讓姑娘看出來,見姑娘笑著,也笑著說。「姑娘想吃什麼跟奴婢說,奴婢去尚膳監給姑娘拿過來,趁著葯還沒來,姑娘先填點肚子。」
「我沒什麼胃口。」王容與只手撐著頭,膝蓋明晃晃的擺在那,豈能不疼,「王人已經搬出儲秀宮了嗎?」王容與問。
「還沒有,聽說是要等一起冊封了再搬宮所。」喜桃說。
「那芳若還在喏?」王容與閉眼,「喜桃,你去把芳若來,我有話問。」
喜桃原想說姑娘這次遭的無妄之災是為什麼,但是看姑娘芳若,許是姑娘已經知道了。
芳若忐忑不安的進到王容與的殿室,隔間早已放下帷帳,便是楊靜茹劉靜等擔憂,因為要避諱外男,都移到另外殿室。如今靜靜悄悄,就王容與躺坐著,喜桃站著。王容與那兩個腫的跟大饅頭似的的紫紅膝蓋就這麼擺在面前,芳若見了暗暗心驚。
躬行禮,「奴婢見過姑娘。」
王容與並不說話,只讓這麼站著,直到芳若憋不住了,又開口說,「姑娘奴婢來有什麼吩咐?若是沒什麼吩咐,王人那還等著奴婢呢。」
「王芷溪如今邊可是四個丫頭,還有什麼事是非你芳若不可的?」王容與淡淡問道。「比如去找安得順?」
「姑娘。」芳若撲通一下跪倒在地,「姑娘,奴婢之前當真不知安得順的關係,只是人讓奴婢去,奴婢就去了。」
「我知道。」王容與閉著眼睛說,「你是宮裡的老江湖了?我找你來你也該知道是怎麼回事?你撿你能說的說,你只是個跑的,我不為難你。」
芳若愈發的恭敬,低頭回道,「奴婢是曾聽聞有人吩咐,鼓吹人來和姑娘癡纏,讓姑娘在陛下面前替人說好話。陛下平時最恨後宮子在他面前互相謙讓求他的去留,那人想著若姑娘答應人,則犯了陛下的忌諱,若是姑娘不答應人,好歹姑娘和人的姐妹深是維持不住,日後在宮中也不會凝一繩來爭寵。」
Advertisement
「但是天可憐鑒,奴婢還什麼都沒說,人這次行為,奴婢唯一做的就是聽人的話,去傳了一次話,又歪纏了姑娘一下午,不讓姑娘出殿。」芳若直視著王容與說,雖無泣聲,但神肅穆也十分可信。
「這個人就是上次那個讓你給王芷溪錯誤報的人?」王容與睜開眼睛問,「你只要點頭或者搖頭。」
芳若在王容與的目下輕輕的點頭,姑娘往常和善的圓臉龐,如今嚴肅起來,也是格外威嚴,芳若本就是有心討好,才會一問就代,但是現下也有些張,怕不該說的也說出來,沒人保,也許消沒聲息的就死在這宮裡哪口井裡,哪棵樹下。不管怎麼樣,都不能說出郭嬪來。
「這幕後人,對周玉婷並無想法?」王容與問起風牛馬不相及的人來。
芳若雖然奇怪,心裡卻大定,只要不問幕後之人是誰就,「周姑娘的把柄太過明顯,並無所懼,尤其周姑娘又得陳太后喜歡,等佔去一個高位后才除去,才是利益最大化。」
「真是個聰明人啊。」王容與嘆氣道,「雖然每每只是針對王芷溪,我無意替王芷溪報仇,可是現在是我遭了這無妄之災,我要什麼都不做,這心裡真過不去,連病都氣的不能好好養。」
「姑娘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喜桃去替姑娘出這口惡氣。」喜桃說。
王容與沖安笑道,「這事還得芳若去辦。」
「姑娘不要為難奴婢,奴婢不敢的。」芳若說,「姑娘要是有氣,沖奴婢發好了,奴婢賤命一條,死不足惜。若是奴婢替姑娘辦事,死的就不只是奴婢一個了。」
「放心,我並不是讓你對幕後人做什麼,敢用你,必然是做好了收尾的準備,就是你攀扯到頭上,也有一百個辦法不認。」王容與淡淡的說,「只是我耳聞前殿有秀對周玉婷積怨已升,若是聽聞周玉婷在最後選三的人選中,很有可能是皇后,想著以後一輩子都要在這樣的人底下生活,一時激憤衝去跟太後娘娘申訴也不無可能。你說是嗎?」
「喜桃對前殿不,也沒有相的姐妹,你就不同了。」王容與說,「你看,我不問這幕後人是誰,我現在即鬥不過也不想斗?但我了無妄之災,就想壞一點小小的算,這不過分吧。」
「我這膝蓋可以說是托你的福,你若這點事都不肯,我就難辦了。」王容與笑著說話,芳若卻不由自主的輕抖起來,看走眼了,真看走眼了,這哪裡是個和善不與人爭也沒什麼本錢爭的秀,心思縝,漫不經心的說著威脅的話,卻毫不讓人懷疑的認真。
如果不聽的也許真的會有更大的責罰。
畢竟是徐醫來看病的秀,徐醫按值,在宮中是只看陛下,兩宮太后的醫。
「奴婢愚鈍,怕不能好好完姑娘的事。」芳若磕頭說,「但請姑娘垂憐,看在奴婢將功抵罪的份上,若太后大發雷霆,將奴婢打至浣局,姑娘拉奴婢一把。」
「你去浣局並不是什麼壞事?」王容與說,「難道你當真想去伺候王人不?」
猜你喜歡
-
連載200 章

團寵小醫妃,攝政王又犯病了
21世紀中西醫學鬼才,稀裡糊塗穿越異世,遇到洪水瘟疫?不怕,咱彆的都忘了但老本行冇忘。 皇子染怪病,將軍老病沉屙,宰相夫人生小孩也想她出馬? 冇問題!隻要錢到位,啥活俺都會! 楚雲揚:吶,這是地契,這是王府庫房鑰匙,這是…… 葉青櫻:等等,相思病我醫不了的! 楚雲揚:怎會?我思你成疾,自是唯你可醫~
18.3萬字8 8865 -
完結690 章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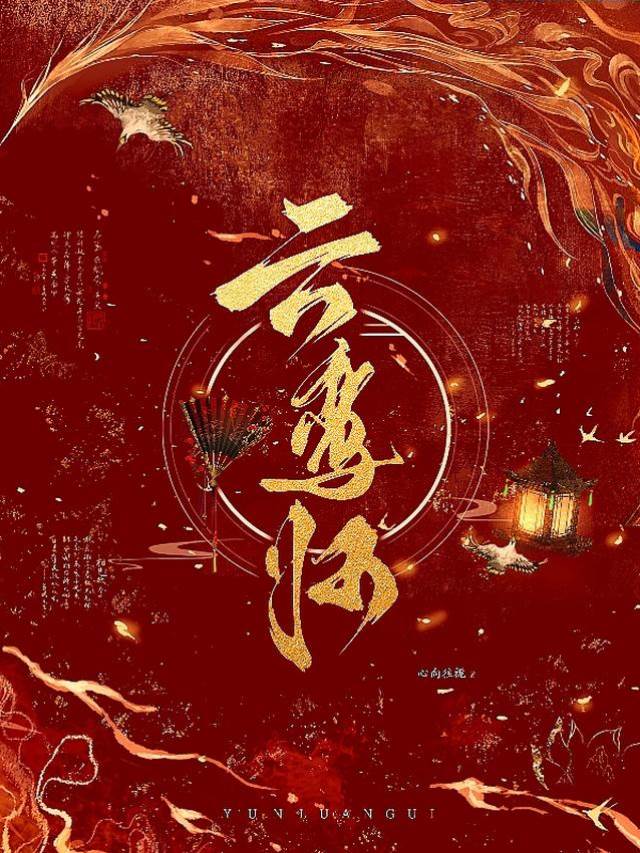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
完結213 章

位高權重的夫君傲嬌霸道,得哄著
【古言 無重生無穿越 先婚後愛 寵妻甜文 虐渣 生娃 女主成長型】薑元意容色無雙,嬌軟動人,可惜是身份低微的庶女。父親不喜,嫡母嫌棄,嫡姐嫡兄欺負,並且不顧她有婚約,逼迫她給奄奄一息的景國公世子爺衝喜。拜堂未結束,謝容玄暈倒在地。當時就有人嘲笑她身份低、沒見識、不配進景國公府。她低頭聽著,不敢反抗。謝容玄醒來後,怒道:“誰說你的?走!罵回去!”他拖著病體教她罵人、給她出氣、為她撐腰、帶她虐渣……她用粗淺的醫術給他治療,隻想讓他餘下的三個月過得舒服一些。沒想到三個月過去了。又三個月過去了。……謝容玄越來越好,看見她對著另一個男人巧笑嫣然,他走上前,一把將她摟入懷裏,無視那個男人道:“夫人,你不是想要孩子嗎?走吧。”第二天薑元意腰疼腿軟睡不醒,第三天,第四天……她終於確定他病好了,還好得很,根本不是傳言中的不近女色!
39.4萬字8 205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