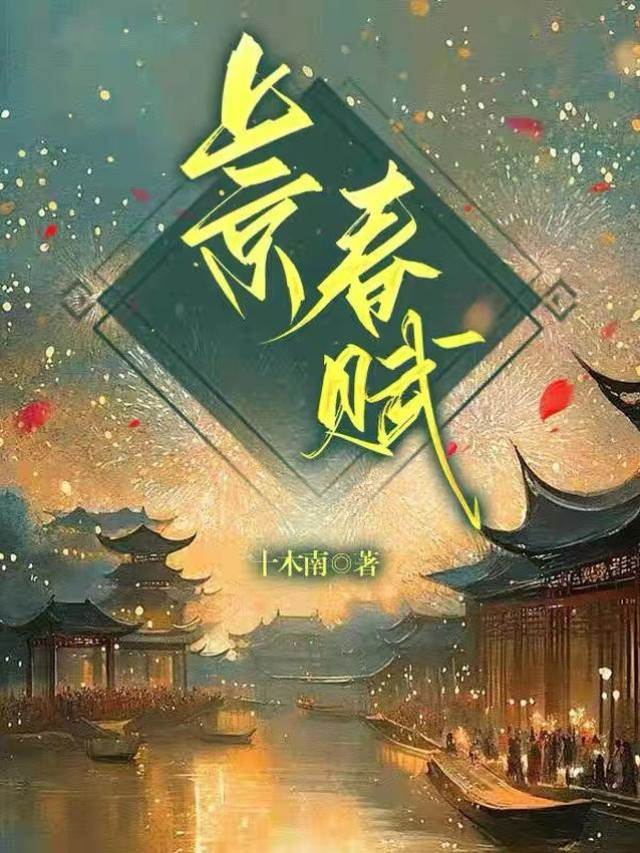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無鹽為後》 第二百八十章
王容與被朱翊鈞推醒,起先還是滿眼不解,但是隨著清醒后知來自腹部的疼痛,讓迅速了解現在是什麼況。
「別怕。」朱翊鈞抓著的手說,「許杜仲來看過了,產婆也等著,現在讓你醒來吃點東西,之後才有力氣。」
「我不怕。」王容與出笑容說,看著朱翊鈞滿頭大汗而不自知,「陛下也不要怕。」
前兩次生產,朱翊鈞都是王容與進了產房后才過來,所以就不知道王容與在進產房前還有這樣的磨難,湯跟喝葯一樣的靠灌,痛的花容失,髮都了,落地就要頓坐在地,還是要被架起來,一圈一圈的走。
「不走了不走了。」朱翊鈞半抱著心疼的說。
「不礙事的。」王容與還有餘力笑。「其實這樣想,當初常壽的時候出了意外,直接進了產房,就沒經過這一遭。」
「痛就別說話。」朱翊鈞說,「省著點力氣。」
「現在都是三郎抱著我走了。」王容與笑著說,「再抱著我走一段吧,等進了產房就是我一個孤軍戰,現在你抱著我,陪著我。」
「我等會陪你進產房。」朱翊鈞說,「從頭到尾都陪著你。」
「那還是不要了。」王容與說,瞧著朱翊鈞滿頭大汗,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去,讓無病去端了熱水來,給。
「這個時候你還什麼乾淨啊?」朱翊鈞不解。「到時候還是要出汗的。」
「那出的就是乾淨的汗。」王容與說,「反正沒有快生,隨便做點什麼都好,不要讓我在這挨著。」
朱翊鈞只能又把人抱著去了溫暖的浴室,簡單的洗后換上乾爽的睡,頭髮也用帕子紮好,「現在去產房吧。」
生之前諸多害怕,真到躺在產床上,王容與心一片平靜,畢竟同樣的經歷也是第三回了,不讓朱翊鈞在產房陪,說是會分心。
Advertisement
朱翊鈞拗不過還是守候在外面。
陣痛一陣一陣襲來,並且越來越快,王容與看著帷頂,要來巾塞,閉上眼,順著產婆的指示呼吸,用力。
如此一個時辰后,孩子還是沒有生下來,產婆面面相覷,知道怕是不好,許杜仲也看了況,最壞的況發生了。
宮口已經開了,但是胎兒太大,出不來,時間拖的越長,胎兒就要憋死在腹中了,許杜仲準備起去跟朱翊鈞稟告這裏的況。
卻被王容與抓住了袖,王容與吐出巾,面蒼白無一,大汗淋漓,只一雙眼還清醒著。
「況是不是不好?」王容與息著問。
許杜仲沉默不語,「這都什麼時候了,你還不說?」王容與追問,「你準備出去跟陛下說什麼?」
「娘娘安心,並不嚴重。」許杜仲說。
「需要你出去找陛下要個主意的時候,你還要跟我說不嚴重?」王容與抓著無病的手忍住痛,「告訴我,這是我的我做主。」
「娘娘不要為難臣。」許杜仲說,「陛下的意思是一定要保娘娘的。」
王容與的眼睛一閉,無病擔憂的喚著,「娘娘。」
「保大是怎麼個保法?」王容與重又睜開眼問,「說實話。」
許杜仲有些為難,「一碗葯下去,再把胎兒從腹中勾出。」
「現在胎兒生不下來,下了葯就能他勾出來嗎?」王容與喝道。
「有特殊的工把胎兒在子宮中分小塊再勾出來。」許杜仲小聲說。
「我不同意。」王容與喊道,「我不同意。」
「你不要想著去問陛下,就算陛下同意了,我也不同意,想保我的命是嗎,我一頭撞在柱子上,我寧願死,不要你們這麼對我的孩子。」王容與說。
「那讓陛下進來跟娘娘拿主意。」許杜仲說,「臣一條小命死不足惜,只怕耽誤太久,一兩命,傷心後悔為時過晚。」
Advertisement
「保小就是在我肚子上劃一刀,把孩子端出來。」王容與無比冷靜的說,只要你找好地方,切開后又上,不是非死不可。」
「這件方法我和你說過,你做了準備嗎?」王容與問。
「臣做了準備不算,這種方法臣沒有試過。」許杜仲說。
「那就從我上試第一次吧。」王容與說,「你去做準備,讓陛下進來,我跟陛下說。」
無病摟著王容與上半生,滿心凄苦,「娘娘。」
「不要怕,一切都往最好的方面去想。謀事在人,事在天。」王容與說。
朱翊鈞在外早就等到心急難耐,遲遲等不到好消息,心越來越沉,都不讓人在面前走,看著心煩。
宮人出來,道皇后請陛下進去。
朱翊鈞有那麼一瞬間,腳似千斤重,不想邁進去,他害怕,一直不讓他進去的王容與為什麼突然要他進去,而且現在還沒有孩子的哭聲。
他不想去面對可能要面對的最壞的境。
但這都是一瞬間的事,朱翊鈞提步往產室,都沒讓人看出他有一的遲疑。
等進到產室,朱翊鈞箭步走到王容與床邊,做過無病的位置,把王容與挪在他的懷裏包號抱好,「別怕,朕來了,朕陪著你,你一定會平安無事。」
王容與抓著他的手,「太子好像有點調皮,要選擇截然不同的方式出場。」
朱翊鈞手一,他想說什麼,但是王容與不給他機會,「我讓許杜仲去做準備了,只是輕輕一刀,太子一定會平安無事的降生,我也不一定會死。」
「朕不願意去賭這個不一定。」朱翊鈞喝道。
「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在我的肚子裏失去生命。」王容與握朱翊鈞的手,「我一定要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來。」
「你一定要同意。」
Advertisement
「不然,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一滴,一滴,熱淚滴在王容與的手背,那是朱翊鈞的眼淚,「他還沒生出來,他還不算個人,沒有他,我們還會有下一個孩子,就是沒有,我們也有榮昌和常壽,容與,就當朕求你,我們不去賭那個不一定好嗎?」
「我已經做好了決定。」王容與說,「你相信我好不好。」
「真的看著他去死,我餘生將不會再有一天是快樂的。」
「你希我是那樣的自責,自傷的過完餘生嗎?」
「如果你賭輸了,我也沒有餘生了。」朱翊鈞抖著說。
王容與閉眼,眼淚也是串的從眼角落,「我覺得我有陛下庇佑,不會賭輸的。一定不會。」
「既然你已經決定,我說什麼也阻止不了你。」朱翊鈞哽咽說,「我現在能做什麼,去太廟前跪著求祖宗保佑。」
「陛下。」王容與抓著他的手,看見許杜仲已經拿著醫箱過來,有些話現在不說,也許再沒有機會。
讓朱翊鈞轉到前來,雖然知道自己現在形容狼狽,但還是沖著他甜甜一笑,「陛下。」
「你不要說。」朱翊鈞攔住,「有什麼等你好了以後跟我說,我能等著。」
「我有好多話可以和你說,那些都可以等到以後。」王容與說,「但是我現在只想跟你說。」
「陛下真的不是我想要的丈夫,我年時希的丈夫,溫文爾雅,文質彬彬,待我專一,家庭簡單,不需要是多大或者說是多有錢。」
「我從來沒有想過進宮,沒想到不但進了宮,還是做了皇后。」王容與看著朱翊鈞一臉悲憤,彷彿說這麼張的時刻,你說這些的錯愕,不由又笑了出來。
「我抗拒過,陛下知道的,我用我愚蠢的方式反抗過。」
「但是這些都不是我想說的,我想對陛下說的是,我真的真的好你。」
「我一點都不後悔遇見你,一點都不後悔進宮,什麼溫文爾雅,文質彬彬,我都不想要了,你就是我想要的丈夫。」
「作為你的妻子,我好高興。」王容與的眼睛發亮,那樣的溫眷,想把朱翊鈞的面容印刻在心裏。
「別說這些了。」朱翊鈞說,「我等著你,我哪都不去,就在門外等著你。」
王容與笑著點頭,「不管結果如何,你一定要記住我今天說的話。忘掉我的不好,只記得我的好,我們的孩子,你會一直護著著,和我在的時候一樣。」
朱翊鈞點頭。
「你也要好好的活著,就像我在的時候一樣。」王容與說,「但你不能忘記我,我就是死了,在地底下,我也一直記著你呢。如果你忘記我,我就沒有了,真的沒有了。」
朱翊鈞埋下頭,不讓去看自己的眼淚。「這些不說,你一定會好的。」
「陛下。」許杜仲說,時間急,實在沒有時間讓他們在這裏依依惜別。朱翊鈞被宮人架著離開產室。
在門口失態蹲下,抱頭痛哭。他何嘗不知道王容與說這番話的意義,在說就算出了意外,不要怪到孩子頭上,因為他,所以甘願為他生兒育,慷慨赴死。
為什麼,他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為什麼上天還要給他們磨難。
陛下如此失態,宮人都遠離,不敢靠近,但是想到娘娘可能不好,坤寧宮各都響起忍的哭聲。
產室倒是莊重的沉默。無病給自己抹了一把清涼油,不要只顧著哭泣,這個時候更需要,王容與看著許杜仲,「如果我痛暈了,沒有大礙的話,不要把我弄醒。」
「娘娘,臣會先用金針封住道,娘娘在過程中覺不到疼痛的。」許杜仲說,準備了一銅盆的酒,滿室都是酒香。
「你還是如此可靠。」王容與笑說,「我與孩兒的命,便託付給許醫了。生死由命,許醫不用太過介懷。」
「娘娘,現在寬容可刺激不了我,娘娘要說醫不好,就拿臣全族命,臣可能會做的更好一點。」
「我的孩子,可不希他的出生帶來殺戮。」王容與笑說。金針刺,折騰了許久的疼痛,突然一下不見了,閉眼。
等待命運的安排。
又是半個時辰后。
死寂一般的坤寧宮終於響起了孩子的啼哭聲。
哭聲越來越大。
「恭喜陛下,娘娘生了,生了太子。」產婆喜氣洋洋的抱著襁褓出來,太子生的很大,白有勁,不像是剛生出來的孩子,哭聲也洪亮,哇哇的,想要哭穿坤寧宮的房頂似的。「恭喜陛下,太子足有八斤呢,是個健壯的孩子。」
「皇后呢?」朱翊鈞赤紅著眼問。
「皇后,許醫在裏頭治著呢。」產婆想到許杜仲的那一刀,不由打個輕。
猜你喜歡
-
完結41 章

東風惡,歡情薄
我不惜性命的付出,不如她回眸的嫣然一笑。
4.4萬字8 6828 -
完結117 章

嫁給大理寺卿後我真香
一盞牽緣燈,她賭上了一輩子的感情。成親五年,他不曾在她的院落裏留宿,她因此被背上了無所出的罵名。她愛了一輩子的裴燃居然還因她無所出,在她病入膏肓當天娶了平妻。當年大婚時,他明明說過這輩子隻有一位妻子的,那這位被賦予妻子之名的女子是誰......一朝夢醒,回到相遇前。就連薑晚澄也分不清哪是前世還是大夢一場。薑晚澄想:估計是蒼天也覺得她太苦了,重新給她選擇的機會。不管選誰,她都不會再選裴燃,她寧願當老姑娘,也不會再嫁裴燃。 薑晚澄發誓再不會買什麼牽緣燈,這燈牽的估計都是孽緣。可這位脾氣古怪,傲嬌又有潔癖的大理寺卿大人,偏偏賠她一盞牽緣燈。賠就賠吧,那她兩盞燈都帶走就好了。誰知道這位大理寺卿大人竟然說牽緣燈是他的心頭好,千金不賣......
21.2萬字8 28771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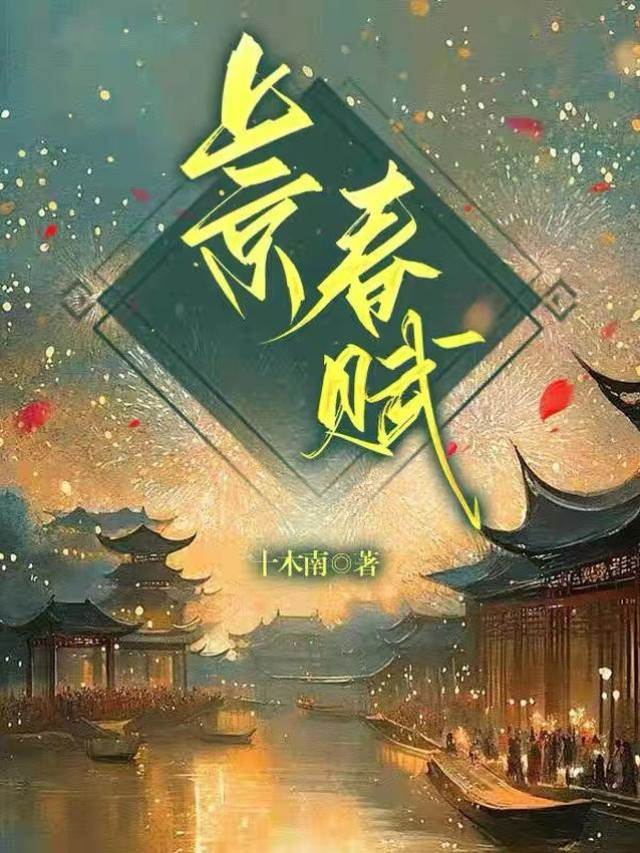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
完結133 章

重回暴君黑化前
昭寧三年,少帝病危,史官臣卿羣情激奮要處死蘇皎這個妖后。 她入宮五年,生性鄙薄,心胸狹隘,沒幫少帝料理好後宮,反而sha他寵妃斷他子嗣,硬生生將一個性情溫潤的少帝逼成了暴君不說,最後還一口氣把少帝氣死了! 羣臣:造孽啊!此等毒後必須一杯毒酒送上黃泉路陪葬! 蘇皎:我屬實冤枉! 寵妃是他親自sha的,子嗣是他下令zhan的,這暴君自己把自己氣死了,又關她什麼事? 然而羣臣沒人聽她的呼喊,一杯毒酒把她送上了黃泉路。 * 蘇皎再睜眼,回到了入宮第一年。 那一年的暴君還是個在冷宮的傀儡皇子,是個跟人說一句話就會臉紅的小可憐。 百般逃跑無果後,爲了不讓自己再如前世一樣背鍋慘死,她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阻止暴君黑化之路。 蘇皎勤勤懇懇,每天都在試圖用言語感化他,兼之以雨天給他撐傘,冷宮日夜陪伴,生怕他一個長歪,自己小命難保。 計劃實行之初卓有成效。 暴君從開始的陰晴不定,到後來每天喚她皎皎。 “你以後成了皇帝,一定要勤勉溫和,不要當個暴君,那樣是沒人喜歡的。” 少年眼中閃過幽暗。 “知道了,皎皎。” 蘇皎欣慰地看着他從皇子登上皇位,一身輕地打算功成身退的時候—— 小可憐搖身一變,陰鷙扭曲地把她囚在身邊。 “皎皎若是前世就這麼對朕就好了,朕和你都不必再來這一回了。” 蘇皎:? ! 這暴君怎麼也重生了? * 重回到冷宮最黑暗的兩年,拜高踩低的白眼,冷血無情的君父,一切都與前世無異,謝宴唯獨發現身邊的這個女人不一樣了。 她前世是個狹隘淺俗的人,今生卻斂了所有的鋒芒,乖巧小意地陪在他身邊,甜言蜜語哄着不讓他黑化。 起初,謝宴留她在身邊,是想看看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後來日日相伴,他沉溺於她溫情的哄,甜言的話,明知曉她沒有真心,卻還是飲鴆止渴般一頭栽了進去。 直到從冷宮出去之時,得知她要功成身退逃離的時候,謝宴終於忍不住徹底撕碎了這溫良的皮囊,眼神陰鷙地將她鎖在身邊纏歡。 華麗的宮殿門日夜緊閉,他聲聲附耳低語。 “你喜歡什麼樣子,我都能裝給你看。 皎皎,聽話乖乖留在我身邊,不好嗎?”
31.2萬字8 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