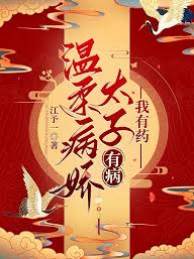《法醫小狂妃》 第88章 聚鳶臺主
頓時,所有目都聚焦在試圖裝聾作啞矇混過關的男子上,看得他無可逃,那傾城容貌難得一滯。
月九齡雖然早就猜到他的份必定不會像他自己說的只是一個江湖中人,否則不可能到三樓來,也不可能大言不慚地說他能為解說一番,所以月九齡猜他要不是份尊貴的客人,要不就是紅鳶樓的人。
如今看來是後者了,只是沒想到他竟是聚鳶臺的臺主!
江湖傳言,聚鳶臺臺主行蹤莫測且從不輕易在人前臉,因而就連聚鳶臺門下,也只有幾位分堂主見過他,世人並不知道他年歲幾何,是是丑,唯一知道的,他是個男子。
於是有人說他是個力大無窮的壯漢,也有人說是鬢髮霜白的智者,還有人說他是城府極深的變態......總之怎麼離譜怎麼編,畢竟那是江湖第一幫派的老大啊,掌握著天下報,勢力遍佈三百六十行,怎麼可能是個正常人?
於是當眾人看著眼前這個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一時沒能將眼前相貌出眾的年輕男子與聚鳶臺臺主聯繫到一塊兒。
在場除了顧墨玧其他人都未曾見過聚鳶臺臺主,但顧墨玧既然說出來了,那他十有八九就是了。
眾人恍然醒悟,如此說來,紅鳶是紅鳶樓頭牌,而他是紅鳶樓東家,這麼說來他確實算是紅鳶的主人了。
君子沒料到顧墨玧會當著眾人的面拆穿他,本還想最後掙扎一下,結果接收到眾人不約而同投來的「原來如此」的目,哭笑不得地否認:
「哎!不是我!」
然而他有說謊的前科,並沒有人因此相信他所言。
Advertisement
於是君子只好耐著子補充解釋:
「雖說紅鳶樓是聚鳶臺門下,但紅鳶樓有負責皇城的分堂主在管,我甚過問,更不認識什麼紅鳶姑娘李姑娘的,縣主,你一定要信我!」
說完還不忘沖月九齡眨眼,看上去要多無辜有多無辜,要多純潔有多純潔。
月九齡差點被他那張無害的臉蠱,輕咳一聲回過神來,「我也覺得不會是君......臺主」
君子聞言連連點頭,月九齡將視線放在李艾上,淡淡地說:
「進門后從未正眼看過君臺主,臨死了,也未曾看最後一眼。」
君子:「......」為何他有種被冒犯的錯覺?
然而此時他顧不了那麼多了,見月九齡鬆口便趁熱打鐵地道歉請求原諒:
「縣主恕罪,我不是有意瞞份,只是不想讓縣主先為主地認為我與縣主相識是有所圖而已。」
月九齡不以為然地睨了他一眼,你這樣掩藏份更加可以好嗎?
君子彷彿沒看到月九齡眼裏的嫌棄,自顧自地繼續說:
「請縣主容在下重新介紹自己,敝人君子箋,是個聚鳶臺的小頭目,十分榮幸能親眼目睹縣主風姿。」
聚鳶臺的小頭目?
月九齡心中冷道:虧你說得出口,聚鳶臺門下的紅鳶樓舉辦個義賣會,全天下的人都破了頭腦想要得到請帖,怎麼從你口中說出來,好像聚鳶臺隨時都可能散夥了?
那些人若知道你如此自謙,會不會氣得吐?
月九齡皮笑不笑地回道:
「君臺主謙遜了,是我到榮幸才是。」
君子,不,君子箋還客氣擺手,「不敢不敢。」
Advertisement
就在月九齡與君子箋「冰釋前嫌」,互相客套時,屋裏的氣氛正在一點一點地凝滯。
悉這種寒意的殘立即看向自家侯爺,果不其然,顧侯爺雖然面無表,可墨的眸子已經結了一層冰霜了!
就在殘猶豫要不要拚死上前緩和一下氣氛時,顧侯爺開口了:
「與案子無關之人需迴避,不要妨礙查案。」
殘鬆了一口氣,然後次意識到顧墨玧這話,是針對君子箋?
可侯府與聚鳶臺並沒有什麼結過梁子啊?
君子箋聞言頓悟,「侯爺所言極是,我這就讓他們都退下。」說著便走到門邊,招來掌柜吩咐了幾句,然後又折了回來,頗有圍觀府辦案的意思。
顧墨玧瞥了他一眼,語氣冷得讓人打冷:
「君臺主也不適合在此地逗留。」
其實君子箋留下也無大礙,只是他忽然想起君子箋說有幸目睹月九齡的風姿時戲謔的眼神,就想讓他有多遠滾多遠。
可聚鳶臺臺主本人大概被人眾星捧月慣,既不會看人眼,也不知臉皮是何,聞言茫然地反問:「我不是無關之人啊,我也算是個目擊證人吧?」說著還不忘保證,「侯爺放心,在下定會全力配合的,若有什麼需要,儘管吩咐。」
月九齡聞言不由冷笑,也不知道剛剛是誰極力撇清自己和李艾的關係,這會兒倒不忌諱了?
顧墨玧並沒有接君子箋的話,只是定定地與之對視了一會兒,隨後不著痕跡地移開,轉而開口問月九齡:
「需要解剖檢麼?」
月九齡這會兒子已經沒了不適,起蹲在李艾首旁邊,一邊仔細查看,一邊回道:
Advertisement
「死因清晰,就是中毒而亡的。不過謹慎起見,我會做一次檢的。」
顧墨玧點頭,他也是這個意思,雖然知道李艾是服毒自盡,但與那個所謂的幕後兇手接過,或許能從上找出些蛛馬跡。
而一旁的君子箋卻有些不解:
「可明明走得了,又為何要在侯爺他們現後自殺呢?」
當時月九齡明明承認沒有證據抓,而也打算走了的,沒理由因為顧墨玧等人出現了就決定自我了結啊?
思及此,他恍然,「還是說,侯爺已經查到確切證據了?」一定是這樣,所以李艾知道今日是無法全而退了,才決定自殺。
但接著他又有疑問:
「那縣主又為何放走?」
就算月九齡不知道顧墨玧手上是否有證據,但後來聯想前後便也猜到了,可卻還表現出對紅鳶束手無策的樣子,讓紅鳶信以為真打算離開。
思及此,沒等人回應,他又拍了一下大,驚喜地看向月九齡:
「原來是準備釣魚啊!」
說著他自顧自地「嘖」了一聲,「可惜,魚沒釣到,線還斷了。」
月九齡看著他自言自語地演出一臺戲,不知怎的有些於心不忍,於是沒有拆穿他,而是清了清嗓子轉移話題:
「臺主能否借我一間屋子?」
「要剖?」
「那就這兒吧!」
月九齡挑眉,「臺主不怕日後沒生意?」
君子箋嘆了口氣:
「反正已經死了人了。」
一副破罐子破摔地模樣,月九齡差點信以為真了,不過是出於禮貌問一下,這人還順桿兒爬了?
紅鳶樓的包廂,別說死了人,恐怕就算流河,世人也依舊趨之若鶩。
君子箋看了一眼桌上那套西洋銀,若有所思,「剖的刀倒是有現的,侯爺還真是有先見之明啊。」
說完還不忘沖顧墨玧意味深長地笑了一下,又興緻盎然地問月九齡:
「還有什麼需要麼?」
月九齡:「需要臺主騰個地。」
君子箋立即明白,笑著擺手:
「就走就走!」
秦琰殘等人也識相地道別離開,顧墨玧走在最後,臨踏出門檻前頓了一下,回過頭,對上月九齡詢問的目,有些遲疑,但還是留下了一句話:
「我去查一下今日的客人。」
月九齡愣了一下,門已經被顧墨玧帶上,才不輕不重地應了一聲:
「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91 章
農門貴妻相公掌上寵
一場戰火她從秦芷變成秦青芷,一冊兵書送出,她從秦青芷變成周萱兒,經曆讓她明白,她要想安穩過日子,這輩子就老實當好村姑周萱兒。爹孃一對,年紀不小,繼兄窮秀才一個,‘親’哥哥一,二,三個,嫂子三個,侄子侄女若乾,一家子麵色青黃,衣服補丁摞補丁,能不能長大都懸,有心改變,可現實教會她出頭的鳥會被打,她隻能小心翼翼裝傻賣萌提點潑辣娘,老實哥哥,哎,她實在是太難了。他是村裡人嘴裡的小公子,五年前他們母子帶著忠仆來到這裡落戶,家有百來畝地,小地主一枚,村裡人窮,地少人多,為餬口佃租了他家的地,因他年紀小,人稱小公子。周萱兒第一次見這小公子被嚇,第二次見覺得這人有故事,自己也算有故事的一類,兩個有故事的人還是不要離得太近,可村裡就這麼大,三次,四次之後,不知何時閒言碎語飄飛,她氣得頭頂冒煙要找人算賬,卻發現罪魁禍首就在自己身邊。娘啊..你這是要你閨女的命呀。什麼,媒婆已經上門了,你已經答應了。周小萱隻覺得眼前一黑,腦海裡隻一句話,我命休矣!
60.6萬字8 25676 -
完結801 章
穿越后,我被竹馬拖累成了皇后
顧靜瑤很倒霉,遇到車禍穿越,成了武安侯府的四小姐上官靜。 穿越也就算了,穿成個傻子算怎麼回事啊?! 更加倒霉的是,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呢,她已經被自己無良的父母「嫁」 進了淮陽王府,夫君是淮陽王有名的呆兒子。 傻子配獃子,天設地造的一對兒。 新婚第一天,蕭景珩發現,媳婦兒不傻啊! 而上官靜則發現,這個小相公,分明機靈得很啊……
147.3萬字8 12394 -
完結616 章

攝政醫妃不好寵
大婚當前被親妹妹一刀捅進心窩,摯愛扭頭就娶了殺她的兇手。一夜之間,她失去了親人、愛人,和家。 逆天崛起記憶恢復,才發現爹不是親爹娘不是親娘,自己十多年居然認賊作父! 好,很好!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作為23世紀的戰區指揮官兼戰地軍醫,她左手醫毒雙絕右手機槍大炮,虐渣絕不手軟,還混成了當朝攝政大公主! 嫁給逍王了不起?信不信我叫他永遠也當不了皇帝? 娶了白蓮花了不起?反手就讓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逍王殿下:“阿辭,要怎樣你才能原諒我?” 楚辭:“跪下叫爸爸!” 奶奶糯糯的小團子:“父王,螞蟻已經準備好,不能壓死也不能跑掉,父王請!”
106.5萬字8 36798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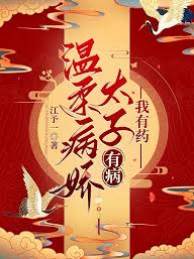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 7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